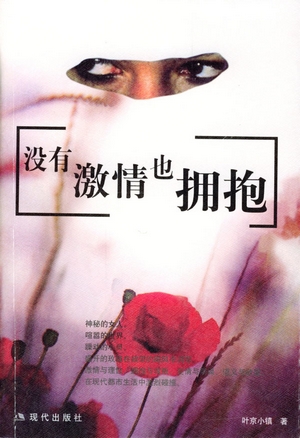背对背的拥抱-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这才明白过来,怕得厉害,朝他们摔东西,把办公桌推到一边,用尽全身力气反抗,过了五、六分钟,才被几个医生一块给架住了。护士拿了衣服来,想带着我往里走,我还在挣扎,我妈从后面推了我一把。
我一下子哭了:「妈你骗我,我没病,你不要我了。」
我趁他们不注意,还想跑,被等在一旁的医生给按在地上。
我不停乱扭,破口大骂,陆续有人赶过来,一起帮忙按着,最后几乎是被半抬进去。
我妈就坐在外面哭,扒着栏杆,只说:「钱宁,好好的,我再来看你。」
我在里面嚎,骂得很凶,还在和人扭打:「你们都骗我!妈的!」
我忘了自己哭得有多凄惨,只记得嗓子吼出血了。
找妈在外面坐着,过了会,才站起来,我看着她给穿白大褂一个个鞠躬,请他们照顾她儿子。
渐渐地,眼前的女人,渐渐变成了戴端阳。他咳得厉害,我陪他去拿药,不知怎么又被人按在地上,要关进铁笼子里去。
我哭出声来,朝那不知道是我妈还是戴端阳的人哭:「你骗我,你也骗我!」
眼泪和鼻涕挂了一脸,我仿佛失去了力气,连站都站不稳,又仿佛全身都是力气,挥舞着拳头,要和他们讨个公平。
连你也不要我了吗?
不是你说的,让我不要跑了?
连端阳你也……
不知道过了多久,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李哥箍着我的手,戴端阳蹲在一边,手上是刚夺下来的水果刀。两个人都是筋疲力尽。
我用力地瞪着他们,等看清了他们脸上被我用拳头打出来的淤青,才不敢再看。
我战战兢兢,小声地说:「我是个疯子。」
他们没人反驳我,只是脸色苍白地蹲坐在那里。
李哥慢慢松开手,却还严阵以待,似乎还在提防我会突然发疯。我忽然哆嗦得厉害,脑袋里一片空白。
为什么到了这一步,我还在等,等人来告诉我,我没有疯。
我逃进客房,把我攒的钱都塞进口袋,匆匆忙忙地从他们面前逃走。李哥拦着我,我透过他身体的空隙,看到戴端阳苍白的脸,一时间万念俱灰,硬着挤了出去。
走在路上,才想起我没了换洗的衣服,没了住的地方,没了吉他,什么都没了。
我突然明白,我为什么急着要走。
原来我不是怕拖累他,而是怕他有一天会这么觉得。
李哥追出来,我躲进树影里,看着他跑过去。
就这么站了好一会,脚终于找到了力气,刚要走,突然看见戴端阳从楼道口冲出来,推开铁门,大声地叫我的名字。
我吓了一跳,几乎弄出响声,继续往树影深处退。
端阳忽然停了下来,大喊起来:「钱宁,你这个胆小鬼!」
我猛地捂住嘴巴,只听见他站在深夜的街道上,一声又一声地骂我:
「钱宁!胆小鬼!」、「钱宁你是胆小鬼!」
我这时才看见端阳手里提着一个塑胶袋,也不知道装了什么。等他彻底去远了,我回到马路上,周围只剩下几个遛狗的,四、五只膘肥体壮的大狗你追我赶地从路边窜出来,又窜进草丛。
我定了定神,正要走,脚下咯嚓一声踩到什么东西,捡起来一看,发现是一块红色包装纸的硬糖。
我愣了一下,想不出哪里来的糖,一边捏在手上看一边往前,刚走了两步又踩到一块。我这才反应过来。
借着路灯微弱的光,看到路上隔几步就放着一块糖,各种颜色,各种口味,全是我喜欢的,连成了一条细细的线。
我突然反应过来,一边走一边捡,越走越是行人稀少,隔着老远才有一个路灯,数不清的飞蛾撞击着灯罩,发出呲呲的轻响。
只走了几百米,手上就拢起了满满一捧的糖果。我只好拿衣服下襬兜着,衣襬都装不下的时候,还在往口袋里塞。
走到路尽头,下意识地弯腰伸手,地上已经没有糖了。
眼前是一大片填湖用剩的沙,沙地旁放着一双皮鞋,一个人赤着脚,背对着我站在沙子上。
他拎着漏光了糖的糖果袋子,至今没有发现自己的袋子破了洞。
我打了个哆嗦,不知道站了多久,才敢小声地叫他:「我不是胆小鬼。」
他猛地回过头,瞪大了眼睛。我浑身发抖,几乎又想逃了。没等迈开步子,端阳已经紧紧拽住了我,把我也拽到沙地上,勒令我站在原地。
我的鞋底一下子沾满了沙粒,本来还想抱怨,感受到他在夜色中冰冷的体温,又渐渐放松了紧绷的四肢。
因为他的那一堆骂,我忽然不想浪费最后的光景。
哪怕只是看着他,到我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
我告诉他:「我今天生日。」
戴端阳胡乱点了一下头:「当然,我记得。原本就打算拉你出来,过个生日。」
他把我松开,伸手在塑胶袋里摸出没拆封的纸杯,发现糖少了,也只是愣了愣。
我看着他忙了半天,把杯子一个个插进沙地上,然后再分别放进蜡烛,拿出打火机,把第一个杯子里的蜡烛点燃。
橙黄色的火光突然亮了起来,纸杯被照成半透明的颜色。打火机上的火苗被风一吹,腾地拉长了,像是烫到了那人的手。光一下子减了,过了几秒才重新燃起,紧接着,第二个蜡烛跟着亮了。
我用衣服下襬兜着数不清的糖,愣愣地看着蜡烛一个接着一个被点亮,最开始是一个小小的弧线,后来才发现更像一个饱满的挑子,还剩下五、六根蜡烛的时候,我叫了他一声:「戴端阳。」
他飞快地回过头,拉着我站到蜡烛圈里,把剩下的几个蜡烛也点燃了。
我被他一拽,连衣襬上兜着的糖都掉了好几块,想要去捡的时候,端阳拦了我一下。
我还没明白过来,看着地上黄橙橙的火,摆成了一个蟠桃的形状,小声说:「桃子,嘿,你真有心,给我祝寿。」
端阳拽着我往后转,嘴里愤愤骂着:「见鬼的桃子。」
我才知道我看反了。
用那么多杯子摆出一个爱心,还要人半天才明白过来。
该怎么说他呢?
戴端阳拉着我,脸上似乎红了一下。我兜着一兜的糖,忽然也不敢看他:「该走了,李哥还在找——」
端阳弯下腰,把我掉的那几块糖都捡起来,嗤了一声:「李孟齐……」
我正要一脚跨过纸杯,听见李哥的名字,愣愣地看了他一眼。
端阳站起来,剥开糖纸:「吊点滴的时候碰到他,他说起你们以前的事,要我好好照顾你。」
我伸长了手,要从他手上把剩下的糖抢回来,结果却搅得更多的糖掉在地上。
端阳把剥开的糖果塞进我的嘴里:「我车里还有好几袋,别急。」
等我把他喂的那块吃完了,才发现太亲昵了。
端阳脚上沾满了沙粒,一直沾到挽起的西装裤腿上。他把手交叉着垫在脑后,轻轻地笑了两声。
「他说以前你帮人搬箱子,一路搬一路骂,忙帮得不少,就是十句话有九句话是假的,只有不怎么开口的时候,才知道你在帮忙。」
我脸上微微发烫,想让他别说了,戴端阳反倒越说越上瘾:「他说你中学性向就被人看了出来,遭了不少罪,胆子也变小了。」
我连糖也不要了,挥着拳头要让他闭嘴。
端阳压低了声音:「他还说,那时候一直以为你喜欢的是他,心里很高兴,后来才知道不是……」
我突然懵了。
戴端阳用力拽着我,轻声问:「钱宁,你真的喜欢我?」
我心里难受得厉害,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只觉得脑袋嗡嗡地响,端阳还在问:「我真的是你第一个……」
我一把推开他:「我那时候把地址都告诉给你了,等了几周你也不来,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端阳睁大了眼睛:「什么时候的事?我溺水住院的时候?我回到宿舍,才知道你搬走了,连你去了哪里都不知道。」
我迟疑地说:「我放在楼下信箱里的。」
他也是吃了一惊:「没有,钱宁,信箱里没有。我根本找不到你,当时一肚子气,要是知道你给我留了地址……」
他突然顿在那里,我们几乎是同时明白了过来,大学一个宿舍共用一个信箱,八成是别的舍友看我不顺眼,把我给他的信扔了。
我们半天没有说话,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听见戴端阳小声说:「这两天,我去找过你妈妈。」
我木讷地听着,第一个想起的居然是只养我到十八岁那句话,转瞬之间,又想起她每一次的眼泪,女人往往比自己想像中坚强,男人则刚好相反。
端阳握住了我的手,几不可闻地说:「她问我钱宁在哪,为什么不肯回来?」
我使劲地想挣开端阳的手,他硬是不放,飞快地说:「大学交换的时候就是向她打听到你在那所学校,毕业后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钱宁。她也在找。」
我终于不挣了,只是瞪着他。
端阳脸上一红,低声说:「我都知道了。」
我愣愣地回了一句:「什么?」
纸杯里的蜡烛燃烧了好一会,烧融的蜡又凝固在杯底,露出一截焦黑的烛芯,烛焰在夜色里越拉越长。
我定了定神,才听见端阳在耳边说:「伯母说,下个月想接伯父回去住。我们也回去看看吧。」
我的手哆嗦了一下,戴端阳看我越挣越厉害,就一直搂着我,直到我胀痛的脑袋慢慢平复。
我轻声说:「你见过我爸了。」
他点了一下头。
我嗓子又开始疼,忍着疼说:「那你就该知道……」我站得笔挺,却笑得比哭还难看:「疯子有多可怕……」
端阳小声地说:「不可怕,钱宁。」
他还没说完,我就嚷嚷起来:「可我不要你来可怜!」
他看着我笑了一下,眼睛都笑得弯弯的:「可怜?什么乱七八糟,钱宁,你真是……」
我皱着眉头问:「你喜欢我哪一点?」
端阳笑着说:「每一点。」
我揪着他的领口咬牙切齿地问他:「你给我认认真真地说!哪一点值得你喜欢!」
我吼得急了,喉咙不配合,低着头得咳了一阵,才说:「你明知道的,我已经唱不了了。」
他突然往前走了一步,用手轻轻地环住我。
我脸上涨得通红,却仍不肯放弃瞪视他。
戴端阳放轻了声音:「钱宁,我这次回去,向伯母问起你休学两年的事。你猜她说了什么?」
我愣在那里,嘴张了张,喉咙里发出嘶嘶的声音:「说了什么?」话一出口,又觉得自己上了钩,慌忙补上一句狠话:「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她说钱宁住院的时候受苦了,」戴端阳用从未有过的温柔语气,轻声说:「也说起出院后复诊,医生要你说说以前的事,你说了一大堆,总共只出现过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钱宁,一个叫戴端阳。」
端阳低着头,眼睛却亮晶晶的:「问你别的同学叫什么,你都不记得了。」
我骂起来:「没有的事。」
戴端阳认认真真地看着我:「那你当着我的面,再说一次?」
我下意识地说:「这有什么!小时候我们住在同一栋筒子楼,六层楼高,两头是公用的厕所,你老穿着一件花毛衣……」
我突然噤声,铁青着脸,试着把前二十二年的故事再倒一次带。六层高的筒子楼,在单双杠上喂我吃年糕的端阳——
我忽然不知道该接什么话。
那时候在医生面前费力地想了半天,结结巴巴地说了好长一段,以为巨细靡遗。直到今天被他一说,才发现那么多苦辣酸咸的事,往外倒的时候,只剩下两个人的名字。
我比最蹩脚的导演还蹩脚,开拍了二十二年,最后只拍下了两个人。
我想了半天,强笑起来:「幸好分手了。不然除了爸妈,我这一辈子……」只记得他。
「我现在比过去强多了!除了李哥,还记得好多人,像琴行的,歌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