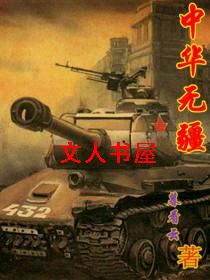光绪中华-第38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一条款被中方一个上午的考虑后正式接受。但前一条款当即被外交部否决,这等同于白白送给美国一个军事人员进入中国势力范围的资格。外交部重申了夏威夷作为看管地的不可动摇,并且希望美国谨慎考虑在此事上的立场,为了此事破坏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这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
当天的会谈毫无进展,几乎可以说是白费功夫。我们当然不着急,着急的必然是英国人,我指示外交部在坚持三点意见的同时,可以稍稍在无关紧要的方面对美国人稍作让步,以配合接下来的外交行动。
事实上这也是个培养小辈的机会,在考虑了皇次子溥偀和已经在内阁弼德院任职的三子溥夏之后,我开始渐渐倾向让溥夏独立去处理这件事务看看。一来他有在美国受教育的背景,与美方沟通起来没有问题,二来次子的德国背景要在下一阶段的事务中派上用处,过段时间就打算要派他去处理德国方面的事务,并与他哥哥新蒙国王合作,现在派出去,马上又要派出去,看上去基本上他的储嗣地位就基本确定了,这不是件好事。
在当晚的家宴上,我稍稍透露了这么点意思,皇长女惠宜和硕公主吵闹着也要去,而次女顺淑和硕公主也趁机提出想到外面去看看的意思,我问起她想去什么地方,她却忸怩着说不上来,看上去很像是有意于某人的样子。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工夫多理之方面的事情,只是藉机说了些我对儿女婚事上的态度算是半开明,也就是说自己去找,但是最后我得权衡一下才能明确静态是否允可。
恭亲王载滢的儿子小恭王溥伟前段时间写信回来说起想从西疆回来,他如今驻屯在西疆首府杜尚别,可能是呆不惯当地的环境,说想往东面调调,但他也不敢说要回北京,只是想去日本呆上几年云云。(注:历史上溥伟并非载滢之子。)
他的事情我是打算让他再在西疆呆几年,回头回京来看看材质再说的,现在他既然想要换地方,也没有拒绝的道理,于是让他调动去了京都松平氏那里,过年期间松平氏说起的想要纳明治的某个内亲王的事情,正好交给他办一办看看他的能力。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比较聪慧能干,但从他在西疆的表现记录来看,恐怕连他老爹十分之一的本事也拿不出来。
安顿了皇家的这些年轻人的事务,估摸着惠宜公主这一去南疆,恐怕是要见蔡锷的,这两个人也该完婚了,蔡锷这个人近期来看有些太过扶持了,这样根基恐怕要成问题,好在这小子争气,打了一个漂亮仗,但我考虑着他的职务还是不要动为宜,爵衔上本来打算给他晋一晋,但马上就要做额驸了,再动又有些不合适,看来让惠宜跟他结婚也正好给他一个补偿吧,至于他现在担任的临时的军级职务,还是给他扒下来为宜。
就这么躺在床上思来想去,回头一看,这一晚上居然全部是在为儿女们绸缪着,身边叶氏正嫔静悄悄地趴在身边,一动也不动的,再看居然已经睡着了。
次日一大早,中美两国关于英法战俘问题的磋商进入第二天,美国人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他们首先表示愿意无条件接受我提出的三点意见,特别是夏威夷集中营的意见。但他们希望中美双方能够就便修改一下夏威夷非军事化条款上的冲突点,要关押七八万的战俘,仅仅几百名治安警察是不够的。这一条在情在理我们都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用了一个上午时间,将双方准军事人员的驻扎总数提高到了一万人。中美双方按照三比七的比例分配。
下午时华生也许是心情大好的缘故,开场就畅谈了一番对目前世界笼罩在战争之中的感慨,并表达了对和平的冀望,随后他又拿出了一份和平建议出来,与之一起的,还有一张他在不久前在梵蒂冈与教皇本笃十五世的合影照片,声称他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着教皇陛下来寻求和平的曙光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在缅甸战争问题上站在弱势的英法一方的缘故。
随后他便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也就是由美国代表主持的情况下,中国暂时先在战俘宣誓不再与中国为敌的情况下释放他们回国,而物资则全部以战利品收获处理。这样既可以平定中国军方的不满情绪,也可以表现出和平的诚意。
另外作为补偿,可以就战争赔偿问题对英方提出要求。印度洋各重要港口均向中国开放,并割让锡兰岛给中国,孟加拉非军事化以作为中英之间在击垮亚次大陆与中南半岛之间的缓冲。英方也愿意在波斯和阿富汗问题上做出让步。
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谓宗教原因和悲悯的情怀等等废话是不能吸引我和让我的外交官们信服的,不过教皇特殊的身份和他所提出的和平建议条款却不能不慎重面对,据现有的状况来看,教皇并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系统性的和平计划,他只是在某些公开场合发表过对战争的厌恶和战争国家的嘲讽,诸如“无能的屠杀”,“愚蠢的政客”等等的词句而已。而这一次华生律师所出示的文件。应当是教皇第一次试图介入到战争的斡旋中去的努力了。
这也是一个系统性的和平计划,一共有七点:一,结束战争,签署公开的和平条约,并杜绝一切秘密外交。二,平时和战时的公海少上航行的绝对自由。三,裁减各国军备到一个合理的限度。四,德军恢复比利时的领土和政权。五,恢复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格罗等国的领土和政权。六,重建波兰,以保障和平。七,法德恢复欧洲在普法战争前的边境线。英法德海外殖民地应当做出适当的,足以降低冲突风险的调整。
当然,这也是一个奢望的和平,一个没有任何世俗权力的教皇,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世俗政府支持的话,他的任何和平计划只能让正在交战的强者嗤之以鼻,而这份计划力求对英法德等国公平,有些条款对同盟国集团极度不公平,而有些条款又要求英法做出极大的让步,在这个血海深仇已经结下的年代,指望他们对对方做出让步实在是太可笑了。
所以,稍晚些时候这份计划传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的官员们已经建立了和我的共识,那就是本笃十五世已经谋求到了美国的支持,而且他还正在谋求中国的支持。
这份和平计划的七点内容已经不是当晚御前会议的焦点,而华生不在更早时候说明他的这一个身份,恰恰会在谈判进入僵局的第二天才抛出这一个新素材的原因,才是这一晚的讨论焦点。
这只有两种可能,并不太难猜测。要么就是教皇本无争取中国支持的意思,因为中国并非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是以儒教为国教的国家,他即使是想争取,也未必能够实现,而华生律师之所以把这个东西抛出来,恐怕是美国也希望中国能够与他们一起去通过支持教皇的和平计划,来帮助他们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毕竟无论如何,中国也是参战国之一,将来无论如何,在和平计划的实施和推动上的功劳都不可能超过美国。而抛出这个和平计划,也趁便可以解释美国为何会在缅甸战争问题上不惜开罪中国的原因。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教皇有意争取中国的支持,但尚未正式展开与中国的接洽,原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并非基督教国家,或者他也是希望通过美国来中转联络中国的支持,毕竟美中关系是近年来最成功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国也隐为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世界的领袖角色。
而美国人则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并不希望中国已经在亚洲建立起超卓地位和崇高声调后,再在世界重建和平的努力中发挥出更多的作用,所以才会隐蔽下这个重要的讯息。只是在充分考虑完全隐瞒的可行性并不高,又加上他们也很需要一个对中国解释立场的理由的缘故,他们才会在到中国后近十天才正式向中方公布这一计划的原因。
这两种可能都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在座大臣的一致意见也是认为无论如何,美国渐渐已经开始显露出对中国不友好的倾向,或者说中国已经成了他们重要的战略对手之一,他们需要运用各种方法来降低中国的影响力。这次英印战俘问题不管如何解决,中国与美国在英法眼里都会走向两个不同的极端。
所以,国内的亲德派反而是最为高兴。醇亲王载洸算是军方在北京的最高代表人物,他与在京的两个元帅都表示无论如何,中国都应当趁此机会大幅加强与德国的合作,并且迫使下个月抵京的美国总统塔夫脱一同签署公平贸易宣言,也就是民用船只在任何海域的航行自由,以便从海路向德国扩充销售。
他们的提议也得到了内阁大部分官员的认同,这有利于刺激中国的工业生产,各种产业都可以在下年度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而这与教皇所提出的七点和平计划也是吻合的。中国不妨发表声明表示基本支持教皇和平计划的立场,同时做好强行说服美国赞成公平贸易宣言的准备。
筹码就是这近八万人的战俘和三十一条大小船只的俘虏。不管怎样,美国既然已经答应英法出面来保证战俘的问题,他们应当会付出一定的努力去完成这一任务,中国完全可以把战俘问题与和平计划捆绑起来,并进而影响公平贸易宣言的签署。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恐怕还需要做出一些让步才行,美国方面一定是从英国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次才会如此支持英国,从谈判条款上来看,英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全印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被德国海军牢牢封锁住以后,英国能够派得上大用场的海外兵源地,就只剩下了印度,以及非洲一部分国家。而印度人的人口和忠诚度都能够让大英帝国在未来的战争中获得一定的保障,如果放由中国和德国海军势力进入印度洋并逐渐在波斯湾及阿拉伯地区取得立足点后,红海的入海口将会被轻而易举的封锁住。大英帝国仅仅依靠本土,那当真是要求上帝保佑才能够抵挡得住德国人的铁蹄了。而且他们自己后院还有一个大麻烦,爱尔兰人正在进行着大起义。这也牵制了一部分陆军和海军兵力,而如果不是海军及时得到了太平洋舰队的补充的话,那么德国人甚至可以干涉爱尔兰事务,届时不列颠本土是否安全已经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所以,可以想象的是英国肯定是在美国那里下了血本,才能让美国如此挺它。至于是什么现在无从得知,但绝不会小到哪里去,而美国获得这一个大进项之后,才会改变在亚洲的谨慎态度,直接干预到了缅甸战争头上来了。
而他们的胃口也会慢慢变大,至于是否会促使他们直接参与战争,那就是天才知道了。
原本是就当天外交磋商进行讨论的御前会议,最后已经演变成了美国问题研究会了,讲了约莫三个小时之后,我看几个老大臣诸如袁世凯,戴鸿慈等人都已经提不起精神来了,于是便打算散会。但又想起还有个俄国事务还没有议,心一横还是把他们留了下来。
用了夜宵后,众人稍稍恢复了一些精神,这样的会议自从一战开打以来,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这些军政大臣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接下来的议程说是俄国问题,其实也只是一个总称而已,与前面的美国问题也不是格格不入的。
譬如中东问题上面,沙特国王这个人是否需要警告一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