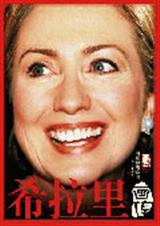沙汀画传-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泡菜、腊肉也做得不错。母亲做为一个女流之辈,凭着她的社会交往,建立起她在全镇的威信,连袍哥中人都尊称她为“杨大姐”。母亲委实太强了。她敢把犯了刀案的袍哥,藏在家里,不动声色。替舅父买枪支,也是她搭上的线索。幸亏她对朝熙的惯宠也有限度,否则,在一顶过大的保护伞下,只易生长纤弱的幼苗。杨朝熙长期得到母亲“保护”,旷课逃学不好好读书,直到十一二岁,有一天早晨,他又赖在床上不起,母亲气了,掀开被盖,伸手便打,但才打了几下,自己倒哭了。她哭着诉说不幸,诉说丈夫的死,寡母孤子的无依靠和他的不争气。一个平时极为硬气的母亲的哭泣,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极深的印象。朝熙可怜起她来,也恨自己。他真正开始用功读书,便是从这以后的事了。
(你的多感,在这里找到了源头。表面看来,你不是那种充满浪漫气息的人。可就像你的母亲,在硬朗的性格外壳之中,包藏一个易受外来刺激的敏感的心。幼年的你,经母亲看到一个大家庭的兴衰荣枯,由家事的沉浮,引导你从小就关心人世)
茶馆——乡镇文化环境
杨朝熙是吃奶母的奶,在川西北的小城镇长大的。
有个朱大娘,永安乡人,带他的时间最久。断奶后仍然留在他家里。这个奶母是他童年的引路人。
(你不要把我的奶母写成高尔基的奶母,或者鲁迅的长妈妈。不是这么回事。她只是抱着我,牵着我的手,走遍我们镇的角角落落)朱奶母经常领他走出老屋,到十字口逛街。
十字口最多的便是茶馆。按照本地市民生活的不成文规矩,男人们一早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一路扣着钮扣,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趿着鞋先奔这个地方来了。没有茶馆就没有生活,这点道理在四川的这个小市镇尤其见得正确。
十字口上旅店兼营茶馆的尚友社,店堂里低矮的茶桌擦抹得还算干净,俯仰坐靠都很舒适的矮竹椅上,已经上了茶客。这都是乡土社会固定的主顾,位置也很少变化,谁是坐在当街的桌边的,谁是坐在里面第三根柱头下的,一一对号,丝毫不差。
这时,人们悠闲地用茶船子托起茶碗,从半扣的茶盖缝隙间嘘嘘地吮啜品味。有人让堂倌送上热水、帕子,在苏苏气气地洗脸,用手指头刷牙齿。有的人已经浓浓地灌下了几碗茶,“开了咽喉”,在互相交换从昨晚离开这里以后得到的市井消息。世代住在这个城镇上的人挨得如此之近,打个喷嚏都能听到,以至于大到县政要事,小到床第间发生的隐私,都是刻板生活中极好的“调料”。等到卖豆芽的陕西籍小贩来了,就抓几个钱的豆芽摊在茶桌上一根根细细撷着,也不耽搁交谈。
吃过早饭,又上原先的茶馆,照例地说:“换一碗!”或者:“茶钱这拿去!”茶堂渐渐坐满,茶桌边的各种交际、闲谈便更加热闹。茶馆营业繁忙,卖茶还带供应出堂开水、纸烟、水烟,利用吊堂炉火的空档代客煎药、煮饭、炖肉。提了茶壶的堂倌,吆喝着穿堂而过,熟练地“表演”续水入碗、点滴不溅的技巧。
茶客们开始赌牌。一般茶馆打两串底的小麻将,偶尔有人团足一场五分一角的赌局,就会传布开去,成为新闻:“××店里今天打银角子哩!”普通是打纸牌,有的“扯招”,有的“打点点红”,或者“挑麻雀”,各有各的玩法。大部分人站在牌客后面当“背光”,出起主意来比当事人还要热心。
十字口这样子的茶馆还有“唐摸王”开的唐家茶馆。本地语瞎子叫“摸人”。摸而成王,可见这个老板的精明厉害①。萧清淼开的是萧家茶馆。萧很善于巴结有钱有势的人,所以,大家授他一个绰号“金眼鸽子”。一个二三百户人家的镇子,拥有这么二、三十个茶馆,在四川真是平平常常。
成年的杨朝熙后来用“尹光”的名字写过一篇散文,描写家乡人们喝茶的情景,其中说: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馆,恐怕就是人们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见过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慢慢酸化着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种嗜好,一种分解不开的宠幸,好像鸦片烟瘾一样。①文章写于三十年代,由茶馆这个“窗口”看出故乡社会消蚀生命的封建性质。当然,这不可能是童年的他所能具有的眼光。不过,儿时的朝熙,也已经能够粗粗分辨县城内不同地位的人所上的茶馆是很不相同的了。
南门外的半边茶铺,是轿夫、挑案、游民们的天地。镇里的华泰店是个行业茶馆,天天聚在此地的是专做青山(木材)生意的行商。他们在这里交流行情,会友应酬,拉客成交。商人们管到这儿来喝茶,叫“上市”。
最讲究的茶馆是大南街的益园,是本地哥老会的“码头”。以后又是安县西南乡自治局所在地。杨家的河清便属于西南乡。益园堂口大,坐场好,一色红油漆的茶桌茶椅,成都的新型式样。这是与朝熙家相熟的詹举人的儿子詹西白开的。詹在省府读过书,拉得一手好胡琴。袍哥茶馆汇集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可以谈公事,喝讲茶,设赌局(赌的输赢就比较大了),也可以进行金银、鸦片、枪支的交易。这是童年朝熙常来的一个地方。
(世界被什么力量分成了各个部分。你从小身处茶馆社会一定早早感到人间的等级森严了吧?我慢慢直觉到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东西在操纵。不过无论欺侮人的与被欺侮的,都可在各自的茶馆登场表演)茶馆的门口围着各种吃食担子。卖抄手(馄饨)、醪糟蛋、担担面、凉粉,一招呼便殷勤送上。这些小贩往往几代人干这个营生,生于斯,长于斯,彼此十分熟识。朝熙自小看惯的小贩有陈麻子,是个卖糖饼的。他捏的糖人,戏里的人物、城隍庙的鸡脚神、关二爷,都活龙活现。孩子们总是把他的摊子围得满满的。四川每一地的小吃,都冠以某一手艺人的姓氏,成为本地特产,安县也不例外。朝熙小时候最爱吃的是“朱凉粉”,“陈油茶”,“尹汤元”。南街上一爿刘家豆花店,小菜、豆腐都做得好。刘家的老大懂点文墨,还会在店堂挂上手画的灯笼。南门外的米粉店更有名,有人为了吃早上头一茬的细粉,往往在城门未开之前,就从门洞里将碗递出去托城外的熟人代买。
一入夜,满城的人仿佛都到十字口和大南街来闲逛。这是小城一天散漫生活的余兴,劳作完后的总休憩。大人小孩随走,随谈,随吃,悠哉游哉。杨朝熙也会央朱奶妈陪他上街,夹杂其中。这时的街道两旁,担子上燃着方形的油灯、蜡烛灯,点点光影照着烧腊摊子上各种卤味。孩子们吵着买一叶鸭翅或一串鸡肫,吃得喷香。大人则进酒铺吃喝,还可站在柜台边从小贩手里买点花生米下酒,俗称“吃木脑壳酒”,便是《红石滩》开头写的刘家烧房门前的吃法。(我一生都嗜吃。爱喝酒,下酒菜最好是黄鳝、鲢鱼。安县有一种无鳞的沙勾鱼,味道奇美。我有个亲戚写文章,把“沙汀”的由来说成是我爱吃沙勾鱼,这当然是错的。但我爱吃这种鱼不假。我后来特别爱吃牛肉。成都的“邓牛肉”很有名气。我在省城读书,曾经把绵竹的酒带一笼去上学,你信不信?——沙汀1986年12月10日讲)
在沉闷单调的山城生活里,仅有的一点文化娱乐也离不开茶馆。益园晚间的“摆围鼓”(川戏清唱),那高亢的音调使朝熙入迷。后来,他学过“围鼓”,会哼几句黑头,唱的是《夜奔》、《杨文昭》之类。母亲怕他小小年纪把身子唱坏,才叫他放下了。但从此种下他对川戏的终生喜爱。
他还常常溜到半边茶铺那里去听打金钱板、竹琴,听《七侠五义》、《济公传》。在烟馆积垢厚腻的门帘外面,常有行脚和尚背了韦陀像,道士背了灵官像,在唱“善书”。还有讲“圣谕”的,入夜在茶馆搭个台子,又说又唱,都是一本一本的历史传奇。
“讲圣谕”的名称来于帝制时代。那时候说唱的人要在台上挂个牌子,上书“圣谕”两字。讲前先读“圣谕”十六条,挂上一个为皇帝教化下方的名义。实际讲起来异常生动。老婆婆拄个棍棍都要来听,一听就哭。因为讲的都是曲折的故事,人物只有对话、动作,没有多余的描述,一般老百姓都能听懂。这种民间叙述形式是朝熙从童年便谙熟了的。全城能讲“圣谕”的是其貌不扬的李裁缝,生得矮矮的,络腮胡子,鼻梁上架一副黑线做耳绊的老花眼镜。看人的时候,总爱从黑牛骨的镜框上沿投出视线。你想象不出他能发出如此圆润优美的音调,赚得许多心慈面软人的眼泪,也惹得有人笑骂道:“这鬼儿,要是不看模样倒麻人哩!”后来,城里一个当过女校稽查的矮胖油黑的孀妇,也讲“圣谕”。一讲,几个浮浪子弟就在台下说野话。半夜还去敲门请她陪酒。所以,不上三天就收了摊子,留下了一则趣闻。这种娱乐到清王朝崩溃后便渐渐衰微,与现代的说书合流了。
朝熙还时常缠住朱大娘去看戏。全城唱戏主要在离他家不远的灵官楼。这个楼在面对东门城楼的一座山梁上,两层,全部用上好的石条砌成,相当精巧。楼的下层有三间房子,一间住看守的老道士,另两间是做花炮的炮房。除春节期间供应各色爆竹外,还可以自己拿材料定做各种竹筒大礼花,正月里耍龙灯狮子,好做配套的焰火。是朝熙很向往的一个地方。
本城人认为灵官可以镇邪,庙里香火于是不绝。同时,在灵官楼下面靠近城墙的坝子上搭起台子,终年唱戏。闲散的乡镇总有那么多热心看戏的市民,不是幻影戏,便是最吸引朝熙这些孩子们的木偶戏。木偶戏是福建人引进的文化,被称为“木脑壳戏”。有个姓蒋的班主便叫做“蒋木脑壳”,是个亲切的称呼。
到了每年正月初九的“上九会”,是安县的大节日。寺庙里念皇经,讲“圣谕”,善男信女带上供品进香,吃斋饭,求得菩萨保佑新的一年无病无灾。这是除夕和“大破五”(元宵节)之间最火红的一天,灵官庙的广场上必定有川戏班的大戏在喝。人头攒动中,总有那个闻名全城的妓女,诨名“小把戏”的,浓妆艳抹地在看戏,惹得许多观众的视线都盯在她身上。她后来被大粮户陈天藻,外号“小霸王”的独占。这个心狠手辣的袍哥,为了有人还敢跑去与“小把戏”叙旧,便把这女人一枪打死。比起这个妓女来,西门外河滩草棚子里专门应酬苦力、船夫的下等流娼,境遇就更惨了。(你从小就知道男女之事?看得多了,就模模糊糊懂得。我很少写女性,但同情这些女人。没有童年的记忆,《一个秋天晚上》里的流娼,我写来笔端不会带有那么多的感情)
米市坝每年阴历五月初十城隍生日,也演大戏。这是从十字口经北街福音教堂,到达北门内,在城隍庙和黄州馆之间的一块空地。平日为交易粮食的集市,总能见一些老女人手执扫把,把撒落在地的米粒连同沙子一起扫进她们的撮箕里。城隍生日向例演连本的“目莲救母”。最后的高潮是飞叉,在人后面置木板,上下左右被飞来的叉子插满。这是朝熙最爱看,也最怕看的一幕,时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