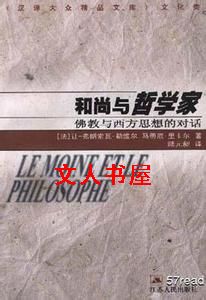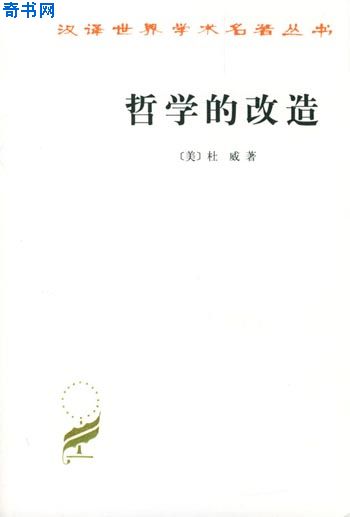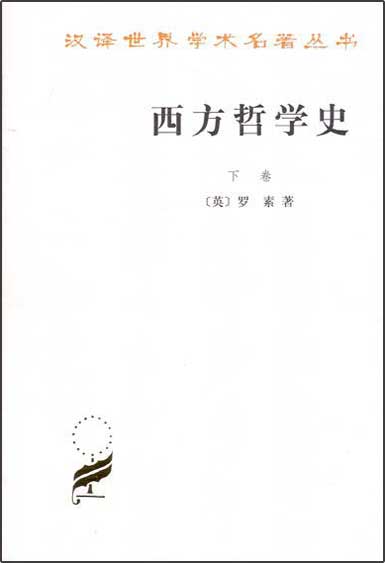西方哲学初步-第4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蒙蔽着凡人的眼睛。
…… 256
252西方哲学初步
在科学沉默的地方,哲学便发话了:“世界是我的意志”。
力也是意志,物体间的相互吸引与排斥、化合与分解,都属于意志。一株小草在岩石缝中挤出来向着太阳生长,这是意志,虎的凶猛,狐的狡猾,鹰的搏击,兔的迅捷,这一切都是意志。人也是意志,牙齿、食道与肠乃是客体化的饥饿意志,生殖器乃是客体化的性欲意志。世间万物从无机界最简单的力到有机界中最复杂的人,都是意志的客体化。意志的客体化有一定的级别,意志客体化最低的一级表现为最普遍的自然力,这种自然力显现于每一种物质中,在意志客体化较高级别里我们会看到显著个性的出现,尤其在人身上,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理念,与人类的距离越远,个性特征的痕迹就越消失,到了植物,除了从土壤、气候及其他偶然性的影响得以充分说明的那些特殊属性外,已没有什么其他个性了,而在无机的自然界,一切个性都消失无余了。
我们生活的世界彻头彻尾是意志的世界,岂有他哉!
意志是第一性的、本原性的东西,传统哲学中倍受推崇的理性、认识只不过是意志客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才1岁的鸟儿并没有什么蛋的表象,但它却会为那些蛋而筑巢,年幼的蜘蛛也没有俘获品的表象,但它会为这些俘获品结网,昆虫也没有什么预见能力,但它总是把蛋下在未来幼虫将能找到食物的地方。因此意志没有认识也照样活动,尽管它是在盲目地活动。认识不过是个体为维持生存和传种接代的一种辅助工具而已,它是为意志服务的,在人有任何认识之先,人已是他自己意志的创造物了,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以“照
…… 257
西方哲学初步352
明“这创造物的,人并不是”要他所认识的东西“
,而是“认。
识他所要的东西“。
意志就像是没有眼睛的瞎子,而认识则似。
不会走路的瘸子,认识的作用就是给意志指路,它命定是为意志服务的。
那么意志是什么呢?
意志即生存,即延续自己的生命。一粒干瘪的种子在坟墓中沉睡了几千年后,甚至仍能生芽长叶,生命诚可贵。人之所以怕死,并不是死亡之中有什么痛苦的东西无法让人忍受,实际上很多人正是为了逃避痛苦而甘愿自杀的。在死亡之前,我还活着,死亡与我无关;在死亡之后,我已不在,死亡仍与我无关。但人们的的确确在怕死,怕死实际上怕的是个体的毁灭,所以才有好死不如懒活的说法。
然而,人总有一死,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为了战胜死亡,意志便发明了生殖,不,意志即是生殖。生殖是有机体最强烈的本能和最后的目的与目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机体的成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生殖的成熟,植物成熟了便要开花授粉,动物成熟了便开始交配,人成熟了则要结婚。
雄蜘蛛在与雌蜘蛛交配后即甘愿被对方吃掉,再凶猛的动物对待自己的子女都是温驯的,虎毒不食子,这一切都是为了繁殖后代。人世间的爱情实际上也是在为大自然的生殖意志服务,每一个人都在寻觅一个能弥补自己缺陷的配偶,为的是这些缺陷以后不再遗传到下一代,虚弱的男子会去寻找健壮的女子,佳人配才子为的是郎才女貌的互补。为什么青春是美的?这与其说是由于娇嫩的脸蛋,还不如说是她(他)还处在生殖阶段,生殖意志的狡计是大自然舞台后的隐身的导
…… 258
452西方哲学初步
演。
意志即欲求的意志,生殖欲毕竟也是一种欲求。欲求是没有目的,没有止境的,植物为什么要开花?苍蝇为什么要飞来飞去?人为什么要忙忙碌碌?不为什么。植物从种子经过根、干、枝、叶到达花和果,这果又是新种子的开端,一个新个体的开端,这个新个体又要按老一套重演一遍,动物、人类莫不如此。永远的变化、无尽的流动乃是意志的本质表现,欲壑难填是意志的本质要求,一个欲望满足了,新的欲望便产生了,饥寒求饱暖,饱暖却又求淫欲,永无了期。从欲望的满足到新欲望的产生这个永不停止的过程,如果转得快,那就叫“快乐”
;如果转得慢,那就叫“痛苦”
;如果停滞不前,那就叫空虚无聊。
欲求在有认识把它照亮的时候,总能知道它在欲求什么,求名,求利,但决不知道它根本欲求什么,名利皆空。
不过,在叔本华看来快乐压根就不是正面的东西,因为欲求的满足总不会持久,一个欲求满足了,一个更大的欲求又来了,原来一切痛苦始终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未曾满足的和被阻挠的欲求,消除痛苦的努力除了改变痛苦的形态外,再也没有什么可做了。性欲、狂热的爱情、嫉妒、情敌、仇恨、恐惧、好名、爱财、疾病……一连串的痛苦接踵而来,“任何一部生活史也就是痛苦史”
,任何欲求的满足如财富、名利等等所带来的暂短快乐只不过是挡开痛苦而已,直到我们失去了这些东西,我们才感觉到这些东西的价值,因此有时候回忆我们克服了困窘、疾病、缺陷等等也能使我们愉快,病后方知健康之重要,“忆苦思甜”的道理也在这里,眼看别人的
…… 259
西方哲学初步552
痛苦的景象或耳听叙述别人的痛苦,也正是在这条路线上给我们满足,当然这已接近幸灾乐祸的恶毒了。鲁迅先生曾对国人围观杀人的场面颇为痛心,其实西方人也不例外,看到别人被杀,或许会让人意识到自己还幸运地活着,这多少对他空虚的心灵是一种安慰。如果真有一天人的所有欲求都得到了满足,痛苦就会穿上无名的烦恼和空虚无聊那件令人生愁的“灰褂子”而来,人们又得想办法来撵走无聊,这使像人这样并不怎么互爱的生物居然也那么急切地相互追求,于是它又成了人们爱社交的源泉了。
“困乏是平民群众的日常灾难,与此相似,空虚无聊就是上层社会的日常灾难。在市民生活中,星期日代表空虚无聊,六个工作日则代表困乏。”即令人们真的把无聊撵走了,结果原先痛苦的形态又会从头开始跳起原来的舞步。人生犹如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来摆去。但丁写他的《地狱》若不是取材于我们的现实世界,还到哪儿去取材呢?与此相反,在但丁着手来描写天堂及欢乐时,不可克服的困难横亘在他面前了,因为这个世界恰恰不能为他提供一丁点材料。喜剧的写作者指挥着他的主人公通过千百种困难与危险达到目的,一达到目标就赶快降下了帷幕,不然还有什么好演呢?
人生是一场悲剧,未实现的愿望,虚掷了的挣扎,受挫的努力,失意与背运,痛苦与无聊,最后以死亡收场;当然这其中也有些喜剧的插曲,一日间的营营苟苟与辛苦劳顿,一刻间的别扭淘气,每小时的岔子,偶而的戏弄人的场合,就都是些喜剧镜头。
“命运就好像是在我们一生的痛苦之上还要加以嘲笑似的,我们的生命已必然含有悲剧的一切创痛,可是我们同时还不能以悲剧人物的尊严
…… 260
652西方哲学初步
自许,而不得不在生活的广泛细节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委琐的喜剧角色。“
人类不要抱怨大自然的不公,痛苦决不是人世间专有的现象,世界作为意志本已是一痛苦的世界,意志客体化的每一级别都在和另一级别争夺着物质、空间与时间、物种之间为生存而展开倾轧、争斗、角逐、冲突,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则在黄雀之后,而人对人是狼,生存意志到处吞噬着它自己,以各自不同形式作为本身的营养。
当然,只有在人身上痛苦才达到了巅峰。因为意识现象越明显,痛苦就越明显。
一般认为无机物和植物没有感觉,尽管诗人能感受到花在流泪、月在惆怅,最低动物如毛虫类只能感觉到很小程度的疼痛……随着知识的发达,意识的上升,痛苦也就跟着增加。同理,一个人的智力越高,认识越明确,他的痛苦就越大,天才是最痛苦的人,“谁在知识上增加了,谁就在痛苦上增加了。”
人世间的很多痛苦大多不是实际的现在而是抽象的思虑,往往是这思虑才是最难以忍受的东西,人们在精神上极度痛苦的时候要扯一下自己的头发,捶脑抓脸,甚至在地上打滚,这一切无非是让精神上的痛苦转移到肉体的痛苦上来,用以驱散一个觉得难以忍受的思想。
因此,意志作为人的本质六性就是自我肯定的,每个人都在肯定自己的意志,利己主义是每个生物个体的本性。每个个体尽管它在无边际的世界里十分渺小,小到近于零,却仍然要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它总是把其他个体当作表象而感知,它自己的本质及其保存就要放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对于自己的死,人人都视为世界的末日似的,对于那些熟人的
…… 261
西方哲学初步752
死,他只不过当作一件满不相干的事听听罢了。
什么是善?
客体对意志的某一固定要求的相适性就是善;当意志的肯定超出了自身的范围强制别人身体中的力量为自己意志服务而不为在别人身体中显现的意志服务,这就叫做“非义”
;如果一个个体在肯定他自己的意志时,竟至于侵入我本人作为一个人格的人在本质上具有的意志肯定的范围,并以此否定我意志的肯定,那么我抵抗这种侵犯即否定这一否定,这就是正。
义;一个人在肯定自己的意志时,又决不走向否定在另一个。
体中显现的意志,这就是公道……然而良善之辈生存多艰,非。。
法之徒逍遥自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天地良心,公道何在?
殊不知这一切只是摩耶之幕,只是在主体的时间、空间、因果性形式下产生的表象,是个体化原理中的现象,世界所包含的一切有限性、一切痛苦、一切烦恼都出自于生命意志的不同表现而已,每一生物体根本都是以最严格的公平合理在担负着一般的生存,族类的生存和它特有的个体的生存,凡是在它身上发生的,凡能够在它身上发生的,对于它都是活该的、公平的,意志是怎样的这世界也就是怎样的,这乃是“永恒的公道”
,“世界本身就是世界法庭”
,岂有他哉!
一且人们揭开摩耶之幕,纵身大化之中,他就会领悟到人世间的悲欢离会,恩恩怨怨,物种间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原不过是同一意志的不同显现而已!岂有他哉!
那么如何才能透过摩耶之幕,纵身大化中,不喜亦不忧呢?
艺术当然是一种解脱之道。在艺术中,主体放弃了对事物的习惯看法,人们不再问事物的“何处”
、“何时、”何以“
、
…… 262
852西方哲学初步
“何用”
,而仅仅沉浸于直观的“什么”
,主体完全摆脱了对意志一切关系,而成为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