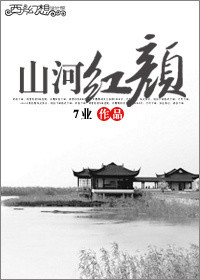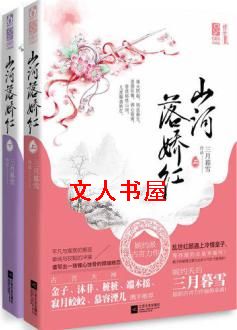静静的顿河-第27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葛利高里默不作声。他点上烟。贪婪地一连使劲抽了几口,他的头有点儿晕了,恶心得要命,最近这一个月他吃得不好,直到现在他才感觉到,这些日子他竞衰弱得这么厉害。他灭了香烟,拼命吃起东西来。福明简单地把暴动经过和在地区内流窜的初期情况谈了谈,还把自己流窜誉为“进军”。葛利高里默默地听着福明的谈话,几乎连嚼也不嚼地把面包和烤得很不好的肥羊肉吞下肚子。
“在人家作客饿瘦啦,”福明好心肠地开玩笑说。
葛利高里打着饱嗝儿嘟哝说:“我又不是住在丈母娘家里。”
“一点儿也不错。你放开肚子吃吧,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们可不是吝啬鬼。”
“谢谢啦。现在该抽口烟……”葛利高里接过递给他的香烟,走到放在板凳上的一只铁锅前面,操起木碗,舀了一碗水。水凉丝丝的,还带点儿咸味儿。吃得舒舒服服的葛利高里贪婪地喝了两大碗,然后津津有味地抽起烟来。
“哥萨克并不十分欢迎我们,”福明坐到葛利高里身旁,继续说:“去年暴动的时候都把他们吓坏啦……不过志愿兵还是有的。已经有四十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过我们期望的不仅仅是这一点儿。我们要把全区发动起来,甚至叫邻近各区——霍尔奥尔斯克和梅德维季河口区也来帮助我们;到那时候我们再来跟苏维埃政权倾心地谈谈!”
桌于周围是一片热闹的谈话声。葛利高里一面听福明说,一面偷偷地打量着他的同谋者。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他一直还不相信福明的话,以为福明是在耍花招,为了小心起见,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总不开口也不像话。
“福明同志,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那么你们想干什么?想发动新的战争吗?”
他竭力驱赶着向他袭来的睡意,问。
“这我已经对你谈过啦。”
“要改换政权吗?”
“是的。”
“那么你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呢!”
“建立哥萨克自己的政权!”
“首领政权?”
“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我们以后再说。老百姓选择什么样的政权,我们就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不过这种事还不是很快就能办到的,而且我对政治问题也是个外行。我是个军人,我于的事情就是消灭那些委员和共产党员,至于有关政权的问题,我的参谋长长帕林会跟你谈的一他是我这方面的专家,此人很有头脑。学问很大。”福明把身于侧向葛利高里小声说:“原沙皇军队的上尉。是个聪明小伙子!他正在内室里睡觉呢,生了点儿小病,大概是因为不习惯这种生活:我们行军的路程总是很远的。”
门廊里传来一阵喧哗和脚步的杂沓声,呻吟声,克制的活动和压低的叫喊声:“给他点儿厉害的!”桌边的谈话顿时停止了、福明警惕地朝屋门看了看。有人猛然地把门推开。一团白色的雾气贴着地面涌进了屋于。一个身材高大、没戴帽于。
穿着保护色棉袄、灰色毡靴子的人,由于背上啪地挨了一下子,所以倾身向前,跌跌撞撞地跑了几步,然后肩膀猛地撞在壁炉台上。(无_…_名*小说…*网…W M T X T。C O M整*理*提*供)在门关立以前,有人在门廊里兴高采烈地叫喊:“请你们再收下一个吧!”
福明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扎在军便服!“的皮带,”你是什么人?“他威风凛凛地问。
穿棉袄的人大喘着气,用手摸了摸头发,想要活动活动肩胛骨,但是疼得被起了眉头。他的脊梁骨被什么沉重的东西——大概是枪托子——打了一下子。
“你为什么不说话?舌头割掉啦?你是什么人,我问你哪?”
“红军战士。”
“哪个部队!”
“第十二征粮团,”
“啊啊,这可太难得啦!”坐在桌边的一个人笑着说。
福明继续审问:“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是拦截部队……派我们来……”
“明白啦,你们有多少人在这个村子里?”
“十四个人。”
“其余的人在哪儿?”
红军不做声了,使劲张开嘴唇。他喉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咯咯地响,一条细细的血流从左边嘴角流到下巴上。他用手擦了擦嘴唇,看了看手掌,然后往裤子上擦了擦。
“这个坏蛋……你们的……”他咯咯地往下咽着血,嗓子里咕噜咕噜响着说,“把我的肺打坏啦……”
“别害怕!我们会给你治好的!”一个矮小的哥萨克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朝其余的人挤挤眼睛,玩笑说。
“其余的人在哪儿?”福明又问。
“护送车辆去叶兰斯克啦。”
“你是哪儿来的?什么地方的人?”
红军战士用像发疟疾似的闪光的蓝眼睛看了福明一眼,把一团血块吐在脚下,用已经是响亮的低音回答说:“普斯科夫省。”
“普斯科夫人,莫斯科人……我们见识过这些人……”福明嘲笑说,“小伙子,你为抢别人的粮食跑得太远啦……好啦,谈话完毕!我们怎么处置你呢,啊?”
“应该放掉我。”
“你真是个天真的小伙子……也许咱们真该放掉他吧,弟兄们?你们觉得怎样?”
福明的胡子里闪着笑容,转过脸朝桌子旁边的人们问。
仔细观察着全部经过的葛利高里看到那些被风吹成褐色的脸上露出了矜持、会心的笑意。
“叫他在咱们这儿子上两个月,然后就放他回家去看老婆,”一个福明分子说。
“也许,你真可以在我们这儿子吧!”福明竭力掩饰着笑容,问。“我们给你马、马鞍子、新高筒皮靴——换下你的毡靴子来……你们的长官对你们的服装大不关心啦。难道这叫鞋吗?已经化冻啦,你却还穿着毡靴子。参加我们的队伍吧,啊!”
“他是个庄稼佬,从出娘胎就没有骑过马,”一个哥萨克装疯卖傻地故意尖声说。
红军战士默不作声。他脊背靠在炉炕上,用已经炯炯有神、明快的眼睛打量着大家。他偶尔疼得皱皱眉头,呼吸困难的时候,就微微地张开嘴。
“你是留在我们这儿,还是怎么的?”福明又问。
“你们是些什么人呀?”
“我们吗?”福明高高地把眉毛往上一挑,手摸着胡子说。“我们是为劳动人民而战的战士,我们反对委员们和共产党员们的压迫,你看,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这时葛利高里忽然在红军的脸上看到了笑容。
“原来你们是些这样的人……可是我还在想,这是些什么人呢?”俘虏露出沾着血的牙齿笑着,仿佛是因为听到这么新奇的事儿使他感到高兴、惊讶,但是他的话音里带着一种使大家都不由地警惕起来的声调儿。“照你们的说法,是为人民而战的战士,是吗?是这样。可是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上匪而已。要我给你们干?哼,你们可真会开玩笑!”
“你也是一个很有风趣的小伙子嘛,我看你……”福明眯缝起眼睛,简短地问,“是共产党员吧!”
“不是,您怎么啦!我是个非党的战士。”
“不像。”
“真的,是个非党的战士!”
福明咳嗽了一声,转身朝着桌于喊。
“丘马科夫!把他干掉。”
“你们杀死我毫无意义。你们没有理由杀我,”红军战士低声说。
大家都没有说话。丘马科夫是个短粗的漂亮哥萨克,穿着一件英国皮背心,他不高兴地从桌边站起来,理了理向后流得很平整的棕红色的头发。
“这种差事我已经干烦啦,”他从堆在板凳上的马刀堆里抽出自己的马刀,用大拇指试着刀刃,兴奋地说,“你不一定亲自动手嘛。跟院子里的弟兄们说一声就行啦,”福明建议说。
丘马科夫冷冷地把红军战士从脚到头看了一遍,命令说:“你在前头走,亲爱的。”
红军战士离开了炉炕,背微驼,慢吞吞地往门口走去,地板上留下了些湿漉漉的毡靴印。
“进来的时候——也应该擦擦脚嘛!来了一趟,给我们这儿留下些脚印,弄得这样脏……看你有多邋遢,老弟!”立马科夫跟在俘虏后面走出去,故意装得很不高兴地说。
“告诉弟兄们,把他带到胡同里,或者场院上去。不要就在房子旁边干,不然主人们会埋怨的!”福明在他身后喊道。
福明走到葛利高里跟前,坐到他旁边说:“我们审问得快吧?”
“快,”葛利高里避开他的目光,回答说。
福明叹了日气。
“什么记录也用不着;现在就应该这样。”他还想说些什么,但是外面台阶上响起了一阵急剧的脚步声,有人喊叫,又传来一响清脆的单枪射击声。
“妈的,他们在搞些什么鬼名堂?”福明生气地大声说。
一个坐在桌边的人跳了起来,用脚踢开了门。
“怎么回事!”他朝着黑暗里喊道。
丘马科夫走了进来,兴奋地说:“居然是个很机灵的家伙!鬼东西!他从台阶上一跃而下,撒腿就跑。浪费了一颗子弹。无_…_名*小说…*网…W M T X T。C O M整*理*提*供弟兄们在结果他……”
“命令他们把这家伙从院子里拖到胡同里去。”
“我已经吩咐过啦,雅科夫。叶菲莫维奇。”
屋子里寂静了片刻。后来有人抑制着呵欠,问道:“丘马科夫,天气怎么样?
还不晴吗?“
“还有点儿阴。”
“如果下一阵雨,就可以把残雪化光啦。”
“你要下雨干什么!”
“我倒不要下雨。不过我不愿意在烂泥地里走啦。”
葛利高里走到床前,拿起自己的皮帽子。
“你到哪儿去!”福明问“出去清醒清醒。”
葛利高里来到台阶上。从黑云里面钻出来的月亮洒下淡淡的白光。宽大的院于、板棚顶子、像金字塔似的高耸人云的光秃秃的杨树顶盖、披着马衣站在拴马桩旁边的马匹——这一切都笼罩在一层透明的午夜的蓝光中。离台阶几沙绳远的地方,被砍死的红军士兵躺在那里,脑袋浸在闪着暗淡光辉的融雪的水洼里。有三个哥萨克正躬身在死人的身上,低声谈论着。不知道他们在死人旁边干些什么。
“他还喘气哪,真的!”一个哥萨克生气地说。“笨东西,你这是怎么搞的?
对你说过——要往脑袋上砍,唉,你这个半瓶醋!“
押送葛利高里的那个哥萨克声音沙哑地回答说:“快死啦!再折腾一会儿。就会死的……你倒是把他的脑袋扳起来呀!怎么也脱不下来。攥着头发往上抬,这就对啦。喂,现在扶住他。”
哗啦一声水响。一个弯腰站在死人旁边的人挺直了身于。那个声音沙哑的哥萨克,嘴里哼哼着,在剥死人身上的棉袄。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的手太软,所以他没有立刻死掉。从前,有一回我在家里动手宰猪……扶好啦,别松手时!哦,见鬼……是的,有一回,我动手宰猪,把它的整个喉咙管部割断啦,一直刺到了心口,可是这个该死的东西站了起来,在院于里跑起来啦。跑了好半天!浑身是血,可是还是在跑,嗷嗷直叫。它已经没有法子喘气啦,可是它还活着一这就是说我的手太软啦。好啦,松手吧……还在喘气儿?请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几乎把他脖子上的大骨头都砍断啦……”
第三个哥萨克张开两手,把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