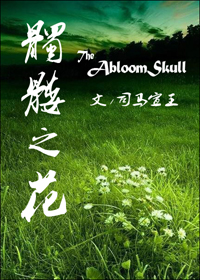髑髅之花-第1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心相爱,她本就应该属于你。”说得轻巧啊,飘飘忽忽,除了五六岁的小孩没人会信,当时他第一反应还真以为这是场处心积虑的试探。“我依然爱她,但忠诚在上,私心无足挂齿。”他重复了一遍给吉耶梅茨的回答,“即使她会成为茹丹全族、而非我一人的女王,即使她会有自己的驭主,我仍将永远忠于她,并且爱她。”
“跟我就别废话了。”伊叙拉说,“还没到那地步。她可以‘选择’你。”
被她选择之人……
“婚姻是茹丹女性与神明沟通的仪式,尤其是位居全族之尊的妃主,就算生父也不能妨碍她们决定谁将成为自己唯一的正式配偶。只因为驭主一职相当于我族的最高军事统帅,所以将军才特别在意下一任的人选。”伊叙拉摸摸鼻子,“实话说若换了我……才不想被那东西捆住啦。我是舍阑人的杂种,他们肯定宁愿认一个受信任的西方人也不愿认我,反正之前也不是没有异族驭主的先例。我呢等一切结束只想渡海向东,回自己的故乡中洲看看,女人啊家庭什么的都是负担……别犹豫了,跟她开口就行。婆婆妈妈像外表一样娘们,这可不是你呀。”
海因里希怔了怔。这是他唯一一次在伊叙拉面前露出此种表情。
“不用了。”他说。
伊叙拉玩世不恭地飞舞着的眉沉敛下来。
“吉耶梅茨将军救过我的命,并提携我直到如今。我已经立誓,对他的忠诚将延续到下一代,即使他在我之前身故,我仍会效忠他的女儿,以及她自己所选择的丈夫。”白舍阑人戴上头盔,从铁面幕后传出的声音闷钝厚实,唯有他的双眼明亮。“如果那人是你,我将庆幸此誓不枉。”
那时他们还是战友,兄弟,第四军统帅的左右两臂,一张坚盾的正面与反面。
“多谢。”海因里希微笑,“但是不用了。”
伊叙拉什么也不懂。
他竟然相信达姬雅娜真的爱他。
……“选那家伙登上神坛,是因为实在缺乏替代品。”又一杯酒泼洒在地,像在为那两个都已在对方心中死去的故友祭奠。“必须续上民众信仰的火种,不管这火实际有多微弱并随时可能熄灭……宗座也只有他十几年来惯长的老戏法可以玩了。让摩根索担任侍卫长,不光是把他放在更容易露出破绽的位置,最重要的是为麻痹我。他不会让摇摇欲坠的圣廷再遭受丝毫置疑,在除掉我之前,必先将众人的视线转到别处,以散尽我的光辉……他给了我等死的时间。不过要让长久被戏弄的猴子认清他们敬拜的英雄只是提线木偶,这时间也足够了吧?”
“你希望他们醒来?”冷不丁地,阿玛刻问。
“活得浑浑噩噩,或清清白白,都是他们的事。”海因里希咳了两声,伤势大体已痊愈,毒质也差不多被拔除,但多少仍有些虚弱。“我只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座城市就快要倒塌了。”阿玛刻举起手中提灯。两人所在的巨大墓园空荡如也,不远处城墙和高塔的黑影像刚吞吃完死尸的卧伏怪兽。“它白日里看上去像复活过,可那只是假象。得到这样一片废墟,对你有什么意义?”
“你问过我。”
“但你从未告诉我答案。”
海因里希蹲下身,将酒具埋在刻着吉耶梅茨名字的墓碑下,用剑拨盖上泥土。他掖紧斗篷。雷声隐然滚过难以看穿的天幕,空气沉压,那是即将有一道光华破开夜色的征兆。
“该道别了,阿玛刻。”他说,“小心你背后紧盯的眼睛。为安全起见,我不会再来找你,除非我得到了云缇亚确切地死亡或还活着的证据。”
“这个时候还有谁能救你活命?”
“我想去赌一次。”
阿玛刻吹熄了灯火。黑暗中只听她在冷笑。
海因里希也轻轻地笑了。“——不吻我吗?下次你见到的说不定就是我的尸体。”
她的手臂挽过来,搭住他肩膀。她身高与他相差无几,因此很容易就贴近他耳侧,令他听见的话语也掺进些许热气。“回答我最初的问题。这样彼此都没有遗憾了。”
“我从未想过要得到这个国家,因为我从未爱过它。我也从未想过要毁灭这个国家,因为我从未恨过它。我的欲望很大却又无比渺小,深不见底但其实轻易即可填满,而且并不以我的死亡为中断。我要走的路途还遥远漫长,但我已留下的足印,唯有历史本身才能洗灭。”
阿玛刻松开手。
“你我果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狗男女,”她低声补充,“都这么……愚不可及。”
脚步声渐渐泯入黑夜。海因里希独自站在墓园围栏前,闪电将他面孔照得苍白。一辆漆黑车篷的马车轧轧地驶过来,驭手摘下兜帽,是他的年轻侍从。“如您吩咐,大人,绕城区穿了几个大圈,再厉害的眼线也该被甩脱了。”
海因里希坐进车厢。“去第四军的兵营。”
侍从讶然转头:“您……确定?听说伊叙拉将军……”
“他和我之间有点小误会,不过无所谓。”那男人笨拙地笑着的脸,一本正经的脸,愤怒咆哮的脸,交织重叠,他有点惋惜自己没能亲见那张脸在今日的万众呼声中会有怎样神情。伊叙拉。曾几何时还是熟悉到令他不屑多看一眼的人。“他没理由把我拒之门外。今天这个日子特别。”
“这太……太冒险了。”侍从吞咽了几口空气,“不管怎么说,您上次的伤……”
“你想活下去吗?”
还不够。
我留给这个世界的足迹还远远不够。
“为了生存,”海因里希微笑,拉上车帘,“就暂且对我们将被他人之手扭转的命运屈膝吧。”
雨水倾盆,击打车篷犹如鼓捶。上空黑幕闭锁,不漏一丝光。车辕前悬挂的提灯时明时晦,马匹虽然驰行迅疾,却也冲不破这风雨交加的夜色,
“那位大人!”一个不适时宜的幼嫩嗓音透过风声雨声,“那位马车里的大人!”
侍从原本打算加抽一鞭快速驶过,海因里希制止了他。不是寻常街头追着喊的卖杂货小童,倒像早已在这久候。“您认识从前的宗座侍卫长海因里希吗?”孩子披着油布,“有位姐姐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他。”
“为什么找上我?”车厢里的人平静地说。
“您的马我见过,给老圣裁官拉车,可威风呢。您现下是在海因里希大人的地方工作吧?拜托了哟。”
小小的身影眨眼消失在雨里。海因里希看着驾车的马,并非审判局官员仪礼专用,事实上他有意牵了两匹毫无特色、稀松平常的灰马,就是为避免监视者认出——然而展开那字条的同时,脸上心领神会的讥诮瞬间隐没。“大人?”侍从问。
“一个我必须赶赴的邀约。”海因里希将信塞进灯罩,火光炽盛了一刹那。“就算是陷阱也没办法。把车停在最近的巡守岗哨旁边,在那等我,小心别教人有机可乘。假若天亮还不见我回来……”
“……不。”顿了顿,他说,“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
黢黑的巷道错综如蛛网。风大力摇晃着头顶写有异族文字的破旧门牌,海因里希心知这曾是茹丹人聚居的区域。暴乱对这里的摧残尚未修复,烧焦的断壁随处可见,梁木从房屋残骸中伸出它炭化的遗骨。他照信上所说的绕过两座废屋,腐朽的窗页吱呀呀像乌鸦鸣叫。低身走入一条狭窄过道,拾级而上,叩响最里面的一扇门,却发现门仅仅虚掩,此时应手即开。仿佛迎接一位阔别已久的主人归来。
坐在小几旁的女子回过头。
她依然美丽。多年以前,他这样推开她书房的门,时间薄而旧黄,成了他面前撕下的一张纸页。
他并未想过还能再拾起它。
“达姬雅娜。”
相同的火焰跳动在他手中灯盏与她身边烛台。他忽然想一步冲过去,尽管这个无由之念随即也如其产生一般迅疾地消失。斗篷湿透,脚下积了一滩水,他觉得不应该带着这些进入她的世界。雷电和风狂雨骤的夜被从这一小片明亮中隔绝,分离出去。
她的名字。她的喑默。她的微光。
海因里希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在笑。“真好。”他说,“你还活着。”
他解开斗篷,走到小几对面按茹丹人的方式盘膝坐下。房间昏暝却宽敞,是她家乡风格的摆设,香薰球在帷幔背后缓缓旋转,地上铺着驼绒方毯和泛发流水一般光泽的丝质垫褥。达姬雅娜拿出两只银杯,各斟了半杯暗血颜色的酒,瓶里刚好一滴不剩。她指了指,示意他取用。
不知这当头她是怎么弄到酒的,就像他也不知道她这段时间有何遭遇,又如何找到这样一个精致僻静的居所。“非常抱歉,”海因里希不动声色,“大病初愈,不方便畅饮。”
达姬雅娜笑笑,将两杯酒倒在一起,仰头一饮而尽。再度直视他时,她的目光隐含针芒刺人。海因里希心底一动,那是最能代表达姬雅娜的眼神。名为“蔑视”。
“你怕我下毒。”手指蘸了杯中残液,她在几案上写道。
“倘若我要你死,绝不会用这么拙劣的手段。”不等他开口,继续写下去,“你也绝不可能死得如此轻易。”
“你恨我。”海因里希说。这甚至不是确认。
达姬雅娜擦去字迹。
“你还没有让我恨的价值。”
“我在你眼里真是如此渺小么?”许多年前他灵魂暗秘的深处就已生长着这个问题,为了她永远不会平等地投向他的视线,她飘悬于云雾之上的月亮高高俯洒的光辉。曾经有一个时候他也许能获取她的依赖,却被他自己松手放弃,或者说它对他已不再重要,然而那之后他确实疑惑过究竟想得到的是什么。“不尽然吧。否则坐在这儿的将是伊叙拉将军,不是我。”
远离时企盼拥抱,接近时可有可无。
你只在你的臆造中爱过她。
“看到他今天的表现了吗?威风凛凛,光华灿烂,宗座器重,万民仰仗,未来会晋升圣裁军的总督军、及至加封额印成为圣徒也说不定。你该去找他才对。他必然会庇护你,以他对令尊大人的忠诚——而我不过是条被剥夺一切逐出家门的狗。”
海因里希将手放在唇边,眼帘低垂,却暗暗从达姬雅娜脸上那微妙的光暗变化验证着自己的揣测。“可伊叙拉只有忠诚。那个男人始终不懂得说谎……”他语速缓慢,“不懂得顺应你的尊严假装爱你。”
茹丹驭主的女儿笑起来。他知道猜对了。
所以你来找一无所有、死期克日而至的我。还是原来的那个达姬雅娜,即使历经血海也一点没变,还是幻想着有比实实在在的保护更具安全感的东西。如自尊。
如爱。
“告诉我你还是不是曾想要迎娶我的人。”她的指尖快速移动,“告诉我你还多少有点……让我爱的价值。”
海因里希沉默着。心绪飘向极远之处,但它所留下的痕迹仅是一线苍白。
“已经晚了。”终于,他说,“我将永远持有宗座侍卫的身份,不能誓忠于宗座以外的他人,不能对荣誉以外的事物怀有欲望。过去是,今后也依然。”
“很可惜。”达姬雅娜写道。她没有露出半丝意外。
光线从她手握的烛台倾泻而下。银发拂过袍服黑色滚边镶嵌的茹丹符文,绿松石和璧琉璃的额饰叮当作响。她站了起来,形如薄暮时分徐徐迫近地平线的夜晚本身。海因里希抬头望她,两年前——在他的时间里足可追溯到大地被孕育的伊始——海潮声鼓动夜风,他跪在沙岸上同样抬起头,而她俯下的眼神一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