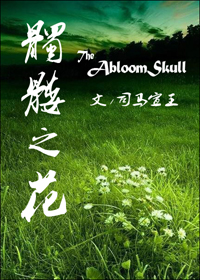����֮��-��15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㻹�л��ῼ�ǡ���˵�����Ҳ�ϲ���˶˵���ĥ�ˡ���
��Ҫ����֤�ظ������������һ��ῼ��һ�¡���ģ�ˡ�����㡣��
������ϣҡҡ��ָ����ͨ��˫�����ױ��Ź��������ˡ�������֤�����㣬û�㣬�Dz����㱾�ˣ����嶼���������ˣ�������ڵ��Լ������ж��������������Ǽ��²�����Ҫ�����������ζ���ҿ��Ժ��˼ɵ������㣬�������Ƴɰ�����ڴ������ӡ���������������Ƿ�������
һ�Ŵ���ζ��Ƥ�����ڵ��ϡ�
����DZ���Ʋ���۾������µ�������Ƥ����������ɫ�ݺݾ�ס����������������ʾ����������Ѫ��ͬԴ�������Ų����������Ღ����������״�Ǵӱ����������£�����ϸ�´��������Ա����������������Ĵ��ࡣǾޱ���Ы���ڽ���λ���ſ�������ɫ��������Ũ�ҵ�β��߸�����б�쵽ԭ�����������·������Ƕ������ǹ�һ�Ż��ȵ����ࡣ
�����桭���������㡭����
�����ǵ����Ǹ����µ����ְ�����
����������������Ů�����ţ��ӱ鲼��̵�ĹѨ�ﴫ����һ��Ļ��������Ҿ������һ��������
ǽ��������Ӱ�Ӷ��ˡ�
������Ȼ��ȥ�����˺�����ϣ������ûע������ﻹ�б��ˡ������������ŻҰ���ͷ����⣬���ϼ�û�����Ҳû�����Σ�������ȫ���ϲ������ǵ���ò������Į�ޱ��飬��գ�ۣ�Ҳ��˵����������죬ȴ�������DZ˴����ֿ�����ʹ����������������У����ǵĴ��ڸ���Ȼ����ϡ��������ζ���̡���ɫ����ĭ�����¶ȵ���
������·ʱ����һ����ذ���Ħ���ij���������
�Dz������ǵĽŲ�������������Զ�����ġ�
��������һ�����ι�״�����壬����˵��һ������ӵ�����ε�Ѫ�⡣
������������������Ҫ����ǰ������һ��������������˫�۰�ٲȻ��һ�����������Է����κ�������������ϣ���˸����ƣ��������ɿ���
�ǰ��档
����Ŀȫ�ǣ�����Ǻ�һ���Ӳ��ϳ���������˫�۵�λ��ֻʣ������������������ʯ�ҡ����ʺ���һ��������˿ڣ�ȴ���ܰ��������ѡ��Ծ�������û��һ������������ģ����ǡ��ιǡ��߹ǡ���֫����ָ��������÷��飻�е���Ƭ����������֧�⣬�е��Ѿ����˳����������IJ��ֿ���ȥ����һ��������
����һ�и����µ��ǣ��������š�
����Ҳ�����ҵIJ��¡����������ҵķ�ֲ���������𱨣�����һ�������ˡ���������ѹ����������³�����ζ��Σ�������˵���������Һ���֮�䡭����������ѡ�������ء���
�����ҧ������������ֻ����֮������һ�߳�����������������ǿ�Ѱ��汧�ڻ��С�̫���ˡ������ɸղ�����Ƶ�����ֻ�ǻþ���һ���������������ô��������˳��ص������أ�
�������������õ�˫��һ��һ�ϡ��ʾ���Ƶ�����ڰ���
������Χ£������Ҫ��������
�����л������ң���������������䣬���㲻�������𣿡�
������ϣʾ�������˺�
�ڰ������ˣ���Ҳ����ʵ������Ķ�����ʢ������
����ǿ���һ����ɫ�������۾����������Ů�ˡ����������̻��绨֦��ɢ�ݳ��������������
�����������ֱ�ӵ�����档
�ҵ����ˣ��ҵ��ֵܣ������¸ҵ�սʿ����ͬѪͬ���İ��£����㰲�߰ɡ��ں�ҹ��嫺�����������ɡ�
Ѫ���������ս��ı����������ȥ���۶ϵ��߹Ǵ̽����࣬��һ˲���������ľ��ף������������������������Ǹо��Լ���ӵ���IJ��������Ӱ�����壬����һ�ż�Ӳ����������������ĺڰ������װ��������������գ�����Ů�ӵ�����һͬ������
����������
������ϣ˵��
�����̧ͷ����������ʹĿ����з��У�������ϣ�ѳ���һ�غ��ǡ�
����˵�����㡣����˸������µ������㡣��û����������䵽�⾳�أ���ʣ˭��ͬ���㣬˭�����Ԯ��������ʹ�ࣿ�������������������
������ⲻ�˶���ˣ������������˵�������������˶�һ��������һ������ͳͳ����������ɺ�ܿ콫��ɷ��棬����������˶�Ҫ�����繬һ��ѳ�ᣡ��
������ϣ��ü��б��������
һ�����ŵ����鲻�����ε��������档������ȴ���գ������ڵȵ���������ˮ�����㡣
�����Ȼ����ס���ˡ���
��ϸϸ��������ǣ������ڼ��Ӽ�����ڵ�ʳ�
����������ʲô�����繬����ɺ�����桭�������������Ҫ�ٵ��������Ҹð����������ǽ�����µ�һ��ݻ���������ȥ�����˷��������µ������豸����ջ����ɣ��б�Ҫר�����������Ϊʲôɷ�н��µذ���ʯͷ����֤�ݣ���
ն��������Ц�ݡ������ڣ����顣��
�������ɫ�ı��ֻ��һɲ�ǵ��¡�
��Ѹ�ٻָ���̹Ȼ��һ�����ƣ�������֮ǰ��Ҫ���ɡ�������ϣ����֪����ŵ�����飬���̻�����ָ�ơ�����ú��ߵ�֪��ȥ���Ƕ����������������������Ѷֻ��������ŵ������Ų飬�ƻ������̻�Ϊ��Ӱ����������ǰ��������һ����������Ϣ��������������ؽ�Ҫ������������������������ס�ˡ������������Ŀ�ͽ���²�����Ը���Ƹ�ɺ�����ˣ�Ҳ������ѿ���Ȩ�������ˡ�
Ψһ��ս��չ�����Լ��ͺ�����ϣ֮�䡣
�����Ľ�����˫������־�ҹ����ͱ��ʮ�ּ�
�������˿��ҵ��죬��ƾʵ�������ɡ���
������̯�֡�
������ץס��²��˫���������������水����һ��ƽ�ŵ�ľ����̨�ϣ���������������������֮��������һ��ɽ������������ѹ����ǵ������������������һ�죬�������������������㵤�˵�ʬ��װ��һ�£�����������˵�̿��ܲ��˿����������С�һ���������ҵ�������
����һ������ͺ��������ͭ˿�۾������˽�������һ������ҩ�䡣
����ס����������Ȼ��ô���ƣ������ϴ�������ǰ�����ʱ������ۡ����ϴ��۵öࡣ��
����Dz����ǣ�ֱ���������������գ�������Ӳ������������Ǹ��ȱ�����ҧ�࣬�ֲ���������˵���Ķ������������ⴿ�����һ�١�
һ�����ײ�ģ���ij����μо߹�������£��С���ϣ���ϥ�Ǽе��ǡ���ȫ���ɴ�������װ�ɣ���˨š����������ͼ��������ѽ��ѷ֡�������ϣ��������ǵ�ͷ��������Ŀ����Щ����ȡ���ij��������Լ�ӲľШ�ӡ�
�������һ�ο����㣬�����ҡ������ս�����Ƕ��ߣ�����֪���Ǽ��¶����������������ҿ���������������ҡ�ֻҪ���ɿڣ����ǻ������ѣ�������DZ��һ�������ת��������������ٵ�����ȣ���ͨ�˳Ų��˶�á���ٴ�ʮ�������°뱲�Ӿ���Ҳվ�������ˣ�ֻ�ܹ�����·������һ�������ϵ�սʿ����̫��ϧ����
����������ԡ�
��һ��Ш�Ӳ����������ķ�϶�䣬����Ȼ������ȥ���������͵�һ����ȴû�����������ش����ͺ�����ϣ�Ľ����ֹǵı�������
��������������
�ڶ�����������Ǹ�����Ĺ��̣�����������������������ǵ�ָ�������ݽ������ľ����������Ƕ������఼�ۣ���ĵĽӷ��кdz��¾ɵ�Ѫ��ζ������˭��Ѫ�����棿����������ijһ��ͬ����������շת��ij��İ���ˣ�
�����ٴξ������䡣�����䡣
��Щ���䡢�Ұס���Զ�����˲�ҵ�������ȷ�е�˵Ҳ���̾ߵ�һ���֡������Լ���������Ȼ����֪ʹ�ࡣ�����Ǻ��������ó�������ƿ�ʹ���أ�
���г����ɡ���������ϣ˵��
һ�����ԡ�
��ûʲô�ɳܵġ����Ƕ������ӡ�����ɻ���˱���Ѭ�����䡢���ƺ�����Ϊ�˲�й¶��������¶�Ļ��ܡ������ܹ��ر��ѵ����������ʩ�̵��в����κ����������������У����Ƿ�ֹʧ�ȶ����������������������dz�ʦ��������һ�����Ҫ������⡣���ǵ�Ȼ������Ц���㡣��
������ϣ��ס��ͷ������Ҳ���ᡣ������¶���ݣ����Ҽ���̫�����������ˡ�ÿ����������ӵ��������ͼˡ�Ů��Ҥ��һ������������IJ�����м��ĩ�˻����Ƿ������������ܾͺ��ɡ��Ҳ����Ц�㣬Ҳ���ᾴ���㡣��
��������������Ǻ�������������
�ڰ˸���
������������ʮ����ǰ�������ֵļһһ��������ǧ���£�ȫ����Ƥ�����ñ���һ����˺���ˣ������˵���������ǿ�ʼ����ͬ�İ취�Ը���Ů����������û��ͦס����һ����˫�ű��պ����Ь�ӳɽ�̿�������ŵ��ף�����ͬ��ȴû��ôӲ�����Ż��Ż��Ͱ��鱨һ��һʮ���˳�ȥ����֪���������αر��Լ��Ժ�������Ŀࣿ�˸��������㣬�����㲻����������Ҳ������㡣��������װ��˷ѣ���ļ�ǿ��Ӣ��һǮ��ֵ����һ�죬����ǣ����ֵ����Ц���Լ�����
��û��ͬ���ˡ������˹���һ�ˡ�����Ϊ�һᵨ�ӡ�
��������Ш�ӳ��ص�ײ����һ�£���ˮ˳Ӧ��������䣬��ľ���ϲ�����Ѫ����Ϣ���������ʵ���ζ��
��������������治������
�����ǿ����������������ϣ����������ֻ���ɫ�����ӣ��м��е��������������ϵĶ��ơ�
�����ꡭ����������Ůҽʦ�����ǽа�˿譵°ɣ��Ҽǵ�����һͷƯ���ĺھ�������
������س���������˰�δ�Ϣ��ʱ�������뵱����������������Ӧ�ԡ������������еĿ��ܶ�������˿譵���Ȼ�����عȣ������ٺӵ�Сľ���������Զ��֪�������Ϸ�����ʲô����֪���˿������Ѫ�ĺ���������������֪��ȥ��η������ںεء�
��Ҳû�б�����Ҹ��Ľ�֡�
���������⿿����ϻ�Ӯ�����ҡ������岻���Ƚ������Ļ����������������ѽ����������
������ϣ������ơ�
������˵��������
��������˵����������ġ�
��ʮ��ľШ������ȥ����������ζ�Ž�����������ÿһ��˲�䶼�������������յ�ˮ�飬�Խ����������������һ�ε��䡣�����û���ټ����������ܿ϶��Լ��ں��У����Ҳ�ֹһ����Ҳ��ֻ��Ҫ�ڸǾ�ͨ��Ш���ô��Լ�������������
��ҽʦ���Ĵ������λ�����ʱ��������ʧȥ��֪�����������������ǵĴ��ڡ��Ƕ��ֿ��ֳ�����һƬ�̵���ϥ�ǵ�����
������ж�¼оߣ���Ť��������֮��ȡ����Ѫ�����Ш�ӡ�һ��ʮ�Ÿ���
���Ѿ�û��˫���ˡ������ǵط�����̲�ཬ�����ż���ϸ���ɳʯ��
������ϣ˺�������ʪ����š��ˮ�ij��£�����������������
�������ҡ���
�ޱ����ᣬٲ���ϸ�ʱ������ͽ�����ո�����ʦ��
������һֱ������������ܸ����ң�Ȼ����������ˡ��ӵ��ǰ����ɡ��������㣬�����ɣ�Ҳ���ܸɴ��������
����ġ������ӡ�����ʣ�¼����ء�����
�㵤�˴����������۾�����ˮ��������Ŀ���ɢ����ȴ����ĥ��������Ƶ���ζ��
������ϣ��ɫ���ˡ�
��������塭������Ҽ�ֵø����𣿡������ٵÿ�����ʱ�䡭����Ҫ���������˷��ڡ����������𡭡���
�ؽ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