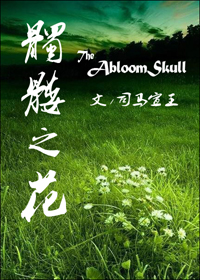髑髅之花-第17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教皇没有否认。“跟我来,”他说,“去看看永远不会舍弃我们的那些战友。”
他们走进一处门锁老旧的陈列室。教皇亲手点上火烛。这房间独属于他个人,历代诸圣都无权插足,里面的藏品不过一种:剑。
“这柄剑在我加冕当日充作仪式道具,此后再未见血。虽然定期保养,锋芒如新,渴求杀戮,但恐怕不会太持久。”护手呈十字,饰以辉金和七彩珐琅,宽度是普通权剑的两倍,劈砍的杀伤力更大。
“这一柄是我为对抗旧圣廷而与奥伯良三世结盟时,他赠给我的礼物。”帝国风格的阔叶剑,双脊,流线型边刃,雪杉木剑鞘刻着皇帝誓词。
“我在茹丹漫游时,由吉欣城的工匠打造的佩剑。”通体乌黯,刃开白光,正是茹丹人偏爱的式样。剑身细长厚重,尤其适合突刺。
“我被普拉锡尼封为武圣徒时赐予的剑。稍早几年,我升任圣裁军统帅时所使用的剑。以及更早的,我加入圣裁军时得到的剑。”……
教皇转向角落里最不起眼的一把。
“这是我战斗生涯中的第一件武器,”他说,“我担任神裁武士那五年间,令四十名罪人伏诛的剑。”
在同伴的光辉面前,它太简陋了,正如那段被远远丢在脑后蒙尘落灰的年代。剑柄的松木若还有生命,内部早已轮圈密布。剑的造型平凡无奇,连质地都只是夹芯钢,而非纯钢,身上更是磨痕累累;它唯一的装饰,是这些伤痕里血垢沉积,蔓延开来,仿佛火焰的脉络。
教皇扯下外披的祭袍。此刻他除了甲胄,一身别无他物。“来吧,诺芝,与我共同作战吧。你自称年迈体颓,但至少还有为我递送武器的力量。”他拿起最开始的仪式剑,“敌人就要到了,宗座侍卫在下面撑不了多久。我战斗时你待在阁楼上,一旦我的剑卷口折断,就立即掷一把新的给我。来吧!我已抛弃三重冠,不再是诫日圣廷的教皇,现在乃是以武圣徒曼特裘的身份而战!不管诗歌多么飘渺虚幻,请你用它为我谱写荣耀,请你为我唱响你失聪前写下的六韵诗,为我的敌人唱响挽歌!”
……尤利塞斯,你不过想证明给我看罢了。你真的明白这句话吗?你真的相信它吗?或者你已经说服自己被它所感动?
“‘我所做的一切,’”轻声地,他顺着督军的遗言说下去,“‘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
作者有话要说:
☆、Ⅴ 于无声处(3)
身体在云石地面倒拖而行,抬眼便是血迹。
不是自己的,海因里希确认。自己的血管早已烧干,能流出的也只有脓液。
血迹源于死者。七零八落地倒卧在永昼宫各处,底下两层宗座侍卫与叛军各半,慢慢向高层去,露台、走廊和过道转角的尸首就全是叛军。待进入一间空旷大厅,尸首的数量达到顶峰,纵然室内阴暗,仍依稀瞧见头颅、断肢、肝肠遍地,看来不久前这里发生过恶战。
拖着海因里希的人把他往厅中一台座椅下面一摔,揪起他头发,火炬对准他眼睛来回晃。“嘿,您早早地就醒啦……大人。”那张脸笑得明晦参半,“这下可更有趣了。”
再怎么模仿,摩根索也学不会他想象中城府深沉的阴谋家该有的样子。海因里希懒得评价他的表演。这家伙的腿骨在那次谋刺事件中被箭射穿,从此瘸了,或许念着他“护驾有功”,教皇并未处决这个傀儡侍卫长,而是扔到牢里当一名最低级的狱卒,正好方便他将所有怨气全发泄到海因里希身上。平日里百般折磨自不消说,就算叛军入了城,他也不忘带旧上司一道出逃,以免后者占了便宜,轻易解脱。两个人的地狱,海因里希想。自己最后竟落在这个既疯又傻的废物手上,教皇让人生不如死的手段果然高明。
“眼熟吗?这儿可是你工作了两年多又交接给我的地方……宗座厅呢。”
背靠着御座的椅子脚,海因里希深深吸进一口气。摩根索走开,去扶起厅侧歪倒的立式长烛台,点亮没烧完的蜡烛头,眼睛却片刻不离。他以前没这么蠢的。一个检验囚徒反抗能力的伎俩为何如此笨拙?下半身不能动,双手也被麻绳反绑,索性放弃挣扎。摩根索一直怀疑海因里希的瘫痪是假装,用沸油泼他下肢,看他全无反应,这才踏实;对他是否真的病重到手无缚鸡之力,却压根没信过。
“啊……还有件东西,是不是也很眼熟?”
那支冰凉的东西顶在海因里希颔下,逼他抬起脸来。他稍后才看清,是手铳。自己曾用它狙击过一名茹丹刺客的手铳。
“我喜欢看你惊讶的表情,”摩根索玩味不已,“在你发现自己失算的时候。”
他喜欢带着厌恶眼神欣赏这面孔上的烂疮,尽管害怕也染上病,从不触碰。“你总是自命不凡,以为凡事都在自己算计当中,呸!猜猜我怎么得到这玩意儿?我瞧见总主教塞一个大包袱在衣服里装成驼背逃命,差点让几支流箭射中,他溜得比受惊的老鼠还快,匆匆忙忙落下这个。运气太好,它一没沾湿,二没走火,里头居然还有颗子弹!很意外吧,我这么一条任你鄙视、玩弄、摆布,被你害得丢掉一切唯独没丢命的狗,终于也能请你尝尝它的滋味!聪明如你,可曾算到今天?”
海因里希张了张眼皮。“你想活?”他哑声反问,“还是想跟我同归于尽?”
手在背后触到一根金属长杆。御座下有支滚落的烛台,被坐垫长帔遮住,因此摩根索未能察觉。海因里希克制着自己抓起它与眼前的人奋力搏斗的幻想。手腕绑得很紧,他悄悄伸出手指,将那烛台以极小的幅度拨动。
“选这个地方了结我,太不明智。下一波叛军不知什么时候攻进来,见许多同伴惨死,唯独你完好无缺……必然以你为大敌,一拥而上。想活的话,办事就利索点,干完就跑,省得麻烦。”
胸口挨了摩根索一脚。他险些窒息。
“不劳惦记。现在可是半夜,我要是叛军,怕里面有埋伏,先把外头围个结实,等天亮再进攻不迟。至少有半个晚上可以好好料理你。玩够了,我再提着你这位前任宗座侍卫长兼典狱长的脑袋,跑去找叛军,说不定他们还会赏我几个钱花——怎样,这椅子舒坦吗?”
摩根索扳住海因里希的头,使劲往御座上拗。“你是没办法坐上去啦,不过得感谢我,给你一个亲近它的机会,让你跪在它底下。”他把手铳收回腰间,特意亮出寒光闪闪的匕首,“子弹就一颗,得留到收尾时用。刀工技巧还要向您学习啊,大人,不过请放心,我会拿布包着手,以免弄脏了自己。”
他解开对方手腕,要将两只胳膊分别绑在御座的扶手上,先从右边开始。海因里希左肘被他暂时用膝盖压制着,手掌却还有少许动弹的空间。趁摩根索全神贯注给麻绳打结时,他暗暗摸索到那支烛台,长杆另一端从椅子下面戳出来,恰好在自己腿部附近。
早已失去感觉的腿突然动了。
摩根索大惊,轻敌的懊悔明明白白写在他眼睛里。他的防备都叫这一动吸引过去,重心稍偏,被膝盖压住的左手立刻有了摆脱之机。
海因里希动作极其干脆,直取对方腰侧,一把摘下那支手铳。
“知道宗座为什么不杀你吗?”他撕裂般地笑,“为的是让你认清你与我的区别。有种人百虑一疏,若不能成功,就是在接近顶峰时摔落;还有一种人,甚至根本不具备向上爬的能力。‘失算’这个词只能用在前者身上,而你,还不够资格。”
在说第一个字时他就开了枪,于是后面的内容统统落入虚空。摩根索踉跄后退,滚下御座前的数级阶梯,惊骇与懊悔的神情自此凝固。再也没有一双耳朵能分享这段话。海因里希不禁憾然。但很快,就连感到遗憾的力气也不存在了。
由莫测的命运暂借给他、供他抓住短短一瞬机会爆发的那股力量,在他方才言语之际又消失殆尽。他听见它的流逝,像自己呼出的气息。血的味道黏腻腥膻,围堵过来糊住鼻腔,每一丝离开他的气息都仿佛带着决绝姿态誓不复返。他哈哈笑两声,提起火铳对准头使劲扣动,当然,什么也没发生。
射杀摩根索成了毫无意义的行为。死亡就在身边,在一个无限接近他、却也仅仅无限接近他的距离外,摩根索的死不会使它的到来早一分,也不会使他为等待付出的痛苦减轻一分。
而海因里希能做的只有等待。
他实在无力给自己的右手松绑,只有在御座下瘫坐着,等待黑夜过去。大厅里满地死尸,围着他一个半死不活的人,等到蜡烛熄灭,星光也黯淡了,一抹苍白色开始刷上墙壁,然后脚步声终于到来,逐渐清晰,来叩响他与死亡之间那扇沉重的门扉。
第四军部队举着火把从大厅侧门走进,见厅中惨状,步伐不由得一滞。借助火光,海因里希认出了为首将领,那张白舍阑人的脸崎岖坎坷,像是一场大病肆虐后的留念。
“……伊叙拉。”
微笑着,他唤道。
伊叙拉警醒地抬起头,目光停驻好一会儿,他才确信御座前这滩烂泥竟是活物。
而且这活物竟是自己熟悉的人。
他在部下也唤醒对这人的记忆之前挥手示意,命他们从另一边的侧门出去。
“是你。”白舍阑人说,“宗座在哪?”
海因里希笑得直发颤。“别这么不近人情……忘了咱们的同袍之谊么?好歹也先关怀一下……我是如何变成这副德行吧。”
“我没工夫和你闲扯,不想了解你怎么作践自己,更不在乎是谁把你捆在这地方。”伊叙拉语气如坚冰,“回答我——宗座在哪?”
海因里希低声咕哝几句,伊叙拉听不清,只得走近。“……陪我叙叙旧,”他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哪怕你不想说,听我说就好。等我说完,自然会回复你的问题,否则就算你再逼迫,我也不会吐露半个字。”
伊叙拉将手搭在腰畔弯刀上,但终究还是移开。
“……说什么?”
“实话,信不信由你。万安节前那七天暴…乱是我策划的。葵花全是一帮蠢货,只会窝里斗,让我稍加拨弄便草木皆兵,结果自取灭亡。你眼睛那时被人捅瞎,也得记上我一份。”
早已组织好的言语流畅得出奇,光是讲述本身就能带给他极大快慰,远远冲淡了肉体的苦楚。“我抓住机遇投靠第四军,好容易又抓住机遇跳出来,摆了贝鲁恒一道,本想弄个圣裁军统帅当当,谁知曼特裘老儿把这位置给了哪点都不如我的你!他以为我在他身边俯首帖耳,就掀不起大风浪么?我做到了,哥珊在我操纵下天翻地覆,信众被他们虔心尊敬的人蹂…躏屠杀,不可一世的葵花遭受灭顶之灾,而曼特裘不得不忍痛宰掉他养的这群疯狗!想到所有这些人的表情,都是我一手营造……伊叙拉,你可否体会我的满足?你可曾从我的欢悦中分享万分之一!”
“你行如此毁灭之事,单单为了从中取乐?!那么多无辜者被你害得家破人亡,单单为了让你欣赏他们的惨痛吗?”
“毁灭哪有什么乐趣?毁灭的结果才有乐趣。”他仍用那种如数家珍的口吻说下去,尤其是伊叙拉青筋暴突的脸,堪称自己的又一件战利品。“若这结果乃是你苦心谋设、倾力所为,才最最有乐趣。唯一可惜的是,我没法走到最后……就连拼着这腐烂之躯刺杀教皇,也功败垂成了。不过在那之前,我已经把那老儿涉嫌通奸的证据散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