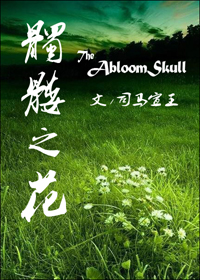����֮��-��2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ڼ��Ļش��κ��ˣ��κ�������Ѿ��������ء�
����ô������������ȥ���˸����𣿡�
��³�㲻��ؿ����������ܿ죬���ֲ���ͻ��������Ũ�صı��������������۾���
�������ǵġ�����˵��
ʯ��Ц���������������̿͵Ĺ���ʱ���ǰѼҲ�����ȵ�Ѫ����۶��ˣ���һ�鱻������ס�ı���
�����л�Ҫ˵��
�����������2��
��³���͵غ���һ����һ�����������ѳ������ľ�������ײ���ǵ����ϡ�ʯ����ͷ������ǰ���䣬������Ŀ���ĵ�Ѫ����
��������������ǽе���
�����γ������������������൱�зִ磬�̿ͱ�����˿�ʮ�����ˣ�ȴ��ȷ�رܿ���Ҫ����������ǰ�������˵����ӣ��㲶��������Ƶ�����ʱΪ��ѪȾ������ǻ��ڻ�е�س��Ű�ĭ��һ���������ȥ��
�����Բ��ˡ�������˵��
��ı��ʥͽ�����µ����İɡ���������ʼ磬�������ﶼ���µ��ˣ�Ҳûʲô���µ��ˡ���
��³�������������ֱۼ䣬��û�����ˣ�ʯ��Ϊ��������������һ�����ɾɴ��������ؿ�Ҳ���ǿ��ײ�������Ѫ�����������ĸɿ�����ӿ��������һ����������Ϣ��ʧȥ��ʶ�����ڻع����������Ƿ·�ɥʧ�������������ֻ���������ڵأ�������һƬ���л�Ҷ��
����ˡ�ң����ˡ�ҵ����������������������ס�˼�ʮ�꣬��ʵ���֣���û��˵��ʲô�Ӽ��������ü�����Ů������ز���ˣ�Ψһ������˵�С���Ӽ�����ʥ͢������ǰ��ʱ��Ҳ����ج�ģ�����ʱ������һֱ�е�Ź֡�����û�뵽��û�뵽����������ɵ�°�����
����վ��������ɵ�£���������˵��������Ȼ�ɡ�����Ԥ�ȷ��¶�ҩ��������ڣ��������������ʧ���ߵ���Ϊ����
�������ϸ�����û�н��룬�Ըղ��Ƕ�����Ҫ��Ϊ�ܹ�ѵ���İ�ɱ��δ��̫����Ц��������ǽ������Ѿ���ֱ����̧��������˭����ͨ��ȥ����һ���ر�ɭ�ϵĴ����ʵ�������ɼ������ҿ�����ֻ�ǵ����ز�����˶��ѡ���
���ر�ɭ�ϣ��������Ӹ����£�Ͷ��ббһƳ�������鷢����ʱ��ʥ�����߶���˭��������Ǵ��ˣ�����ʱ������������ˣ������������Ϊ�˸�������������
����Dz��ٿ����������֪���ģ���������ִ�����˷Ѵ��࣬��ֱ������ȡ���衣��Į����̣����У�ƫִ����ı�ۣ���Զ����һ�С����������ô��Ϊ����һ�������ߵ��أ�
����˻�Ƶ�˵��ʲô�����Ѿ�û���������ˡ���췢�ڵIJ�Ҷ̰����˱Ѫ����ֱ����Ũ����Һ����ȴ���̣���������Զ������һ�𡣡���ס�ڡ�����³���������
���ܾ���������
����������ֻ�dz����⣬������ȥ���κ��ˡ���ʥͽ����Ŀ�⣬����δ���Ц����Ȼͣ����ʯ�����ߣ�ȴ�ѿ�ʼ���䡣���úð�������Ϊ��ף���ɡ����¸ý����ˡ���
û��������顣��ǿ׳���̴Ӳ����³���ʱ��һЩ��Ů���ڵ������е��ʣ��ֺ�������ϸ����˿�ؿ�����
������һ�̣�������Ƽ��˱�³�������
���Ȳף�����Ѫɫ��һ�������������ֻ���ڱ�³�㶯��ɱ��ʱ�����Ż������һ���ز�����������������������Ĺ��꣬������������Ѫ����ů������������룬�������㡣
��ǹٵ�Ԥ���ڵ���ҹ��õ���֤ʵ��
��ҹʱ�֣������뿪���ع����н������ռƻ������ǽ���ɽ´��Ӫ��Ϣ���������ɭ����ֻ�в�Զ��һ��·�̡�
�˰����˵Ķ����������һ�����ȣ��ֲ������˴��ܹ���Ӧ���ķ�Χ������Ϊ���Է���һ������ͻȻ���ֵĵ���ǰ��л�����³�����ڶ���ǰ�������ݺͼ����ϵĻ��ԶԶ�����������·�һ��ɢ�����С�������ҷ����������Ʈҡ��
������ָ��ժ��ʲô�������ݸ���������ı���˵�ͷ����������Ӷ�ȥ��
���������������Ķͼ���������Լ�һ���䱸�ѻ�����۶ܵ���װ��ʿ������������������沿��ǰ���������ԭ�ز����������������������һֻ�֣������ӳ������֡�
���ǣ��������ˡ���
������˵��ÿһ���ֶ���ʥ��³�����Ը����ָ�䴹��˿�ߣ���ʥͽ�����������ط����¹⣬�����뻳�ɣ�����Υ������
�ӳ���������ö��ָ����������������ж�ʮ���꣬�Ǹ��þ�ɳ�����ϱ�����Ȼ���������ij�����ζ��ʲô���������ǡ�����˵��
���������������˶������������ͬ���ǵĵ��ˡ��������Ὣ������Ī����ҫ����
���ǡ���
�������ݵغ����ۣ���һ˲�䣬���������������������ƺ���һ˿���ݣ��������������۾�ʱ����Щ������һ�����ŵĻ���
��������Ϩ�ˣ���ת��ǰ����ʮ������
��������ˡ�����ʻ���Ʋ�֮�У���ͷ�Ļ�Ѻ�ͭ��״�Ĵ��Ҳ��ȼ����һ�����������������ַ����͡��ع�ͷ����������������û�ں��������걳������Լ�Ļ��Ҳ�·��ΪңԶ���ǵĵ�Ӱ��
�����������һ��������������
��ͬ�е���ͨ�����壬�ӳ��͵�̧��ͷ���������ˣ�������Ѱ��϶��Ƶĵ��������������عȡ���
�������ޱ��飬ҹɫΪ���ļ�Ӳ������һ�߷����ı�Ե����û���������ظ������������
******
��ǹײ����ѵ�����ߵ�ʯ���ϰ��ϣ�����Ϭ���Ļ���ƥ�������Ҹϣ�ԭ�����ֵ�һ��ǹ���ľ�����������С�����ڣ��������������ٴ�ͦ��ǹ�⣬�������٣�ǹ�˲���ȴ��Ȼ����������ת˲���ŵ�һ˿�����������DZ����������ķ�Ӧ��˳�ƻ������Ͼ�����ǹ��ǿ��ij������Ȼ�Ὣ��ָ��İ��һ�ᴩ��
��������������Լ�����ͷ����һ�������Ȼ���ѣ���Ȼ�Ƿ��ˣ����߲���Ҳ��Ϊ��𣬡�С�����ӣ���������ˣ���ǹ����ֻҪ�������Ͼ��ܴ����˵�����ֻ������Dz��ã����������˾�Ҫ�������ƣ�����ǣ��ú�������������ӿ��ڵ���������ĸо�����
�����˰���ɫ��������ȫ��ʽͷ�����ͳ�һ����Ц����ÿ����ͷ��Ӯ�����ң��Ͱ�����������һ����Ͷ����Ƥ������ô����
��������ʿ����������һ�ڣ����ֽ��Ѿ����ε������ӿ��������������һ��������˫�о������Ķ���ȴ������æ����������������ˣ������˸ջ�����������Ȼ����Ԥ�ط�����档ǹ���´�����Ӳ���죬ȴ�ǵз����ϵ����ľ���ķ����ѡ��������˿ɱȵľ���͵�ʶ�����˲�ת������������Է����ࡣ��ǹ̫�����ط�����������˲ʱ�����ұۣ����н�ҧ�ں��ص���Ƥ���ϣ���Ȼ����������һ�֣�ȴҲ�������ڶܺ�������ʹ���������үү����Ӳ�ļһ�����ָ���ȡ�˸�ʲô�������ְ�����
��˭�������үү����һ��ռ���Ȼ�����������������ת��磬���һ�����úܣ������ٴ���ʮ�꣡����Ϊ˭��������Ǹ����������Ѿͷ����
������ড�һ���ɵ��ƿն�����ǡǡ����������ȥ���ܾ�������һ����˻��ǰ���������𣬽������ؼ�����ʿ���°��������������ٰ���ȫ�����ڸ���������ƽ�⣬��һ��ˤ�ý��ʵʵ����Ϊ�DZ���
����ѽ������ǹ��ʿ������Ͼ�ز������˼�������������Ҳ���Ʋ�ס�ر�����Ц����������Ϊ����֪���ģ����Ŷ�����ŭ��λ�����˵Ļ����³������൱��ҵ�Ŷ����
�ɵ������˴�ʱ��б����ѵ�����ļ��бߡ�������صIJ��Ӹողŵִ���ɭ���������Ѿ�ϴԡ�������¼��У�����һ��������ʵ�������������̿���������Ȼ�����롣���������������ü��������ô��������Ǽһ�һ����˵�����������ģ���
��ʿ����ǹ�����ֽ�����ʵʵ��ͷ��ժ������¶��һ�����ź�ͭɫ�̾������������������ʨ���������³������������IJ�����ȴӵ��������е��˲���������ʢ��������������֮�����ֵ��˾��Ʋ����뵽����ֻ��һ�������Ա�����ϸ��ȸ�ߵ�ʮ�����к�����û�������������һ���Ҳ���Ҫ�е�����ء���
���ⲻ�Ǻþò����İ���̽���𣿡��������ⷽ�ŵ�ʧ̬�����˴ӳ��������𣬼��������æΪ��ж�����ס��������ƺͻҰ��뷢����ȫ���������Ӧ�е�������̬�����ο�ΰ�������Ӳ��˫������ս��ʱ�����ƣ����˿̣�����ȴȫ�ǽ����������Ц��������˵˵������ͥ�ļ��ţ��Ƕ��Ĺ����Dz���Ƥ������ţ�̣���ϸ����һ��˿�о����նϣ���
���ǿ��ڴ����ǵ������������ߵ����ޣ������һ�ž����˹�ȥ�������������ε�ս������ѫһ�����⽨��ʿ�����Ĺ��Ŷ�Ҳ�������ε���ͬ�ź�������ҫ���ķ������¡��ղظ�ʽ���������������ָ�������Ů�����ѳ������������ɷָ��������ɣ�����˵˭��˭���ӷ���ܺܶ�����Ϊ�������۷紿�����꣬������˽���´�����ijЩ����Ĵ��⣬������ѹ��������ֹ���Ŷ��û����ٳ���Ů����Ů�Ի��º���������Щ������Ӳ�IJ�Ʒ������Ҳ��������/������ԭ��һ�����û����ӣ�������ϧ������ͷ������ô���������˵������Dz����������ӣ�����ǰ�Ļ����Dz��Ƕ��纵��ʱ���ӱ���ˮ��Ұţ����
���Ҷ������˿�ûʲô��Ȥ�����ǵ�Ů���ֳ��ִ�׳��ֻ���ݺ����ڼ��̡�������Щ�߰����㵤������һ��������ս���Ͽ�ɱ���Ǵ���ɴ���г裬�ͽ��˴ӽ�ֺ���ﶼ�˷ܵ�ֱ��������
�������ҪС���ˡ���������Ц��˵�����۾���Ư���������峺�����ɫ��������ʱ�·���ʱ���б�Ȫ���磬���㵤���˲����ڴ�����Ů�˻��ĵĹ�������㣬�ù������䵶�ļ���Ҳ�������ܼ�Ŷ����
���Ŷ����˴����ӡ���˵�����°ɣ�����̡�������ɫ����������ʥ�߳���ǰ������������ɭ��������ȴֱ�����ڶ�û������Dz���Ϲ�ͷ������ȥ�͵������ˡ�����������¶����ε�ս�Բ���ô����
����̹��Ŵ���Ц���е���Ӳ��
������ô�����˵����֪��������ˡ�����
���ٴ�������˻�����������ɭ����ʿ���Դ����ɵ��ó�һ��·������ʥͽ�Ĵ���ٴҴ�����������������ǰ��ϥ��˫�ֵ���һ������ӡ�ľ�������������һҹδ�ߵ�ƣ�����Լ�Ѫ����
������ӹ�ȥ���ĵ�һ�ۣ�ԭ������ԣ��ı�����ʧ�ˡ�
ϸ��Բ���Ķ������ʽ��д��һ�ɲ��䣬��������ǵ��ּ���������̵�Ȼ�����ʥͽ�Ļ�Ҫ���飬�Ǹ�������Ϥ�������ˣ��������ڵ�������������ݾ�������м�Ҳ��������������ԵIJ���������������ʲô�������Ŷ���ü�ȵ�����˵��ϸЩ����
����ٵͲ���˫�ۣ�û��̧ͷ����ʥ�߱�����������̿͵ı������ɾ������������Ǹ��뿪ʱ���عȳ�ͷ���ؾ���Ȼ���ӷ�����������һ������ľѻ������ڶ�����������������ʮ���������ͬ�̶ȵظ��ˡ����ǵ�ս���������ؾ�ȴ�ܲ������������ȶ����֣����Ʊ�˵ҹɫ̫���������Ϊ��ɽ���ű�������������
����ôʥ��������������̵����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