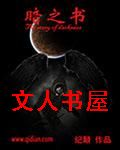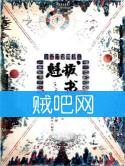失败之书-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心脏。
有的出租车司机目标很具体。有一回坐车,司机是从土耳其山沟来的中年农民,从后视镜能看见他忧郁的眼睛。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攒钱买辆好车,衣锦还乡。他仔细向我打听各种车的性能和价格,高不成低不就,好像我是车行老板。亏得我也爱车,趁机卖弄我那点儿知识。他暗自拨拉一遍小算盘,断定自己明年就能回国了。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
跟纽约出租车司机聊天要避免卷入政治宗教之类的话题。那一天头上包布满脸胡子的印度司机收工回家把我捎上。他马上要下班了,心情愉快,跟我东拉西扯。他来自孟买,在纽约开了十五年出租车,全家老少都搬到纽约。他说他的收入相当体面,都是现金,没有税务的问题。我提到塞蒙·拉什迪(Salman Rushdie),那个被伊朗追杀的印度小说家,以为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他一听这名字破口大骂,用尽所有的英文脏话。他准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我及时闭嘴,否则非得被他赶下车去。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个老纽约。有一回搭出租车去甘乃迪机场,随口问司机从哪儿来。司机一下火了,用浓重的外国口音说,从哪儿来从哪儿来,每回人都这么问,可等他说出自己国家,没一个知道。我的朋友说让我试试。司机说那好,我说出国名你说出首都,这趟算我的,否则加倍收费。成。司机说阿尔巴尼亚。他不仅说出首都地拉那,还提到阿尔巴尼亚一个男高音的名字,可把司机乐坏了,下车时怎么也不肯收费。
前两天我去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小剧场彩排,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白人,仪表堂堂,像即将离休的哈姆雷特。他叫罗维斯(Lovis),话剧演员,是六七十年代活跃在纽约的街头戏剧的骨干。他对中国一往情深。父亲是抗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队副,但不许他去中国旅行。说到大选,他骂布什是白痴,代表美国军火的利益;说到纽约房租,他骂市长是黑社会老大,这个黑社会由三种人组成:律师、银行家和房地产商。下车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他最后告诉我,等他从革命大潮退下来,发现这社会已无他容身之地,只能开开出租车,偶尔客串一下。“你还没醒过来,这世道他妈的早就变了。”他说。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纽约变奏(2)
五
田田不喜欢纽约。她前不久到纽约来看我,住了半个月。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在加州乡下小镇住了五年——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毕业,去年夏天又转回北京上高中,其内心困惑可想而知。住加州时想北京,真搬回北京她又失望了。这孩子念旧,她想念加州的同学,但并不喜欢美国,她将来要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十六岁是一个苦闷的年龄,再加上跨国迁徙、文化位移、家庭震荡、青春躁动,要处处小心才是。
田田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大概由于时差或对纽约的拒绝,她每天上午昏睡不醒,一到晚上来了精神,上窜下跳满屋飞,让我眼晕。客厅的橱柜上有个老座钟,想必停摆了很多年,零件早就锈死。田田从来不戴手表,大概在北京和纽约之间获得某种参考时间,她没事儿就去鼓捣那座钟,拨动时针摇晃钟摆,可走不了几下就停了。
在我看来,到纽约就要登高。我要带她去帝国大厦。她反问:“为什么帝国大厦?”“那儿高。”“还能比山高吗?”这下把我噎住了。好吧,那就去中央公园。“为什么中央公园?”“那儿大。”“到底有多大?”我比划半天,最后找出纽约地图。“才这么丁点儿。”她蔑视地吐了气说,“算了吧。”最后我只能陪她逛苏活(Soho)。一进那种青少年的服装店,嫌我丢人现眼,她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几句话把我打发走。
我们带田田到Q大姐家去做客。Q大姐的丈夫彼特(Peter)是德国犹太人,全家死在纳粹集中营里,只有他逃出来。他在纽约做了多年的心理医生,可每周还要自己花钱去看心理医生。他们住中城东边的一座现代公寓楼。一进门,大理石光可鉴人,门房穿戴如将军,很容易迷失在那些镜子中。他们家一尘不染,雪白的沙发雪白的地毯,聚光灯投射在墙上一幅幅抽象画上。
“简直像个五星级宾馆。”田田吐吐舌头说。
Q大姐做了一桌地道的上海菜。彼特的脑门奇大,像个老寿星。他会怪腔怪调地说几个中文短语,比如“拉关系”,嘲笑自己“搭错了筋”。我们带来两瓶法国红酒,喝得提心吊胆,生怕滴在脚下的白色地毯上。晚饭后,彼特取出他们最近在中国的照片。他事先警告田田,他是有毛病的人,必须戴上橡胶手套才能看相册。我正给田田照相,她伸出一双手,同时捏着橡胶手套装成另一双手,向我挥动。
英雄所见略同:彼特提议带田田登高去看纽约的夜景。她后来告诉我,楼顶中央有个露天游泳池,天气冷,上面盖着帆布。她想走过去看看,“搭错筋的!”老彼特突然在背后大喝道:“不许动!你、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死!”
六
G有个普通的汉族姓氏,因祖上满族正黄旗,为维护正统,他想改回去姓皇族的姓——那拉氏。据说上两代,他家某某曾是京城的卫戍区司令,可信。若再往上多数几代,我猜则多半是攻城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要不他怎么当年能从北京直奔荷兰,又从荷兰杀到美国,南征北战,其中必有血液的召唤。
他是“星星画会”最年轻的成员。他那时年仅十八岁,眼睛明亮,一脸憨笑。记得“星星画会”在北海公园办画展,他帮大家挂画,话不多,忙上忙下。当年那个明朗的北京小伙儿,待八八年秋天在纽约重逢,一晃变成了阴郁的纽约人。他俨然以东道主的身份,开车陪我们到康州的海边去玩,逛哈雷姆区,在中国城请客吃饭。
我九三年搬到美国,G的故事有点儿离谱了。在画画搞试验电影的同时,他投身华尔街,摇身变成了生意人。更邪乎的是,据说他同时有两个老婆,不久又生了两个闺女,年龄相差没几天。我打电话去问,他一乐,不置可否。依我看这也没什么,古已有之,再说那不正是多数男人的梦想嘛。让我奇怪的倒是,怎么以前从未觉察到他的疯狂。
自打我搬到纽约,我们周末常在一起喝酒。他喜欢苏格兰威士忌,不兑水不加冰块,干喝。微醺时他总要挑起一些形而上的话题,且用英文,直到先把自己说糊涂了为止。他笑起来挺费劲儿,多半是未完成的,支离破碎。
他性格中有很多对立的东西。他既疯狂又自我压抑,厌倦名利又渴望成功,待人诚恳又过于苛刻,既暴烈又脆弱。他在西方受教育,但骨子里是地道的中国人。他无疑是个怪人,怪人只能住在纽约那林立的高楼之中。前两年他搬到与曼哈顿隔岸相望的新泽西州。这一回可搬坏了,其纽约人的内心受到了重创。这多少在他的一组画中反映出来:形同废墟的建筑物梦幻般地呈现在平涂的单色背景中,无限寂寞。他开始在家里养鱼,而且专找那些丑陋古怪的热带鱼,养在自己心头,韬光养晦。
他最近画风大变,画了一批疯马,横眉立目,鬃毛倒卷,犹如他本人的自画像。我很喜欢,从中选了一张做我英文诗集《在天涯》(At the Skys Edge)的封面。我突然意识到,我跟他在性格等诸多方面南辕北辙,但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内心的疯狂。在某种意义上,疯马的对应物就是天涯。这么说来,我们在纽约相逢不是没有缘由的。
七
星期六上午,G开车到曼哈顿捎上我,过桥进入皇后区,上四九五号高速公路。不少纽约人去长岛度周末,车多,走走停停,到水磨房镇(Qater Mill)已中午一点。我用手机先通风报信,S站在路的尽头,那头灰白头发像信号旗在飘扬。
我们是在一本国际刊物的发布会上认识的。我早到了一个钟头,孤魂般在大厅转悠。终于有人出现,斜插过来跟我握手,他就是S,以前从未谋面。我请他帮我朗诵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会后我们应邀共进晚餐。分手时互留地址,他约我到他的乡下别墅做客。对纽约人的这类承诺不必认真。一个月后他打电话来:“还记得吗?对,是我。”
窗外海天一色,鸥鸟齐飞。他的夫人詹(Jane)随和善谈,是退了休的社会学家。S七十多岁,诗人兼出版商,但靠的是艺术收藏和交易。他专门经营意大利、西班牙的古典名画,和各个博物馆打交道。我问他是否靠家族遗产。他摇头说,他是从零开始的,最初的知识得自于以前的女友,她是个意大利画家。说这话时,我们坐在客厅,夕阳平射在他脸上,他眯起眼睛,满面倦容。长时间的沉默,直到阳光悠然滑走,他陷入昏暗中。
第二天上午我下楼时他在画房。他说他五点起床,正在看一本昆虫学的画。
一周后又接到S的电话,这回是在他家设宴。他住河谷镇(Riverdale),离曼哈顿仅十几英里,是有钱人躲避都市喧嚣的好去处。他的豪宅坐落在哈德逊河边,视野开阔。从阳台望去,在变化微妙的光线中,天空河水丘陵层次分明。他家是个小型博物馆,几乎都是文艺复兴的名画,包括伯尼尼和戈雅的重要作品。
今晚的主要客人是美国桂冠诗人库尼兹(Stanley Kunitz)及夫人,分别坐在长桌两头。S雇了几个人打下手,由他亲自掌勺。坐在库尼兹旁边的是个患艾滋病的女诗人,眼神扑朔迷离,但有一种正视死亡的坚定。我和S坐在库尼兹夫人两侧。她九十五岁,说起话来像个孩子,天真不连贯。她请人在她的红酒里兑点儿水。“这回好多了,”她呷了一口,对我说,“我看这儿的客人都很模糊,只有声音是熟悉的。”
S今天很健谈,从意大利人的性格讲到昆虫的生活。他认为昆虫有自己的世界,做爱做到昏天黑地的地步,那是一种幸福,人类不能理解的幸福。他有一天醒来,发现两只蝙蝠正在他胸口上做爱。“我怕蝙蝠。”老夫人说。S又讲到蛇的爱情,老人扮了个鬼脸说:“我怕蛇。”
八
去迈阿密晒了半年太阳的老夫妇马上要回来了,我们得从他们的单元搬出,临时住到朋友家去。要说这单元还算宽敞,但惨不忍睹。棕黑色家具丑陋笨重,好像跟随老夫妇多年后决心长在那里;两个并排面对电视的单人沙发,加上那停摆的座钟,代表了退休者的生活格局;墙上挂满廉价的商品油画和旅游明信片,如窥视浮华世界的大小窗口。我们不得不用色调明亮的布和地毯,以及从画家朋友那儿借来的画尽可能地覆盖一切。
这个单元在上城中央公园西侧的一栋三十二层公寓楼里。住在里边的都是穷人,若无政府的住房补贴,谁也不可能留在这寸土寸金的曼哈顿。我们的邻居多半是黑人。在电梯那狭小的空间和短短的升降时间里,打声招呼,最多三言两语,说说狗、天气和孩子,然后目光错开。别瞧纽约人直眉瞪眼,其实什么都没耽误,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