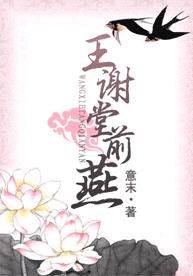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 的研析与索隐-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他终于如愿——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致他肉身于死亡的,不是什么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灵魂。难怪“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卢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验尸官在死因栏上写“心脏麻痹”,并没错误。
这,便是卢先生灵和肉的悲剧故事。由于他本来是那样一个温柔、高尚、贞洁的人,他突然间的直线堕落,以及灵肉相互的毁灭,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悯。而美好的过去,和丑陋的现在,两者之间的对比对照,就是这个短篇小说的主题。
我已提过,细品这篇小说,我们会惊于作者的写实能力。里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跃纸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写,也是十分逼真有力。我们随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绍描写洗衣妇阿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这样活泼生动的描写,不仅把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同时也酿造出一种有点夸张滑稽的语气,反映出叙述者日常的生活态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个写实能手,但他并不单单为了写实目的而写实。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伟大的作家,例如法国写实大师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过,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脱离,独立存在,不与情节动作或小说主题发生关联。这却是现代小说写作的一大忌讳。
我们如果把《花桥荣记》这篇小说,硬邦邦地解释为卢先生的故事,则作者让老板娘噜噜苏苏道出自己生活琐事,又介绍描写李老头子、秦癫子等广西同乡顾客,就好像也犯了巴尔扎克的毛病。小说六节中的第一节,事实上就和卢先生毫无关系。可是老板娘这些好似无谓又无目的的絮聒,实际上都是有作用的。
贯联这篇小说的大小细节,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题意识。这一主题意识,从小说的开头,一直穿流到小说的末尾。试看小说开始几句: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说结尾几句:
我好指(照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
如此,小说以爷爷的花桥荣记开始,又以爷爷的花桥荣记结束。首尾都是有关花桥的光荣过去的记述,难怪作者取名为《花桥荣记》。小说的起点和终点,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绕一个圆圈,又回返到原来的地方。而循着情节的圆周,潜流于内的,就是“想当年”的感慨意识和乡愁意识。
确实,这一主题意识,即“今不如昔”的感触,在小说里一再起伏出现。我在这篇论文开头,已经提过,《花桥荣记》一篇,采用比较明显的方式呈示主题。我们确可轻易从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对比的明显例子。小说开头,在介绍爷爷那家“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的花桥荣记之后,叙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而她现在这么个“春梦婆”,当然不比在桂林时那“有名的美人”。来饭店包饭的李老头子,“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可是现在流落在台北,又老又病,被儿子遗弃,最后上吊一死,另一个秦癫子,“在广西荣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可是现在,在市政府调戏女职员,被开除,又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额头开花,最后跌进阴沟里淹死。老板娘一心向往代表“过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现在”的台北:
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过,就卢先生而言,“今”与“昔”的界线,是他来台十五年后理想之破灭。而我已详细讨论,理想破灭之前之后的他,是怎样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带领学生过街这同一件事,来比较今昔:从前他极有耐心,像一只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后来他变得暴躁易怒,甚至动手打人。卢先生之前后判若二人,当然就是这篇小说今昔对比主题的最有力的呈现。
小说结尾,老板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卢先生少年时期和罗小姐合照的相片。“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这样年轻纯洁的模样,和老板娘初见卢先生时所见的“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之模样,之间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们再拿他堕落以后染发抹膏的小丑模样来相较,这一尖锐对比,刺激得令人心酸。过去,卢先生心灵恋爱的罗家姑娘,长得“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这样一个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体终于姘上的“肉弹弹”泼辣浪妇,真是有天地的差别。
总而言之,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表达“今昔对比”主题的方式,是多方面进行的:
一、藉卢先生的故事来呈现主题。
二、藉叙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来呈现主题。
三、藉李老头子、秦癫子等配角遭遇来呈现主题。
四、藉叙述者的唠叨和她对人对事的主观评语来呈现主题。
而今与昔的对比,就是肉与灵的对比,就是俗垢与纯净的对比。由于时光不断流逝,不肯暂停,没有人能长保青春,不受年岁的腐蚀污染,花桥荣记位于“长春”路底。卢先生在“长春”国校教书,当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讽。
另有一点,也顺便说一下。像这篇小说的这样一个结尾内容,即以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来引发今昔之感,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流于“感伤过度”()。白先勇却十分机巧地回避了这个陷阱。他回避的妙法,是用叙述者的现实态度,来中和题材的感伤性,我说过,老板娘来卢先生住所的动机,完全现实,便是想拿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的饭钱。她看到这幅照片,全是出于偶然的。她根本无意寻找“纪念品”。而她对这幅照片发生兴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尽管她很仔细的检视相片里的两个后生(如此我们才见到卢先生少年时的样子,而得以比较今昔),并对这一对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长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来”,可是她对照片人物的这份兴趣,是一时的,鉴赏性的,无关痛痒的。要不是里面的背景,能让她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自己的过去,夸耀她爷爷那家“招牌响当当”的花桥荣记,那么,卢先生房里就是真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她也不会想到要把这幅照片带走的。
其实,说起来,不仅是小说结尾,而是卢先生的整个悲剧故事,单就题材本身来说,过于感伤化(),过于戏剧化()。白先勇却十分巧妙地藉由叙述者现实、轻松、风趣的“语气”或“语调”()控制抵挡住这两种趋向。大凡一个小说作者,写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不在于选用什么样的题材,而在于如何处理他所选用的题材。
《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
《秋思》是《台北人》中最短的一篇,全文仅四千字左右。这篇小说不但字数少,情节动作的规模也小,整个故事,只是主角日常生活的一小切片,以及她片刻之间的流动意识。
然而这个“袖珍”短篇,却也和别篇一样,具有《台北人》整体的一贯特色,兼具生动的社会写实和深刻的象征含义。《秋思》同时也是《台北人》里社会讽刺意味较浓的一篇。
情节动作之推演,所占的时间,大约不出半小时。主角是上流社会的华夫人——抗日时期一位大将军的未亡人。华将军显然是在抗日胜利之后大陆沦陷之前的一个秋天,在南京患喉癌去世。撤来台湾后,华夫人住在台北,依旧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她有一个女儿,住在外国,显然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华夫人常和同她年龄相近的几个上流社会太大,相聚打麻将。其中一个万大使夫人,由于丈夫不久要外放日本,十分勤快地学着日语,并模仿起日本人的举止风俗来。华夫人免不得和她社交周旋,内心却对她怀着轻蔑与妒恨。
小说开始时,华夫人正准备赴约,到万公馆打麻将。年轻的美容师林小姐,已替她做完脸,正在小心翼翼替她修剔手指甲。两人随意交谈,林小姐十分羡艳地称赞华夫人皮肤的美色,并悄悄告诉她,万夫人不久前动过拉面皮的美容手术,结果不大成功,最近额头又有点松下来了。又说万夫人涂眼圈膏,是为了遮掩眼袋子。两人说着发笑。她们对照着华夫人要穿戴的宝蓝色真丝旗袍和翡翠手饰,细心斟酌,选择指甲油的颜色。不久,万公馆打电话来催,华夫人便穿戴齐整,又对镜端详一番,觉得头发梳得太死,林小姐便用一把尖柄子的梳子,替她挑梳那高耸的贵妃髻,突然华夫人在镜中看见林小姐在她右鬓上角头发里翻找,于是她颤然明白,头上又出现了白发。林小姐又替她拢了好几下头发,把白发掩藏在里面,不露出来,她才走出房门,去乘她的私人汽车。
在花园里,走向大门的时候,她忽然在一阵秋日凉风中闻到一股冷香,那是从墙东一角盛开的几十株“一捧雪”发散出来的。“一捧雪”是最上品的白菊花,却十分娇弱,在台湾很不容易养活。去年种下去,差不多全枯死,华夫人叫花匠敷了一春天的鸡毛灰,才活过来,突然间白茸茸一片,开得十分繁盛,万夫人因为跟日本人学插花,曾开口向她讨几株插盆。华夫人心里极不甘愿把这些尊贵的白菊送给她,但因万夫人嘴巴十分刻薄,她怕遭她哂笑,只得勉强去采几株,当她用手把一些枝叶拨开,却赫然看见,在一片繁花覆盖下,许多花苞竟已腐烂死去,冷香之中夹杂着一股花草腐烂的腥臭。这股腥香,使她联想起她丈夫病死前的情景,因为,当时他床头几案上插放的三枝“一捧雪”,也发散出同样的气味。那三枝大白菊是从他们南京住宅花园里采的,那时一共种有百多株。华夫人特别记得,抗日胜利那年,“一捧雪”开得最是茂盛。那年,她丈夫带领军队开进南京城的当儿,民众又哭又笑,热烈欢迎。英俊无比的华将军,挽着她走进花园,在白浪一般翻掀的“一捧雪”前面,异常温存地把一杯酒敬到了她唇边。
仆人报告车子已经开出。华夫人走向大门,临行,她吩咐老花匠黄有信,去把“一捧雪”的残苞修剪一下。
以上就是《秋思》情节之大概。
这篇小说的结构,前后可以分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