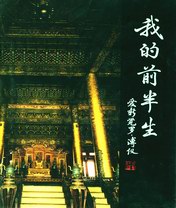半生为人-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文革’结束了!”这两个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地点和场合的故事使我震惊。他们的,还有你的,对于这段经历至今的耿耿于怀,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即便走得出历史的废墟,也走不出心灵的阴影。亦如你为了让儿子摆脱“虚伪与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从语言到地域彻底把他与父亲及其中国背景隔绝开来一样,我的那个并不缺少才华与豪情的朋友,宁愿在他乡抑郁而死,也不愿回故乡苟且偷生。
曾经与不止一个朋友有过共同的读书体验,书中的故事常常会惹我们哭。回想起来,几乎没有让我不哭的小说,托尔斯泰使我激动而哭,陀斯妥耶夫斯基使我悲伤而哭,车尔尼雪夫斯基使我感动而哭。《红字》《牛虻》都无不让我哭得昏天黑地。同时,我们也都觉得奇怪,现在的孩子不哭。儿子让我意外地卒读了罗曼·罗兰的四卷本巨著,但是他不兴奋也不感动,而是考证主人公与贝多芬的异同,然后总结性地宣布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革命说教过时了!”但是,他会为另外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而动容,比如披头士或X…Japan的音乐。他宁愿花几百元到现场挥动闪光棒直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而我们不管多么反叛,当SARS这样的灾难降临之时,却还有去当志愿者的冲动。
我不知道你和你儿子父亲的故事,但是可以肯定,你的儿子也会慢慢长大,从你为他蔽荫的房子里走出去。也许有一天,正是因为你的封锁给他造成的好奇,使他神差鬼使地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权知道真相,也一定能够知道真相。你希望他像牛虻一样遭受致命的打击而破碎,还是希望他在真实中慢慢成熟?吃着巧克力、穿着耐克、玩儿着电脑游戏、看着动画片、听着披头士长大的儿子们,也许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反右”与“文革”,不需要学习如何写“检举信”与“检讨书”,也不需要分辨政治上的正确与不正确,以及道德上的是与非。但是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他不能不面对生活中的美与丑。毫无疑问,专制腐败草菅人命的制度是丑行,“虚伪与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是丑行。但我相信,美国也不是一块净土。相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标准来说,审美是更稳定更恒久的标准,只是它也许比任何标准都更高更完美,因而更加难以企及。
前几天,我和儿子一起去观看美国《国家地理》图片展,我惊奇地发现,一百多年来,这个非盈利性机构(而不是私营公司)的领导人,由一个家庭(而不是家族)的四代人接连担任。其中有一幅黑白图片,画面是发明电话的老贝尔拉着孙子的手。这个七八岁大的男孩儿,正是现任董事长的父亲。这是一种怎样的延续与传承啊!正是这种超越了政治与社会的、由精神与审美连缀而成的链条,使得一本貌似科普的杂志,充满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瑰丽的审美色彩,成为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它能让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着迷;所以,才会有一个中国母亲和她的儿子一起,在那些图片前流连忘返,对一本异国的杂志赞叹不已。
自私地说,一个不想失去儿子的母亲,一个想拥有儿子的母亲,在审美层面上的沟通,几乎就是惟一的途径了。当然,这也是冒险。人与人是如此的不同,DNA又是如此的神秘。我们得有支付代价的心理准备。
感谢你的来信,特别感谢你的问题,让我静下来想关于我和儿子共同成长的经历。
徐晓
二○○四年元旦
…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1
…
二○○一年八月去美国旅行,因为非常偶然的原因被一个姓魏的朋友带到了新泽西州一个风景如画的住宅区。它远离闹市,幽静自然是好,但生活上很不方便,我做客那家被称为“阮太”的女主人七十多岁了,还要自己开车到几公里远的地方购物。几年来,高尔泰就在这里读书写作,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就是这个阮太,无意间说到高尔泰是她家的邻居。对于关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人,高尔泰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人们对于他的敬意来自于他在社会上两度昙花一现。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在《论美》一文中,高尔泰提出了主观美学的观点,挑起了一场美学大辩论,并因此被打成了右派;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一方面,除了继续表达因为五十年代不能在场而没有表达完整的美学思想,他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文章,开启了一代青年与学人;另一方面,当人们对潮水般涌来的新思潮应接不暇时,他始终以理性主义的精神,对于保守与创新、西方与东方、世界与民族等重要问题发出拨乱反正的声音,并因此在“反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中国现有的美学史或者文学史,不知道会不会给他的著述一点儿篇幅,或者只提到他的名字,或者不公平到了干脆连名字都被省略了。而他的上辈人以及同辈人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等等,他们的名字和著作,却肯定会远远比他辉煌和隆重。
我对高尔泰的敬意还不止于此。从九十年代中起,我从海外复刊的《今天》杂志陆续读到高尔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系列散文。杂志一到,先找他的名字,像是要过把瘾,一口气读完,再读第二遍,然后从心底里感叹:高尔泰就是高尔泰!
所以当吃完了阮太包的饺子,说打电话给高尔泰时,我又高兴又忑忐。因为一直以来都有人说,这个人有点儿怪!不知道电话那边都说了些什么,总之,阮太说他读过我的文章,很愿意与我见面。这已经足够让我受宠若惊了,尽管见面必须在晚十点以后。因为他的妻子浦小雨在邮局工作,每天上夜班,那时正在休息。
早听说高尔泰瘦,现在还是瘦,但筋骨好,精神也好。尺把长的头发扎在脑后,一副仙风道骨的隐士模样。他迎出来,讷讷的,有几分拙,加上听力不好,说话声音特别大。也像是有人曾经说过的,没有一点儿所谓知识分子驾势。一个曾经在八十年代到他成都的家里去过的朋友说,那时他是家徒四壁,除了床和桌子什么家具都没有,窘困到买不起肉和水果!是啊,悉数他的经历,出生和读书都在江苏,毕业后工作在兰州,一九五七年“反右”后被送到甘肃省夹边沟农场,一九六二年结束劳教到了敦煌大漠,一九七八年平反到一九八二年,四年间他在兰州-北京之间打了个来回,然后是天津、南京、成都……如此动荡的生活,怎么容得下一个安稳的家?如今他有了可以放置桌呀几呀的地方,房间仍然是空荡荡的。他说,这样方便画画。我恍然,噢,他不只是美学理论家、作家,还是个画家。后来读了书稿才知道,他原本就是学画的,可偏偏在美学上出了名,歪打正着地,他一写文章就招灾惹祸,一画画就逢凶化吉。七十年代初,他被迫画了百多幅巨型毛像,因此逃离了夺命的夹边沟。
我们之间惟一的联系是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散文,对于他的文章除了赞美还是赞美,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他告诉我,他正在写《寻找家园》第二部,已经完成的第一部希望能由我带回北京出版。此前已经有几个人与他联系,但出于信任,他愿意由我做这本书的代理,我深知这份托付的分量。因为不用电脑写作,稿子只有一份,我们商定,第二天由阮太开车去复印并寄到我下一个落脚的城市。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第一次通读了《寻找家园》的全稿。本来难以忍受的行程,因为阅读的投入变得不值一提。我意识到,这是我编辑生涯中遇到的最有价值的作品。在这本书两年多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反复地读《寻找家园》,也反复地读高尔泰这个人。他的著作让人联想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著作中的他,又让人联想到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知识界来说,高尔泰实在是一个异数。
高尔泰一直是孤苦的。在夹边沟农场的日子不用说了,“文革”中,他从敦煌被抽调到酒泉办展览,体弱多病的妻子李茨林带着女儿被下放到农村,因为交通不便病倒了无法医治,当他用了三天时间赶到时,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妻子死时怀着八个月大的胎儿,留下个三岁大的女儿。从此,他带着女儿,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这个苦命的孩子最终没有逃离母亲的命运,重点中学免试保送的成绩,却上不成大学,九十年代初死于非命。母女俩死时都只二十多岁。高尔泰的第二次婚姻在法律上维持了十五年,其中为离婚分居七年。另外的时间塞北江南,相隔万里,如果按每年见一次面,每次一个月算,加起来一共八个月。离婚后两个女儿跟母亲,如今女儿已经三十上下,父女隔海相望,起码有十五年没见过面。中年觅得知音,再婚却困难重重,婚后虽心心相印,但贫病交加,第三任妻子又险些丢掉性命。他把如此黯淡的生活,都当作命运的恩赐领受下来。
世俗生活的孤苦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的绝对孤独。《论美》完成之前,他曾把疑惑与苦闷写信给傅雷,让他失望的是,傅雷的回信像支部书记打通思想:口口声声追求真理,真理早就被证明了,就在眼前,你却视而不见,难道是聪明的吗?因为越想越不服,越想越堵得慌,于是奋笔成就了《论美》。完成之后,他曾就教于当时西北师范大学院长徐褐夫,这位来自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虽然态度极为诚恳,但是观点却让他无法苟同。文章作为批判的靶子刊出后,大名鼎鼎的朱光潜、宗白华、侯敏泽等美学权威都发表了批评意见,直至被别有用心地利用,把唯心与唯物上升到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怎一个“地老天荒无人识”!
…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2
…
中国几十万右派,被整死的有之,被压垮的有之,劫后辉煌的有之,辉煌之后忘乎所以的亦有之。惟有高尔泰,劫难宿命般地追赶着他,却丝毫没有磨钝他触摸自由的敏感神经。与我们需要经受觉醒的镇痛的一代人不同,他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十五岁,带着山里少年的野性本色,他从家乡封闭的山里走进一个个同样封闭的边远小城。他拒绝几十个人把同一个模特画得一模一样。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拒绝会成为一个“事件”。他更不明白,一向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居然和别人说一样的话。十六岁,读《大卫·科波菲尔》,他评价说,很美,很生动,但不深刻。理由是,密考伯最后当了印度总督,但没一个英国人问一问,英国有没有权力统治印度,如果是俄国作家,一定会弄一个人出来问一问的。十九岁,他自问:“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二十岁,他挑战权威,开拓了中国美学最富生命力的学派。从大自然的怀抱中走出来的少年,没有偶像,没有权威,没有导师,他的精神家园是自给自足的。为了偷吃几颗沙枣,他在一片沙丘中走迷了路,他想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却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正则艺专》《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