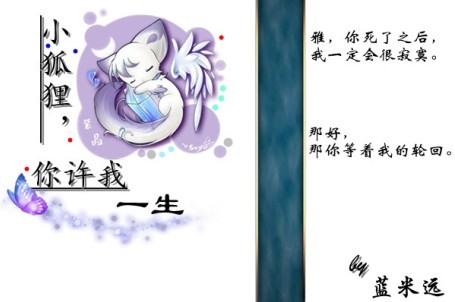季羡林先生-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接着,文章便开始介绍“大跃进”“秒新分异”的情况:
最初在报纸上读到有人想亩产小麦千斤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满是问号。然而不久亩产千斤的纪录就出现了。不但出现了,而且像给风吹着一样,纪录一天天升高。有的时候晚报上的最高纪录,第二天早晨就被打破。有一些科学家也着了慌,他们用最高深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来证明,小麦亩产最高产量是三千斤;然而事实却打了他们一记耳光,纪录一直升到七千多斤,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现在有许多农民和科学家已作出计划,明年的产量不是以千斤计,而是以万斤计。
稻子也是一样,早稻的最高纪录已经达到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竟达到四万三千多斤。有些人觉得这些数字简直是神话,他们有点半信半疑。信嘛,他们不能够想象,在那有限的一点点地方,这么多的稻子如何摆得下;疑嘛,他们又知道,中国报纸从来不说谎话。不管这些人怎么想,我可以告诉诸位侨胞:这些纪录还只是牛刀小试,不用说明年,就是在今年,也还会有许多地方打破这一纪录。至于最高纪录究竟是多少,现在很难预言;我只希望侨胞们有一个思想准备,将来不至于过分吃惊。
季羡林说的水稻亩产四万三千多斤的纪录,果然是“牛刀小试”。1958年9月18日,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上赫然登载了广西容县水稻亩产达十三万斤的报导,放了一颗特大“卫星”。这个鲜为人知的容县顿时名闻天下。在全国人民为这颗特大“卫星”欢呼雀跃的时候,也让世界人民笑掉了大牙。
…
狂热的1958年(2)
…
“大跃进”、“浮夸风”、“蛮干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骇人听闻的地步,全国人民却浑然不觉,依然沉醉在“放卫星”的狂喜之中。只有当时的苏联沉不住气了,他们说,把一亩地全铺上粮食,铺一米厚,也达不到中国报纸上吹嘘的产量。这本来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说法,然而却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普遍反对,被中国老百姓嗤之以鼻。就连季羡林这么实事求是的人,也从没有怀疑过报纸上的消息。他说:“我听到‘上面’说:全国人民应当考虑,将来粮食多得吃不了啦,怎么办?我认为,这真是伟大的预见,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季羡林在文章里还向侨胞们报告了北大大跃进的惊人成果:
只是化学系一个系就完成了研究项目一千多项,经过严格的审查,其中七十几项超过了国际水平。……我所在的东语系,在短短的二十几天以内,已经编出了汉朝词典、朝鲜外来语词典、华日词典、越汉词典、乌尔都汉语词典、印地汉语词典等等。这些词典,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质的方面来看,都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些词典也许编出来了,但是当时并未出版,其中有的至今也未出版。至于它们是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就只有天晓得了。
引述季羡林在“大跃进”年代写的文章,目的只在说明,季羡林也是一个凡人,他当时同“六亿神州”一样幼稚,并不比别人高明,也没有金睛火眼、远见卓识。他虽是留过洋的教授,但是在“全民无意识”的狂热社会环境中,知识和智慧也帮不了忙,一个留过洋的教授丝毫不比一个文盲更清醒。
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神话。接着来的便是三年“自然灾害”。人们普遍挨饿,浮肿病四处蔓延,校医院门口排上了长龙。北大不得不“减少生产劳动、停止剧烈的文化体育活动、暂停体育运动会、严格控制会议。”党委的中心工作是“办好食堂,劳逸结合”,从全校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到食堂工作,口号是:“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
两年前燕园里大跃进热火朝天、车水马龙的风光顿时销声匿迹,眼下是一片偃旗息鼓,冷清萧条的景象。
季羡林曾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说:“我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说过。”实际上,在这段“困难时期”,季羡林的精神面貌反而格外地好,从他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散文这点上,便可以看出来。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文再说。
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当务之急应该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就惹了大祸。一场反“左”变成了反右。“反右倾”运动从上而下,铺天盖地而来,又打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
季羡林曾说过:“我一生最佩服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员。这四个人是: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和彭德怀。”
众所周知,这四个人虽然政治信仰不同,职业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爱国者,都是敢讲真话的硬骨头,都是因为讲真话而蒙冤受屈的。从季羡林“最佩服的人”,也可看出季羡林本人的性格和信念。彭德怀的蒙冤,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在文章里特意写了一段话来表达自己对彭德怀的崇敬之情,他说:“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会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庐山会议后,“大跃进”狂飙再起,跃进,跃进,再跃进,直到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发烧的头脑才暂时冷静下来。可是,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刚刚好转,又开始了继续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传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弄得全国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最后忽然发现“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北大一向是政治最敏感的地方,任何一个运动都不能少:“反右倾”、“拔白旗”、“干部下放”、“参加劳动”、“教育改革”、“学毛著”、“学雷锋”、“反修防修”等,又经过了数不清的运动。北大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运动,都已经锻炼成了“运动健将”,行家里手。无非是这次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大家都习惯了这一套,不再感到新奇和害怕,反而变得麻木了。季羡林也跟大家一起,在时紧时松,时强对弱的运动中度过了四五年乱哄哄的日子。
…
啊!朗润园(1)
…
季羡林在中关园一公寓一住就是十年,始终是单身一人。到了1962年,叔父去世,他便把妻子和婶母接来北京同住。可是中关园一公寓的房子住不下三个人,于是学校便分配给他朗润园公寓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当时13公寓刚建成,季羡林是头一家搬进去的。
朗润园在北大校园的东北部,这里原来是明清名园之一,属于圆明园的一部分。1900年圆明园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朗润园也变成一片荒芜,只剩下一弯湖水,一座土山。1962年北大开始在朗润园旧址修建职工宿舍,共建了六座,结构一样,都是四层,两个门洞。五座在湖东边,由南向北排列8-16公寓;在湖的北部偏西,孤零零地矗立着的,就是朗润园13公寓。
在燕园院墙里面,还有一个园叫燕南园,与朗润园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燕南园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围住,园中错落地建了十六幢西式小洋楼,楼周围是小花园,楼与楼之间有水泥铺的小路相通,满园树木参天,绿草如茵,分明是一派欧式庭院风格,与燕园内整体的中国古典式建筑迥然不同。
燕南园地处校园中心地带,围墙外就是图书馆、学生宿舍、商店、食堂、篮球场,人声鼎沸,喧闹异常,但是园内总是静悄悄、空荡荡的,人迹罕见。教授们住在这里真是闹中取静,想必会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感受吧。这里一向被视为燕园的“世外桃源”。自燕京大学建校以来,学校著名的教授大都住在燕南园。到了1962年,像著名教授冯友兰、王力等也都住在这里。冯友兰的“三松堂”也因此地而得名。80年代初,季羡林曾经有希望住进燕南园,可阴差阳错未能如愿,为了纪念这段因缘,他特意把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燕南集》。
可是,时移事易,事隔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人人向往的燕南园,因年久失修,更兼“文革”期间抢占住房的破坏等原因,已经变得草木凋零,小楼颓败,杂草丛生,一幅“废园”的凄凉景象。与其相反,当年荒凉的朗润园,如今却是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一派旖旎风光。朗润园现在是北大众园中最美的一个园。有一次,季羡林同一位老朋友去庐山归来,老朋友到他家拜访,看见朗润园的风景,对他说:“你家里有这么好的风景,还到庐山去干什么?”可见朗润园给人的印象有多美。
季羡林自从搬进朗润园13公寓后,便结束了三十多年的单身生活,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季羡林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
季羡林一家给左邻右舍的印象是忠厚俭朴,古风古貌,还带点乡土气。三位老人的人缘极好,他们受到朗润园老人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与邻里的关系也很融洽,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季羡林人称“季爷爷”,妻子彭德华人称“季奶奶”,婶母人称“老祖”。孩子们见到他们,大老远就喊:“季爷爷好”,“季奶奶好”,“老祖好”。三位老人也会含笑回应一声:“真乖,好孩子。”
季羡林家里也是一团和气。季羡林自己说:“叔父去世以后,老祖同我的妻子彭德华从济南迁来北京。我们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从来没有半点龃龉,总是你尊我敬。自从我六岁到济南后,六七十年来,我们家从来没吵过架,这是极为难得的。我看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为过。”
老祖虽然年迈,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操持家务主要靠她。老祖天天背着一个大黑书包去采买食品菜蔬,成为朗润园的美谈。
妻子虽然文化不高,只念过小学,对季羡林搞的这一套学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也从来没想知道,在这方面她和季羡林之间可以说毫无共同语言,但是,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她同婶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使季羡林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治学中去。
季羡林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来说明他家的幸福生活。他写道:“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食前方丈,杯盘满桌。烹饪都由老祖和德华主厨。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对这样的家庭,一切誉美之词都成了多余,都会黯然失色。
此时,季羡林的女儿婉如、儿子延宗都已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并且都成了家。每逢节假日,女儿和儿子带着家人来朗润园团聚,季羡林家三间屋子便人满为患。祖孙三代,老老少少挤在一起,有说有笑,边吃边聊,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季羡林这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烦恼之事,一扫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