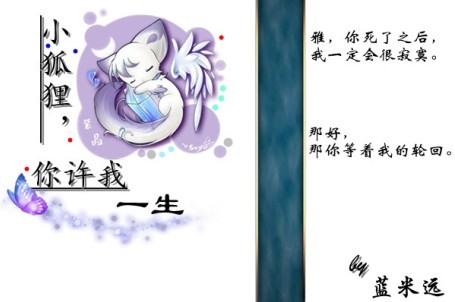季羡林先生-第6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此,我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
20世纪以前,尽管我们的正史和杂史上有关于中国文学的记载连篇累牍,可是专门的中国文学史却是没有的。有之,是20世纪初期始,可能是受了点外来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颇出了一些《中国文学史》,书名可能有一些不同,但内容却是基本上一样的,水平当然也是参差不齐。连《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出了几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五十年来,更出了不少的文学史,直至今日,此风未息。应该说,这都是极好的事情,它说明我国学术界的繁荣昌盛。
但是,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同上面讲到的《中国通史》一样,《中国文学史》的纂写也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极“左”思潮一向是同教条主义、僵化、简单化分不开的。在这种思想左右下,我们中国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无疑也受到前苏联很大影响。50年代,我们聘请了一些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来华讲学。他们带来的当然带有苏联当时的那一套教条,我们不少人却奉为金科玉律,连腹诽都不敢。前苏联一个权威把极端复杂的、花样繁多,然而却又是生动活泼的哲学史上哲学家的学说,一下子化为僵死、呆板、极端简单化了的教条。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历史上文艺理论的一个指针。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研究焉能生动活泼、繁荣昌盛呢?
在外来的影响之外,还有我们自己土产的同样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教条主义的东西。不错,文学作品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却不能只一味强调政治标准,忽视艺术标准。在其时,一般中国文学史家,为了趋吉避凶,息事宁人,就拼命在第一条标准上做文章,而忽视了这个第二条艺术标准。翻看近四五十年来出版的部头比较大、影响比较大的《中国文学史》或是类似名称的书,我们不难发现,论述一个作家作品的政治性或思想性时,往往不惜工本,连篇累牍地侃侃而谈,主要是根据政治教条,包括从前苏联来的洋教条在内,论述这位作家的思想性难免牵强附会,削足适履。而一旦谈到艺术性,则缩手缩脚,甚至了了草草,敷敷衍衍,写上几句倒三不着四的话,好像是在应付差事,不得不尔。
根据我个人的浅见,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艺术性绝对不应忽视,甚至无视,因为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元用处,这样的作品决不会为读者所接受。有一些文学作品,思想性十分模糊,但艺术性极高,照样会成为名作而流传千古,李义山的许多无题诗就属于这一类。可惜的是,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忽视了作品艺术性的分析。连李白和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文学史的作者对他们的艺术风格的差异也只能潦草地说上几句话,很少有言之有物、切中肯綮的分折,遑论其他诗人。
这样的文学史是不行的。因此,我主张,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
新时期文坛骁将(10)
…
美学研究的根本转型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但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体系。“美学”这一门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是受到西方影响之后才成立的。这个事实恐怕是大家所公认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有一段时期,美学浸浸乎成了显学,出了不少人才,也出了不少的书,还形成了一些学派,互相争辩,有时候还相当激烈。争论的问题当然很多,但主要集中在美的性质这个问题上:美是主观的呢?还是客观的?抑或是主客观相结合的?跟在西方学者后面走,拾人牙慧,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走进了死胡同,走进了误区。
何以言之?按照西方语言,“美学”这个词的词源与人的感官(senseorgan)有关。人的感官一般说有五个,即眼、耳、鼻、舌、身。中国和印度等国都是这样说。可是西方美学家却只讲两官,即眼与耳。美术、绘画、雕塑、建筑等属于前者,音乐属于后者。这种说法实际上也可归入常识。
可是,中国美学家忘记了,中国的“美”同西方不一样。从词源学上来讲,《说文》:“美,羊大也”羊大了肉好吃,就称之为“美”。这既不属于眼,也不属于耳,而是属于舌头,加上一点鼻子,鼻子能嗅到香味。我们现在时时都在讲“美酒”、“美味佳肴”等等,还有“美食城”这样的饭店。这些在西方都不能用“美”字来表述。西方的“美”不包括舌头和鼻子。只要稍稍想一想,就能够明白。中国学者讲美学,而不讲中国的“美”,岂非咄咄怪事!我说,这是让西方学者带进了误区。
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些美学家谈论美学转型的问题。我认为,这谈得好,谈得及时。可惜这些学者只想小小地转一下型,并没有想到彻底走出误区,没有想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
我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陆续读过一些美学的书,对美学我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外行。但是浅尝辄止,也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内行,只能说是一个半瓶醋。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半瓶醋才能晃荡出声。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提出了一个主张: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决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文艺理论在国际上“失语”问题
近七八十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文艺理论时有变化,新学说不时兴起。有的延续时间长一点,有的简直是“蟪蛄不知春秋”,就为更新的理论所取代。我套用赵瓯北的诗句,改为“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国际文艺论坛上的喧嚣闹嚷声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有人就形象地说,中国患了“失语症”。
难道我们中国真正没有话可说吗?难道国际文艺理论的讲坛上这些时生时灭的“理论”就真正高不可攀吗?难道我们中国的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就真正蠢到鸦雀无声吗?非也,非也。我个人认为,其中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有一些学者过多地屈服于“贾桂思想”,总觉得自己不行;同时又没有勇气,或者毋宁说没有识见,去回顾我们自己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水平极高的旧的文艺理论宝库。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所使用的”话语”,其基础是在我上面提到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与植根于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我们面对艺术作品,包括绘画、书法、诗文等等,不像西方文艺理论家那样,把作品拿过来肌掰理分,割成小块块,然后用分析的“话语”把自己的意见表述出来。有的竟形成极端复杂的理论体系,看上去令人目眩神摇。
我们中国则截然不同,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或耳听一段音乐,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手执解剖刀,把艺术品或音乐分析解剖得支离破碎;然后写成连篇累牍的文章,使用不知多少抽象名词,使读者如坠入五里雾中,最终也得不到要领。我们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或一般读者,读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诗文,先反复玩味,含英咀华,把作品的真精神灿然烂然映照于我们心中,最后用鲜明、生动而又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读者读了以后得到的也不是干瘪枯燥的义理,而是生动活泼的综合的印象。比方说,庾信的诗被综合评论为“清新”二字,鲍照的诗则是“俊逸”二字,杜甫的诗是“沉郁顿挫”,李白的诗是“飘逸豪放”;其余的诗人以此类推。对于书法的评论,我们使用的也是同一个办法,比如对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论之者评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多么具体凝练,又是多么鲜明生动!在古代,月旦人物,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不赘述。
我闲常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除了《文心雕龙》、《诗品》等少数专门著作之外,竟没有像西方那样有成套成套的专门谈文艺理论的著作?中国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又派别繁多,议论蜂起的。许多专家的理论往往见之于《诗话》(《词话》)中,不管什么“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境界说”等等,都见之于《诗话》中;往往是简简单单地几句话,而内容却包罗无穷。试拿中国——中国以外,只有韩国有《诗话》——《诗话》同西方文艺理论的皇皇巨著一比,其间的差别立即可见。我在这里不作价值评判,不说哪高哪低,让读者自己去评论吧。
…
新时期文坛骁将(11)
…
这话说远了,赶快收回,还是谈我们的“失语”。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扳挺不直,被外国人那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我个人觉得,我们有悠久雄厚的基础,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卑,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决不会再“失语”下去的。但是兹事体大,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多思考,勤试验,在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思想指导下,才能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任何掉以轻心的做法都是绝对有害的。
——《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季羡林关于文化、学术的新思考、新见解、新观点,还有一些,不具引。上面摘引的这些观点,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重要,又都是当前学界十分关注而又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季羡林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表态。对他这些观点的看法,必定是见仁见智的。季羡林既有勇气公开自己的看法,就不会惮于辩论或争论。如果真的形成一场大辩论,这肯定对推动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5、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二十余年中,季羡林一直是文化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甚至可以说,在许多领域中他是一位领军人物,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新时期的文化潮流,勇往直前。季羡林在此时期内,参加和领导过多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的弘扬,中外文化的交流,都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此,择其要者简介如下:
l978年,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开始启动,这是新时期开始后的第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空前壮举。姜椿芳总编辑盛情邀请季羡林参加编撰工作,出任其中《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当时,季羡林在北大身兼数职,本身有教学科研任务,还在翻译巨著《罗摩衍那》,工作十分繁重。但是,季羡林认为此项工作意义重大,于是挺身而出为姜老分忧。季羡林与《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冯至合作主编这卷书。他们二人本来就是挚友,现在两人配合默契,克服了重重困难,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编完了。198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