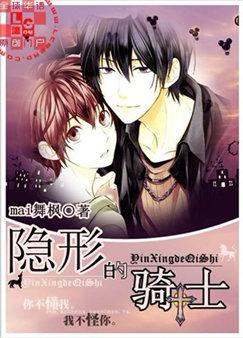隐形伴侣-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让她上你的驾驶楼去吧,她受不了了。”陈旭不由分说,把她连抱带夹地塞进了驾驶楼。
“不会坐‘热特’,算不了农场的人。”小司机嘟哝了一句。“哎呀,小心点,别碰了我的鸟。”他突然伸腿护住了座位下的一只盒子。
“什么鸟呀?”车上养什么鸟。
“前几天在水库翻地抓到的,它受伤了,我给它抹了红药水,不知能不能养好。养在宿舍里,早让那帮人烧吃了。草甸子里鸟可多了,什么颜色的都有……”车灯映出他脸上一层淡淡的茸毛。
肖潇看不见那鸟的颜色,座位好高。真有闲心,开车还养鸟!
车又开了,颠簸并未减轻,只是有了抓手,便没有了恐惧。刚才他说什么?当然,谁没有坐过“热特”,谁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颠簸。
“……新书,现在有啥样新书值得半夜去排队?”小司机哼了一句,并不看她。
他要再往下问,就露馅儿了。陈旭干吗瞎说?不会说……说什么?说回杭州?可他为什么非回杭州呢?下午余指导为什么叫陈旭去谈话?……昨天晚上分场打群架,同陈旭有什么相干?陈旭又没动手……
车剧烈地晃动,车头歪到路边去了。
“操!”小司机骂骂咧咧地踩油门,勒紧了方向盘。
肖潇觉得他有些吃力,生出些同情。
“开车多久了?”
“嗯……十来天吧!我原是开‘东方红’的。”
“嗬,你学得好快哟!”
“这有啥难?机务排的老职工说,把馒头插在操纵杆上,连狗都会开,这玩意儿!”他撇撇嘴。
他竭力地说着东北话,肖潇却听出那南方话的尾音。
“宁波人?”
“温州。你们呢?”
“杭州。你……才十……六岁吧!”
“不,十五。”
“这么小也支边啊?”
“不小了。我爸爸……”他把后半句咽回去了。
车猛地一震,她弹起来。车轮子颤抖着,翻腾着,好像在宣泄心中的什么怨愤,从灰暗的公路上碾压过去。
什么碎了?是窗玻璃?热水瓶?瓦片?还是那只雪白的天鹅蛋?她从炕上裹着被单跑到屋外去时,男宿舍门口已经摆开了战场。憧憧人影,翻滚蠕动,扭结成团,痉挛的手,蹿跳的脚,狠狠地踹着黑暗——黑暗竟有这样的弹性和忍耐力。似乎大树被飓风连根拔起,飞梭与车轮互相绞割;呻吟、呼救、吆喝、咒骂,像塌方的土块,惊心动魄地砸落。被击碎的玻璃碴像炮弹掀起的尘埃,没头没脑地扣下……一道寒光嗖地掠过,是铁锹、二齿子、炉钩子、镐头!有人跳上了草垛,又惨叫着跌下,屁股上尖利的二齿子像扎住了一堆湿马粪,铁锹从空中飞过,一顶开花的帽子落在地上。她一个趔趄,触到一条胳膊,黑乎乎的黏液,凉兮兮地爬到她手指上。
/* 4 */
《隐形伴侣》二(2)
“不许打人!”她扑过去。
“回去!”一只手粗暴地把她拉开,是泡泡儿,陈旭的影子。他上衣一颗扣子也没有,眼里冒着青蓝的烟。“这是男民兵训练。”他对她挤挤眼。
前天刚挂锄。鹤岗、双鸭山青年都回了家。连长呢?那个刘瞌,又喝醉了?谁来救救——救谁?谁打谁?
“服了你大爷不?”
泡泡儿的脚,踢在一个软软的物件上。一声惨叫。他为什么换上了球鞋?他一夏天都只趿着一双拖鞋。他根本没有球鞋,球鞋早在支边列车开车时掉在窗外了。他就是穿着拖鞋下的火车。冬天穿。
“子,服了你大爷不?”
“别打了,有理讲理。”一个瘦高个儿从人群中挤出来,穿一件深蓝制服。额下的镜片闪闪发光。
“管着我了?书呆子,走开!”泡泡儿歪着头看他,伸出一拳。
“打人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他喃喃,去捡眼镜。是邹思竹,原先和陈旭一个学校的。
又走过来一个人。“魏华!”有个女声尖叫。魏华是鹤岗青年,新提拔的副连长,这会儿鼻青眼肿,两片嘴唇像切开的西瓜。泡泡儿拽住魏华的衣角,狠狠向上一提,衣服翻起来,像一只布口袋,把他的脸儿整个套在里头,露出腰以上的胸、肋,赤裸裸无遮挡,听任炉钩、脚掌落在那黑黝黝的皮肉上……
她浑身冰凉,腿发软,牙齿打战。她想喊陈旭。陈旭呢?这样打下去魏华会被打死的。
有人冲过来,抱一床花被子,没头没脑地盖在魏华身上。一根棍子啪地落在她腿上。郭春莓,她的好朋友。她来干什么?她扑上去拉她,她死活不动……
“行啦,别打啦。”
一个声音从她头顶上传来。陈旭站在阴影里,冷冷地捋着头发,那头发根本就整整齐齐。刚才他在哪里?
他去找来了车老板,送魏华上场部医院。
子瘫在草垛下。那只天鹅蛋呢?一定是碎了,中午在地头就碎了……
“车快拐弯了。”小司机突然说。
“你说什么?”
“到地方了,你们该下去了。”
车毛手毛脚地停下来。在空中?海上?头晕目眩。
“新华书店在镇子大北头,门前有个便所。”小司机又探出身子来叮咛,“要是碰上老乡的马车,再搭一段儿……”
她忘了说谢谢,脸有些发热。幸而黑夜里什么颜色都涂黑了一遍。陈旭那个新华书店来得可真快,她可不会这么唬人。他们打架的时候他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快打完了他才出现?为什么非要偷偷地离开农场,匆匆回杭州……
“才坐了十来分钟车,走了七八里地。”陈旭望着“热特”跃入黑暗,把她肩上的书包摘下来,拎在自己手里。
十来分钟?倒好像横渡了一次大西洋。
/* 5 */
《隐形伴侣》三(1)
月亮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一只小小的、同镰刀头一样弯弯的月亮,咧着嘴,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几缕深蓝色的云,在它周围悠荡,试图同它对话,却遭到拒绝。于是它们降落下来,将月色朦胧的大地,再罩上一层玄虚的夜雾——先前的黑暗,变淡漠了;先前的苍白,变模糊了。他们就在这被月光弄得疑虑重重的公路上走着,一切都似乎有点儿不真实。肖潇觉得。
前些天中午地头也打过一架,那时他在哪里?
可惜下午邹思竹来叫她到队部去时,余指导的训话已进行了一大半。又隔着一扇门,隔着门上两块涂了蓝油漆、一块钉了木板后剩下的唯一的玻璃格,大部分谈话听得模棱两可。只看见孙干事一只脚踩在一只拉开的抽屉上,袖子挽得老高,屁股后的手枪几乎顶着地板角上泡泡儿的鼻子。余指导靠在一只皮椅上,抖着腿抽烟。那只皮椅是有人为他定做的,坐上去颤悠悠的,蛮神气。泡泡儿垂头丧气地瞟着陈旭。陈旭铁着脸一言不发……
窗外,有个人影晃了晃。洗得发白的衣领。眼镜片的反光射在肖潇的衣扣上。
好像是邹思竹。他在这窗下来回溜达有一会儿了。
他竟然跳了跳,往窗里看。
她走到外面去。果然是他,贴墙根站着,好像吃了一惊,嚅着嘴说:“找你。”
他走过女生身旁,总是目不斜视。哪个女生铲地“打狼”,他从不接垄。没有女生愿帮他拆洗被褥,可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他任何时候出现,总是形影相吊一个人。正好同陈旭相反。
“你,听了,别紧张。”
他推推眼镜,自己倒是很有一点紧张。
她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好几年前,他第一次来找她,说的第一句话,也是这几个字,也像现在似的,喉结如发动机突突跳动,嘴角紧抿,好像要使劲钳住一种即将爆发的激情。
“什么事?”
“没什么,要紧的事……就是,陈旭,让余指导和孙干事叫到办公室去了,正审问他……”
她后背一阵发冷。
余指导开会回来了?审问?为什么——为草莓谷?
一种时隐时现的羞耻感,突然急速上升。犹如一个装着秘密的枕芯,被人一刀戳破,那些喁喁的儿女私情,卿卿的山盟海誓,都像羽毛一般,飞得漫天皆是……
“同你说,不要紧张,大概是为打群架的事……”他安慰她,盯着地面。
她的脚重又落地,飞快朝队部跑去。
“昨天晚上打群架,是不是你挑动的?”孙干事冲着陈旭吼道。
“证据!”陈旭冷冷地反问。
干吗总想这一段?此刻邹思竹在梦乡里绝梦不到她和陈旭已经走出十几里地了。昨天晚上打群架,真会是陈旭策划?决不可能。他在“破四旧”时都没打过人。如果是个梦就好了。梦里她还揍了子呢,谁叫他抢了她的天鹅蛋。
“昨天晚上做梦,到处寻刘老狠,寻到西葫芦地里去了。”肖潇有些好笑,边走边对陈旭说。
“寻刘老狠做啥?一脑壳酒精。”
“梦里头你们男生总是打架,真的开了枪,吓死人了,还有个指挥官,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他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
她在一块沙地上走。沙子的颜色变幻莫测,像一堆黄绿的蚂蚱,到处蹦跳。她想起来,她是来找连长的,可她怎么也走不快。前面有一口井,井里鼾声如雷。刘瞌,她趴在井台上喊他。连里打架了。这群败家玩意儿。他在井底骂道。把我拽上去。她伸手,井壁深不见底,贴满长毛的白霜,根本够不着。井台有个辘轳把,死沉。她望见一口浅的井,井水溢到井口,井口铺着绿绒似的青苔,井台有一棵桂花树……走近去,树叶上积满冰凌。她摇辘轳把,手粘在铁杆上了,粘掉一层皮,她从没见过这样的井,应该住防空洞。怪不得刘老狠躲在里头喝酒。她又摇辘轳把,却摇上来一桶水。一个男青年,光着上身,穿一条鲜红的裤衩,大腿缝里鼓鼓的一个包,走过来冲凉。他刚把一桶水泼在身上,许多女生四散逃开去,尖叫着:耍流氓,老浙皮耍流氓……子从牛车上跳下来,揪住那人就揍,那人冲子吹口气,从子的衣服里蹦出一群紫色的虱子和跳蚤,个个青蛙大。那人喊:北佬北佬,虱子跳蚤木佬佬,炒菜做饭吃不了。子去追他,边喊:操你妈,南蛮子,老浙皮,洗脚盆儿盛菜,尿盆儿打饭,从里到外埋汰!那人钻进了一顶黑色的蚊帐,蚊帐外面一圈全是蚊子,牛一样的哞哞叫。子掀起蚊帐,抡一把雪亮的火车头牌铁锹,大叫:你们南方人用蚊帐,蚊子不就干咬咱们啦?不行!要咬大家伙儿一堆儿咬!蚊子来咬她,她掉头就跑,闻到了一股酒味,是从前面的西葫芦地里传来的。
连长——她大声喊。
在这哪!声音从一只西葫芦里发出来。
她踢了一脚,西葫芦裂开了,刘老狠躺在瓜瓤里打着呼噜。一只猩红的鼻子,两只金红的眼睛,三点红,一个红三角,没错,是刘老狠。
连里打架了。她说。
不叫打架,叫干仗。刘老狠打个呵欠,谁跟谁打来着?
她想不出谁跟谁,好像是宁波的和鹤岗的,杭州的和牡丹江的,上海的和双鸭山的。南方、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