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书屋2004~书屋2005)-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革命”或“权力”意识形态强制就可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和传媒都是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手段。这是一个双重的塑造过程,一方面“文学”以其道德和情感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实现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在“文学”主动成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这一符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其自身的形象也得到了重新“塑造”,中国当代文学的“形象”、内涵甚至历史也由此得到了确立。在孟繁华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发生、发展、演变的“动力”就掩藏在这一双重“塑造”过程中。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不仅能整体性地解释和还原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生史,而且还能揭示这种“发生史”的必然性和内在规律,从而有效避免了以往那种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把中国当代文学分割成孤立的段落的做法,既整体性地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形象”,又从理论的层面解答了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为什么会是这种“形象”的问题。
其次,《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一书的学术成就还体现在作者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问题时对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出色运用。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探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与转折”,第二章探讨50~70年代传媒的“一体化”控制方式,第三章探讨80年代以后文化领导权在“传媒时代”的重建问题,第四章则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传媒帝国主义”展开批判。作者完整地梳理出了“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确立和演变线索,并对其中隐含的各种政治文化现象进行了精彩的解读。在这方面,我觉得本书的第一、第二两章尤其值得重视。比如,关于50~70年代的文学风格和文学修辞,本书的研究就很有突破和启示意义。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激情和对社会主义的“想象”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发生期的核心“动力”,“社会主义的方向解决了社会的文化紧张,它在提供了社会生活的地图的同时,也为新的生活提供了相适应的符号框架,因此也就成为产生新道德和集体主义文化的母体”(24页)。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工程的需要以及社会主义激情和乐观主义、理想主义的普遍存在,也使得传媒在塑造社会主义形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这种新的言说方式集中体现在它的修辞方式上。……这一方式的来源于中国说来就是毛泽东文体。”毛泽东文体中存在的象征、对比、承诺以及对未来事物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和鼓动性正是社会主义文学“青春写作”特征的体现(34页)。再比如,关于大众文学之于社会主义文化空间建构的功能性价值的论述以及大众文学的道德化倾向的分析,本书的观点同样是极有深度和前沿性的。作者指出,“大众文艺或通俗文学成为共和国时代的主要文艺形式,不仅这一形式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重要的是它对于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构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所具有的功能性价值”(40页)。“对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来说,在大众文学中要渗透和体现的就是民族性、献身理想和阶级斗争教育”(39页)。与文学的大众化相一致,文学的现代形式也“是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得到确立的,五四彻底反传统的路线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不可能被贯彻到底。它的影响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超出知识分子阶层。像刘知侠、曲波、刘流等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家,大都是革命战争的亲历者,他们接受的是革命文化的哺育,这一经历本身不仅使他们具有了一种‘身份’的优越,同时他们接受的文化,‘旧形式’始终是伴随的”(42页)。而大众文学的道德化则既与毛泽东的道德观有关,“毛泽东不是唯道德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念的丰富和不断的强调,则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高尚的惟一的道德标准”,也是大众文学的道德叙事方式的产物,因为,在大众文学的叙事中,“道德”又“被赋予了极为诗性的色彩,流血牺牲、视死如归、公而忘私等道德品质,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文学作品努力表现的”(46页)。“大众文学所张扬的道德理想在民众那里就不是‘理想化’的,他们在兑现的过程中一定要诉诸于‘对象化’,并把它作为一种尺度和标准。所谓‘道德化’的倾向正是在不断的宣传中形成并被放大。献身理想能够成为几代人的追求并引以为荣,与大众文学关于理想的诗性叙事大有关系,对理想和献身的认同,也就是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认同。”(49页)此外,书中关于“积极教育”与“消极教育”、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与文化认同、反城市的现代化悖论、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农村文化趣味的普及等相关问题的论述也都相当精彩。譬如:“知识阶层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认同,就只剩下了一种方式,这就是不断地检讨和互相指控、揭发、批判。这一当代精神文化现象,不止从一个方面示喻了那一时代文化领导权的性质,而且也从本质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62页)“传媒所表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恰恰是反对作为现代化表征的城市文化的,它不仅把城市与资产阶级想象为一种天然关系,而且致力于农村文化对城市的移植,努力培育城市市民乡村的文化趣味。这一矛盾、悖反的现象,不仅限制了城市文化的发展,而且也无意中造就了国民虚假的乡村崇拜的思想倾向和文化趣味。”(92页)等等都可谓是精辟之论。
再次,《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一书对于“现代传媒”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传媒”在文化领导权建构过程中特殊地位的分析也极有学术涵量和理论创新价值。因此,无论是在探讨50~70年代传媒的“一体化”控制方式时,对报刊制度与文化同质化以及中国电影文化的民族性与政治想象的分析,还是对80年代以来网络文化和电视文化等“新兴传媒”样式的解剖,作者的论断总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比如,作者谈到中国红色经典电影时就指出:“对日常生活的排斥和拒绝,对道德理想的乌托邦建构,其背后隐含的是中国电影文化的政治浪漫主义想象。”(115页)“红色经典电影中的民族性建构和政治浪漫主义想象,既是中国现代性焦虑的反映,同时也是缓解这一焦虑的手段和形式。”(119页)“超越了资本主义和它缔造的现代性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终结。而50年代电影中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气氛的渲染,是缓解现代性焦虑的手段之一,事实上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117页)再比如,关于50年代的戏剧改革和戏剧的现代转换问题,作者的论析也同样极有思想穿透力:“围绕着戏剧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既是争夺权力的斗争,也是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中国的形式表达。它从一个方面隐含了社会主义中国对‘现代’的强烈渴求,这种绝对意志所造成的文化同质化,在戏剧领域无可避免地要表现出来。”(130页)在作者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样板戏的所谓“三突出创作原则”正是“文化同质化”的极端产物。
比较而言,本书对于80年代传媒发展和文化领导权问题的论述似乎不及前两章精彩,这一方面由于现代新兴传媒还正在发展中,对它们的认识还要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身陷这些传媒的包围中,尚缺思想的“距离”,但我们看到,作者在对待现代新兴传媒时的清醒态度和批判立场仍然确保了作者在论述相关问题时的理论深度。作者指出,80~90年代“传媒一体化时代的终结,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格局。但是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经验的完全放弃。文化领导权的重建,仍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文化传统的惯性延宕;一是全球化、商业化、信息化的深刻影响”(145页)。“传媒的多样性使文化多元主义的格局成为可能。但在现代性的漩涡中,任何一种‘颠覆’或‘解构’所带来的都只是短暂的解脱或庆幸,它背后隐含的另外一种我们并不熟知的统治在我们的庆幸中已经形成。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250页)而关于网络文化和大众文化,作者的批判锋芒则更为鲜明:“在网络写作中,一方面是以挑战霸权的姿态,表演了现代主义式的野蛮‘嚎叫’,以本能的宣泄置换了传统写作的所有规则和要素;一方面它使亚文化对写作的初级理解得到发扬光大,它貌似激进的外表掩盖的恰恰是最为保守的文化/文学观念。因此,以网络为代表的媒体神话是今天最令人震惊的文化谎言。”(161页)“网络文学的开放性仍然是有限的。网络文学作为一种形式存在,包括它所表达的文学意识形态内容,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都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把它夸大甚至神话化,那么网络文学自身存在的问题,本身就是网络文学不能超越的解构的力量。”(239页)“对大众的膜拜是二十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最大的时尚。这与救亡图存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广泛的民众动员有极大的关系。与这一目标相关的是对其合理性证实的需要,于是,民粹主义作为最适合的思想资源在中国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179页)“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制造了两种虚假的文化时间。一种是过去的文化时间,它以怀旧文化作为表征;一种是当下的文化时间,它以白领趣味作为表征。”(181页)
最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的学术特色还在于作者成功地处理了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背景研究与本体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学术激情与理性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论述周密、严谨,富有思辨力,而且学术观点也尖锐、饱满,辩证而不武断,语言上更是激情洋溢,充满了思想的力量。这一点,我不再展开,因为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已大量征引了该书的原文,目的就是要让读者诸君尽可能直观地感受孟氏的“学术风格”和“思想风格”。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第52节 批判的理性和理性的批判
批判的理性和理性的批判——毛崇杰《颠覆与重建:后批评语境中的价值体系》读后
周平远
1999年5月中外文论南京会议期间,一青年学者迎面走来,恭恭敬敬叫我一声:毛先生……
我一愣,颇有点尴尬。我知道,他把我当成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导毛崇杰先生了。好在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不至于过于窘迫。我停下来,和颜悦色不紧不慢地告诉他:我不是毛先生。这回,轮到他尴尬了。似乎有点残忍?莫不是在“搞笑”、“恶作剧”?我对这位年轻人很有几分同情,也很有几分愧疚与歉意了。
回头想想,几度陷我于鱼目混珠不仁不义,陷他于云里雾里不辨东西者,自己也难逃其咎:毛先生瘦,我也瘦;毛先生白发,我也白发;毛先生鼻子有点勾,我,也有点?不过,毛先生是“思想的猫头鹰”,而我呢?既拙于思,更不会飞,枉生了个鹰钩鼻。
因此,读到毛先生的新著《颠覆与重建:后批评语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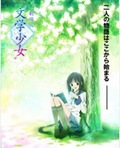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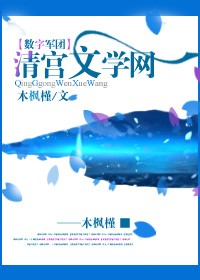
![[hp]魔文学教授封面](http://www.9wshu.net/cover/45/4598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