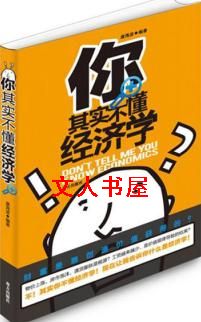张五常学经济-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发了七届他才逝世),被行内人认为是该奖的一个大污点。我有幸,在奈氏谢世前数年遇到了他,跟他谈过两次话,其时他虽已八十多岁,但我还能从那些简短的谈话中,体会到为什么他的学生那样厉害。奈氏个性突出,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他文章湛深难明,而授课也不清楚。但他有创见,表达时有千钧之力。这样的老师是世外高人,余生也晚,不能拜他为师,实在可惜。
一个关于奈特的故事,对香港墨守成规的教育应该有针对性的讽刺。一个多年前曾跟随奈特读博士的学生,年纪大了后,有一天到芝加哥大学去接他的儿子回家。儿子刚刚考过奈特所出的博士试卷。为父的一看,试题像二十多年前他考博士的一样。正感诧异之际,年已老迈的奈特在走廊上迎面而来。他连忙问道:「奈特教授呀,我儿子今天所考的博士试题,跟我二十多年前所考的相同,难道你的经济学没有进步吗?」奈特继续前行,喃喃自语道:「试题是一样,但答案却不同!」明师之见,确是不凡。
大宗师不一定教得出有成就的学生,桃李满门的大宗师,当然也是有的。奇怪的是,有些近乎不见经传之辈,也可能教出高手。中谚云:「冰成于水寒于水,青出于蓝胜于蓝。」高斯对他的老师——A。Plant——推崇备至,但我对Plant的著作却不敢恭维。高斯对我说,Plant使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懂,所以日以继夜不断地钻研学问,寻求答案。也有一些人——如艾智仁——怎样说也不知是谁能教出像他那样天马行空的思想。艾氏说他的启蒙老师是A。Wallace。但Wallace是统计学高手,不懂经济学,那又从何说起呢?我拜读过Wallace的统计学讲义,绝不湛深,但奇妙之处是,他把统计学的基础解释得通透绝伦,使人觉得初学的基础就足以应付任何有关统计的难题了。艾智仁像小孩子般的发问本领,显然是从Wallace那里学来的。
师以徒名,徒以师名,相得益彰,是我们从事学术的人引以为荣的传统。我自己教过几个算是很不错的学生,在学术上稍有成就,但不能说师以徒名。不得已而求其次,徒以师名,我倒可以这样说的。外人说我是艾智仁的学生,是赫舒拉发的学生,使我感到很骄傲。也有人说我是高斯的学生(其实不是),我感到高兴。佛利民对人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也不是),使我更感高兴了。事实上,我曾「偷听」佛利民的课(在芝加哥大学时我们是同事,同事听他的课不止我一人);也曾屡与高斯研讨问题,谈到投机兴奋处,我有时对他衷心直说:「你这个观点我非『借』用一下不可。」
学术的交流就是那样奇妙无穷。说是偷也好,是借也好,是影响也好,只要求知投入,存真诚之心,没有任何博学之士会「秘技」自珍而不肯倾囊相授的。学术的进步用不着青出于蓝,但却要千变万化,多采多姿。屡遇明师是我难得的际遇,而我感到骄傲的是,当我引用他们的思想,或推广发扬,或加上变化,或直指其误,他们都那样高兴,给我提供建议和鼓励。徒以师名,到头来,我的老师可能觉得有点师以徒名了。
第四章:《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
《佃农理论》是我学生时的论文习作,大约一九六六年五月动工,一九六七年四月交卷。那时在加州长堤大学任职,每星期要教十二课,又要在长堤艺术博物馆开什么个人摄影展览,所以真正下功夫的时间不到六个月。六六年的秋天,我有三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
一九六七年九月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很详尽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料,就补加了一章。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把该书精装面市时,已是一九六九年了。
《佃农理论》这本书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历久犹新:出版后三十年,该书及书内的文章每年还被引用大约二十次;另一方面,好些学者朋友认为该书是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的“始作俑者”。其二,作为一本“名著”,这本书的滞销可能破了世界纪录。
天下间怎会有这样可怜的事?一九六九年芝大出版社印制了一千本;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自动买了五百本;作者及其学生、朋友等买了大约三百本;二十五年后芝大出版社决定把版权交还给我时,竟然还有“货尾”三十多本送给我。可以这样说吧,真正在市场出售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不到二百本!
今天朋友们要求重印,而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又花了三年时间搞中译本,我就闲笔回顾,好叫后学的知道《佃农理论》的一些往事。
一九五九年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六一年学士,六二年硕士,六三年的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试。殊不知这势如破竹的进度,在博士试后却碰到铜墙铁壁: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论文题材。
两年中我换了四个题材,到最后都放弃了。败走麦城,要不是因为理论上的困难解决不了(如风险的高低如何量度),就是资料不足(如林业的各种定价),或语言不通(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或者是题材过于庞大(如香港的租务管制)。
这些强攻不下的题材,当时使我气馁。于今回顾,这些失败对我后来的学术生涯大有好处。这不仅使我在四个题材上成为一个准专家,而更重要的是对搜集资料学满了功夫。
一九六五年八月,心灰意冷之余,我放弃学术,公余之暇拿相机静坐在一个园林中搞摄影。六个月后卷土重来,在图书馆找到一些关于台湾农业的资料。那里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地主不能超过农产品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令经济学者难以置信的,是在这政府硬性的约束下,农业产量急升。我当时怀疑那是台湾政府的数字游戏,要宣传一下国民党的优越性。但多方调查的结果,是产量上升的数字可信。政府管制,生产怎会上升的?
我想,要解释这个怪现象,第一步是要做出一个分成没有管制的租田理论,而分成租田就是佃农了。我没有参考有关的理论读物,只两天这理论就做了出来。我跟把分成的百分比管制加上去,在理论逻辑上生产竟然上升。这结论不容易相信,但反复查核理论的每一步,找不到有任何错漏的地方。
当时在长堤大学共享同一办公室的是Eldon Dvorak。我请他坐下来,逐点逐步地向他解释我的理论结构。他听得很用心,提出不少问题,我都答得清楚。几个小时后,他突然说:你的理论会引起地震!
对我来说,该理论的“创立”顺理成章,没有什幺新意。我只拿三个基本原则去推理。第一,我是艾智仁(A。A。Alchian 1914——)的入室弟子,又熟读高斯(R。Hase 1910——)的论著,当然明白产权对行为的重要性。土地是地主的私产,劳力是农民的私产,所以要从私产的局限入手。第二,佃农分成是一种合约,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第三,农民之间要竞争,地主之间也要竞争,所以佃农合约中的条件(这包括分成的百分比),是在私产与竞争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我对这三个理论基础很执着,任何稍有分歧的推论都不考虑。所以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农户租用土地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皆是由上述的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佃农合约的条件了。
有了如上的佃农理论,我很容易知道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这是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大致一样。
但既然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呢?这是个浅而又不能不问的问题,后来触发了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研究。
佃农理论做得满意后,我就加入台湾土地改革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只几分钟就把问题弄清楚了。因为这约束是在原有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所以在竞争下他们必需增加劳力,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为生产增加而有点补偿。这样,农产品就上升了。
我反复思考,找不到错处,就写了十一页纸,题为《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革》,寄到加大作为博士论文的大纲。第一页预告了大纲内的六个结论。
一九六六年五月某日下午五时,加大为我的论文大纲开研讨会,到会者大约四十人,其中十多位是教授。教授们没有在会前读过早已拿到的大纲,因为他们一致认为第一页的六个结论全盘错了。
(之二)
当我听到教授们说六点皆错,就想:错一两点有可能,但说六点皆错就显得他们不明白。在会的人开始争论,但我只注意赫舒拉发(J。Hirshleifer 1925——)及艾智仁。他俩是本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不可能不明白我的理论。赫氏一言不发,想些什么,时而摇头,时而点头。艾氏木无表情,拿我的“大纲”翻阅。
争论的诸君主要是为了一点后来我才知道是老生想谈的:地主若收农户固定租金,付租后的生产剩余全归农户所有;但佃农分成,农户的所有生产都要分可观的一部分给地主,其生产意图怎会不被削弱,所以佃农生产是比不上固定租金的。我说农户要竞争,说地主有选择权,他们听了等于没听,继续争吵下去。
两个小时后,第一个站在我那边的是H。Somers,很有点强辞夺理。他说:“没有教过史提芬的不准发言。我教过他,知道他不可能错得那样容易。”赫舒拉发跟说:“不要管第一页的六个结论,我们要从第二页的分析开始。”
第二页解释的是第三页的一个古怪图表,天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好象是一条面包给人一片片地切开来的。我解释说:假如一个地主拥有一块很大的农地,若以佃农方式将整块地租给一个一家四口的小农户,地主的分成率会很高,因为小农户以低分成率而得的收入,足以使他不另谋高就。地主于是把大地切开,租给两户佃农,他的分成率会下降,但总收入却会上升。
我跟代表地主再切下去,加上第三户佃农,地主分成率再下降,而总收入再增加。我又再切,赫舒拉发大声问:“你要将那块地分给无数的农户吗?”我答道:“不是的。农户愈多,地主的分成率愈低。开始时地主分成率下降会有较高的总收入,但到了某一点之后再切下去,地主的总收入就会下降了。只有一个农户数字使地主得到最高的总收入,而若其它情况不变的话,只有一个分成的百分比是与竞争没有冲突的。”
会上一时鸦雀无声。过了良久,赫舒拉发说:“我明白,我同意,但我还有其它不明白的地方。”转到第四页,他们又吵起来了。晚上十时(研讨了五个小时),艾智仁一看手表,站起来,走了。其它的人皆去,余下来的只有E。Thompson。他是个奇才,会中反对得最激烈的是他。他继续和我争论,但我无心恋战,他说他的,我想我的。晚上十一时,我到加大邻近的一家餐室吃点东西,忍不住挂个电话到赫舒拉发家中,说我三年来认为可以交出去的论文大纲只有那十一页,但那么多人反对,感到很失望。他响应道:“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