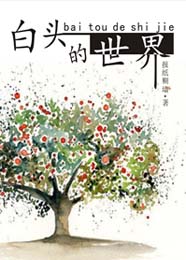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莫泊桑述评-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的,普鲁士人不见了,他们提前十八月撤回了本土,因为,国防政府已向他们缴付了足够的赔款,并将阿尔萨斯全省及洛林省的一部分割让给了普鲁士。而摆脱了征服者的梯也尔政府现在可以集中精力消除巴黎的革命火种。三月中旬,巴黎工人起义,并于下旬成立“公社。”
梯也尔像刚撤走的普鲁士人一样,重新包围了巴黎。在这个长期被围的城市里,经济生活等于零,因而,皮埃尔·米盖尔说,“就巴黎而言,公社这一插曲仿佛是围城的继续。首都已被团团围住。它将很快地受到围攻。”
梯也尔的军队 (“凡尔赛分子”)从未曾设防的圣克鲁门进入了巴黎,开始了五月下旬的“流血周”。最后的战斗发生在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墓碑之间。公社遭到失败。此后,巴黎不再是爆发革命的中心了。巴黎终于成了一座没有血性的城市。“感激涕零的共和派为梯也尔编织了花冠,然后一砖一瓦地为他重建被焚毁的宅第—— ‘新雅典’”米盖尔这样说。从此,巴黎已失去了它曾经有的激进主义,而供奉了保守主义这面白色的旗帜。
巴黎公社这段历史,莫泊桑并不是目击者,——那时,他还在埃特尔塔海滨城。阅历并不算丰的莫泊桑几乎在日后的作品中没有谈及这一在他的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也许出自他对工人阶级的尚不明晰的同情态度。然而,最为内在的原因却是:这个具有政治良知的作家在未弄清楚问题前是不急着表态的,也不会将他未曾感觉过的事件写于作品中。
这是一种对于真理,对于艺术的忠诚。于·列那尔谈到莫泊桑时,说:“莫泊桑,他很少自白。他不说:‘我是真理的源泉。’”
一八七一年的七月,莫泊桑告别了埃特尔特,登上了重返巴黎的驿车。等着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巴 黎
满是泥斑的驿车缓缓驶进了巴黎城。这是梯也尔的巴黎,一个以论坛取代街垒的巴黎。阿莱维谈到这个时期巴黎的精神风气时说:“人们不再示威游行,而是去投票,按照乡镇的共和派、兽医和酒商的建议,将委员会准备的选票投入票箱。”甚至梯也尔垮台后,取而代之的是色当的战败者麦克—马洪元帅组织的一个“公爵们的共和国”,一个试图在法兰西重建已跌落在尘埃中的“道德秩序”的不很牢固的政权。这样,作为历史的一个循环,那一度被断台头驱走了教会势力,开始着手“收复人心”。任何曾使巴黎扬名的激进主义都被视作“从革命中脱胎的世俗社会的现代祸害。”教会想在法国生活的一切领域——国家、城市、家庭——恢复上帝的权威;对于教会来说,法国重新成为传布宗教的地方。皮埃尔·米盖尔从宗教的重建看出这“完全是一种复辟。”
其实,这种调子只是第二帝国受伤的理想主义的一个重复,或者,一声轻叹。路易·波拿巴在十年前就暗示了这种阴沉的时代气质,他在一本化名撰写的小册子上中发了这么一种低调的言论:“领土越小,追念起深。”
这一时代的文学却显示了某种异乎寻常的批判精神,这也许是街垒让位于论坛的一个必然结果。被路易·波拿巴流放在外的维克多·雨果在波拿巴倒台后,重返法国;这位奥林匹斯山神带给了法国文学一种对于法兰西的热情史的研究。他的这种研究已褪去了早期的浪漫主义色彩,而显示出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于历史的全部洞悉,它体现为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不过,确切地说,尽管雨果那时仍是个伟大的作家,可是对于“爵爷们的共和国”及其后的时代来说,他更多地是被当作一个享有崇高敬意的父亲的形象,而被社会关注,他在气质上更属于那个已经故去的时代,那个与巴尔扎克并立的时代,——一八五○年八月十七的夜间,奥瑙利·德·巴尔扎克这位“历史的书记员”的去世,标志着一个热情似火的时代的精神的终结,一个既产生了拿破仑,又产生了伏脱冷的时代的埋入地下。在他之后,时代的风气或者精神显得越来越卑琐了。
这一时代的文学精神呈现出——勿宁说是——一种反浪漫主义的倾向。研究代替了热情,手术刀代替了枪。而从文学所表现的主题言,对于历史的宏伟场面的追求,也即巴尔扎克所说的对于“一种浩瀚地气势”的追求,已让位于对于现实的精细的分析,爱米尔·左拉的“鲁贡—马卡尔家族史”,就是放在他的手术台上的一个病例。这位颇读过一些医学书——其中包括克罗斯·贝尔纳的遗传学——的作家这样说过:“不谈什么日神、月神,也不会象我们的诗似的,看着一枝芦荻或是一片月光就会昏晕。”有趣的是,这个时代的另一位文学家——居斯塔夫·福楼拜,他的成名要比左拉早——也有“医学”的背景:他的父亲是鲁昂市立医院的一个主任医生,小福楼拜曾扒在窗口看他解剖尸体。
外科医生的冷静的气质代替了热情的不可靠的迸发。巴尔扎克曾幻想过这种“外科医生的似的冷静与客观”,他笔下的医生毕安训便是这个幻想的一个寄托;可巴尔扎克的气质过于炽热,是一个巨人似的气质,这使他的艺术呈现出浩瀚的气势的同时,又不时地显出一点粗糙的痕迹。可以想知,他以后的文学精神将朝一个相反的方向发展,即失去了浩瀚的气势的时候,又获得了一种艺术的精致。与莫泊桑同时代的那位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也许集中体现了“艺术的精致”这种时代精神。他在把雨果或巴尔扎克(他喻之为“从一个山顶到另一个山顶建筑的一些宏伟的高架渠”)与梅里美 (他喻之为“紧紧贴着地面,没有无用的装饰,也没有不必要的玄虚的水管”)作了一番比较后,说道:“对于这些宏伟建筑,我们固然赞叹;但如果我们发现沿着地面装设一些简单的小管,来代替那些伟大的建筑,我们的赞叹就会更大了。”
医学的发展同时意味着科学的发展;在哲学上,就产生了实证主义。丹纳提出的“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的原则,多少代表这一时代的一种普遍倾向;而丹纳自己受了普法战争的刺激,而决心从事“现代法兰西渊源”的研究。
冷静,客观,分寸,——这是第二帝国垮台以后精神领域的一种风气。这是一个更加谨慎的时代,因为它已经被接二连三的恐怖弄胆小了,也更理智了。
一种“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指梅里美)的文风将成为这个时期一派作家的风格。从我们这个更加谨小慎微而且时代精神显得更为猥琐的时代的心理来看,这些细小然而精致的艺术,也许高于那种宏大然而粗糙的艺术,因为那种宏大的艺术不自量力的地想去与哲学争夺地盘,与历史争夺地盘,而精致的艺术除了借用一下医学外,并不准备把主观的热情倾注在对时代的思索中,它的精神被福楼拜用一个词概括起来,这个对莫泊桑具有深刻影响的词是——“非个人化”,它的意谓着“客观”、“第三人称叙述”、“不作结论”、“信守中立”等等不偏不倚的态度,尽管这些作家在文学之外,也许是有政治热情的人,但他们决不把主观性的热情倾泻在作品中。
这一“客观”倾向在诗歌中的反映是巴那斯派,它标榜艺术至上主义,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尤其注重造型,从而偏离了“客观主义”的初衷,因为客观主义是想通过不带情感色彩的描绘,从而更好地揭示现实的病态,“它是一张非常薄的、非常透明的玻璃,它本来就是这么透明,形象透露过来,立刻就在它们真实的形态下再现出来。”左拉在致瓦格勃来格的信中这样解释道。
不过,初来巴黎——重返巴黎——的莫泊桑并没有立刻接受福楼拜的原则,他被诗诗歌迷住了;尽管按照左拉的一个暗示:从浪漫派到现实主义意谓着放弃诗歌而选择散文,然而,在这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距离,左拉本人也是不久以前才克服这个距离的。谁知道“鲁贡—马卡尔家族”的外科医生曾经也是一个“在巴黎的马路上饿着肚子的诗人”(让·弗莱维勒语)呢?
和青年时代的左拉一样,莫泊桑怀着一颗诗人的心来到巴黎,为了获得梦幻中的桂冠;为了不至像左拉那样饿肚子,他必须先找一个工作。
小职员、登徒子与艺术家
可是,起初,事与愿违。国防政府即将通过一项“新兵役法”,按照这个兵役法的规定,还未脱掉军装的莫泊桑得马上去炮兵部队服役七年。不过,这项法令还有一条附加案:假若应征人员不能亲自服役,可以让人顶替。
法国军队在普鲁士人的炮击下狼狈溃逃的情景与法国军队在内战中的残忍,重叠在吉的脑海,使使对法国军队的军服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位在日后的作品中从来就对法国军队不抱好感的正直的作家,把再度进入军队视作一个灾难。他是这样轻蔑地谈到法国军队的:“两个月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谨慎地侦察敌人,有时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立刻准备作战,现在却都逃回自己的家里。”在另一外,他更轻蔑地说:“这些人以前只耍弄秤杆,现在手中拿了武器,操持上步枪,都高兴得几乎发狂;而且毫无理由地变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他们常常处决无辜的人,为的是证明他们会杀人;他们在普鲁士人还未光临过的乡间巡逻的时候,常用枪打死无主的狗,安安静静正在倒嚼的母牛和在草地里吃草的病马。”这种几乎残忍的对法国军队的反思,使他不愿与之为伍;何况,眼下,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去扑灭由巴黎燃起而蔓延到了外省的一些骚动。
另一个原因,一个出自艺术野心的原因,是:他不愿再放弃被战争打断的写作。本来,突如其来的普法战争使莫泊桑被迫放弃写作达一年之久,而他现在已经二十一岁了,维克多·雨果在这个年龄上已经家喻户晓。
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脱掉身上这套象征着失败的制服。这时,兵役法的附加案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刚到巴黎,他就写信给他父亲,让他找个顶替的人。“如果过三个月才能找到顶替的人,”这封标明写于七月三十日的信写道,“我就砸锅了……因为,要是新兵役法在这三个月之内就通过,我就得进第二十一炮兵团当普通士兵,那将比在后勤处更糟糕。”他提到的“后勤处”是指一年以前驻扎在鲁昂的勒阿弗尔军区第二师的后勤处,莫泊桑曾在这里担任过文书。
直到这时,他的父亲,那个登徒子居斯塔夫,才显示出父亲的形象。这位已年届五十的父亲整天顶着灼人的烈日,奔走着,为吉寻找顶替的人。在九月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一位自愿顶替者——那时,在诺曼第,挨饿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当兵至少能够解决一个人的口粮,何况,还能得到一笔可观的顶替费——这样,吉终于脱掉了那身使他极感束缚的军装。也许我们可以作以下的假设:假若没有居斯塔夫的奔走,吉的名字也许不是列在文学史上,而是列在凡尔塞分子的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