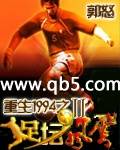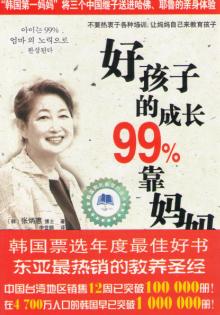书屋 1999年第六期-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或者说根本就没看明白就匆匆忙忙拿起笔写批判文章以进“忠言”要好得多。要知道,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发展受到的根本制约是人口与资源的约束,至于进没进行制度批判更无需解释。
还有人则认为我这本书“来得非常乖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心”,这话是在部分小文人当中口口相传,没有文章问世。我只想问问这些在背后吱吱喳喳嚼舌头的小文人:这本书乖巧在哪里?哪一点乖巧?是不是因为我现在还平安活着,正常地拿工资吃饭,还活出了小康水平,就证明书是乖巧之作?
还有一篇长达一万余字的文章“中国现代化反省”(《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CDI研究报告》1998年6月)更有趣,开篇之处作者陈开国先生谈了他所在的研究院对我的集体愤怒之后,写了这么一段话:“主持综发院工作的某某某教授(原文有名,我考虑还是省略为好)认为,应该进一步阅读何清涟的《陷阱》,……某某某先生建议我与他一起阅读,他这时已开始读了一部分。这种兼容博取的态度对我是一种激励,我接受他的建议。”“何清涟的职业使她容易深入生活,同社会各方面有广泛接触。这从她书中引用的大量报刊资料和自己的调查手记看得出来,我没有这种优势。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些年处于半封闭状态,对外界情况了解不多,也不动手写作(写不出东西)”,“要对她的书作出具有学术水平的评论,则超出了我的知识与理论能力。”不过作者还是写下了洋洋万言的评论,那评论足以证明作者前面的话并非谦虚之辞,比如他指责我碰到关键问题上就绕开了,比如他认为现在人文科学“继往开来,日益兴旺”,比如他认为我这本书是受商业风气影响,在浮躁心理作用下的产物,全书并不能给人以解决问题的阅读快感,使用“资本原始积累”这一旧概念并不能概括新问题——这是陈先生全文惟一对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不敬的地方,等等。一个不写作的人当然不知道写作者不得不注意的环境禁忌,而且他根本就不了解这本书就这么改来改去还拖了一年半时间才能出版的痛苦遭遇。不过我还是很佩服老先生的勇气,能够在与被批评者不处于对现实认知的同一平台时,不怕掉底地如此云云不辞劳苦写了洋洋万言,相信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从事研究工作几十年的资深老学者,还能这样谦虚地用文章表明自己毕生才具仅仅只剩下批判能力,并且“奉旨”批判。
大概是觉得陈开国老先生文笔严肃,不够调侃,陈先生的两位同事取名“龙马”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发表于《深圳商报》上,该文指出,何清涟之所以会对中国的现实作出如此分析,认为腐败不应该成为改革的代价,等等,是因为每天呆在小小的卧室里,没有到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广阔的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去遨游一番,如果到过那些地方,经过商品经济的洗礼,就会对中国问题认识深刻一些。然后作者告诫我要谦虚谨慎,因为深圳市像我这样的人才即便没有一万,也至少有好几千。至于去那里遨游过一遍甚至几遍的他们何以没能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刻研究,而只能在互联网上抄写东西编编东南亚金融风暴之类,文章中没有解释这因果关系。我于是感到自己的闭塞,不知什么机构什么时候立下了这一规矩:研究中国问题必得到那些地方去经受洗礼,如同穆斯林必得去麦加朝圣才能够有资格做阿訇一般。我暗下决心,今后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去上一回,以便经受美国商品经济的洗礼,再想法获得“龙马”两先生的认可,取得做中国问题研究的资格。
另一篇同样发表于《深圳商报》上、署名为“闲云”的深圳市“金融工作者”则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真正的学术著作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懂,而我的书因为大家能够看懂,充其量只是本经济学的通俗读物。还有一篇在《万科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干脆说这本书只配拿去盖咸菜坛子。
还有一位颇有点名气的社会学学者到处说:“她谈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看也都知道。让这女人得了便宜去。”言谈中颇有懊悔自己没抓住机会的意思。按照这种评价演绎,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她写的也不过是当时美国人人都知道的黑奴问题。至于我是否得了便宜,有哥仑布立鸡蛋的故事在先,不用多谈。
上述这些“学术批评”,是“陷阱”一书掀起的小小波浪,我并未动气,看过了权当寂寞治学生涯中多了一点调味料,作为资料丢一边去。因为毕竟大都只是就书谈书,就算是有人延伸了一下“批评”的外延也不要紧,虽然批评的方法、口气以及部分作者的写作动机我并不怎么能接受。比如人家将书买回去了,书已是人家的财产,人家有财产支配权,他要拿去盖咸菜坛子,你难道还能生气,去干涉人家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人家立意高远,喜欢写“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看懂的真正的学术著作”,那也是人家的自由,“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况且退一步说,即使批评了我的书,也不是我的敌人,因为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没有私敌,真正的敌人只不过是某种思想观念罢了,因为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薰陶中长大的国人,都真诚地相信在对立统一的矛盾斗争中可以让世界前进,那么就让人家在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斗争中得到向上的升华”吧,我活着还有做靶子让人获得批判快感的功能,也不枉了人生一场。
三
真正惹起我动气的是一些造谣生事者。比如一些文人背后口口相传的说我“与政府合谋”搞掉了《黑马文丛》一事,我已在电话里质问过谣言的源头。这位自诩身兼“大侠”、“思想家”、“出版家”的酋长竟然不承认自己说过这话,还一再表示不再管这事。酋长完全忘了,管这事并非谁请他出面,而是他自觉自愿主动“参与”。想当初他是那样十万火急地将我在西安打假一事在第一时间电告非法出版物的始作俑者,并“仗义”地将书稿拿来火速出版。酋长也根本不顾事实:我是去年十一月下旬去新闻出版署打黄扫非办,拿着全部证据(包括始作俑者写有我看过书稿并同意出版字样的两份委托书),要求打黄扫非办这一行政执法机关严惩制作非法出版物《现代化的陷阱背后》的小团伙,因为当时新的著作权法还未出台——那部法律直到去年十二月才出台,不能追诉此前的犯罪行为,为这一点我一直遗憾不已——再加之非法盗版物还未正式出版,算作犯罪过程中止,所以只能将为首者整顿除名,另一名主要参与者则受到所在出版社惩罚。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种拆烂污的货色竟然会被眼光高明的酋长看作奇货可居的宝货,并收进《黑马文丛》。我知道酋长要出这书时,已是今年一月下旬的事了,因为书已出来,且酋长已遵照承诺删掉作者那些想入非非、假造事实之语,此事也就算告一段落。但在打击了制假者以后,竟然还有少数小文人为制假者打抱不平,说什么制假虽不对,但可以在报纸刊物上与某文人打笔仗,而不应该求助政府。对于持这类论调的小文人,我实在抱歉得很,因为本人没有在报纸上耍猴戏给各位观赏的雅兴,也不相信这类舔碗底的小“文人”有什么正义感。这类人之所以出来打抱不平,只是物伤其类罢了。而酋长在以“某某某挑战何清涟”为词进行大幅广告炒作以谋大利却没达到目的后,竟又不惜制造我“与政府合谋搞掉《黑马文丛》”的谣言辱我清誉。我在电话中正告大酋长,只要有人出来指证他说过那些话,或者他在任何公开场合说过类似的话,哪怕是有人将他的谣言写成文字被我看到,本人将毫不迟疑顺藤摸瓜地以诽谤罪诉诸法律。至于这种如同地下室的老鼠般躲在阴暗角落里不停啮咬的行径,本来就非人类所为,所以连身为男人并兼“出版家”、“思想家”的草原部落大酋长自己也羞于承认自己曾说过那些话。在此要说明的是,《黑马文丛》收的是哪几本书我至今也不清楚,这倒不是我胆敢瞧不起其他作者,只是因为看到那文丛的名字就有一种深深的被侮辱之感,所以宁可错失机会,这一点要真诚地敬请其他作者原谅。至于说我为人厉害,一方面批评政府,一方面又依靠政府之类,这话实在表明酋长与那位小文人的言行混乱之极,且对事物缺乏起码的认知。首先,现在的政府是中国惟一的执法机构,难道我不向政府申诉要求惩处非法出版物的制作团伙,而去找黑社会的“教父”?更何况某小文人早已先放出风来说我要找黑社会的人修理他,还为此也去依靠了一把政府,给深圳市领导写了一封控告信,只是提供不出任何证据,没能依靠上罢了。其次,酋长自己难道是不食周粟,呆在首阳山里饿死的伯夷、叔齐?他自己“做书”,不是也在依靠政府垄断的出版行业给书号吗?说我厉害那倒没什么,因为如果我不“厉害”一点,并为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依法而战,甚至愚蠢地听从那些在报纸上讨公道的“善意”劝告,那不早被他们连骨头渣都吃没了?至于历年来被那位小文人吃的不幸者,包括早已闭关的老历史学家、死去的张志新,以及一位被兜头泼了一盆脏水,从此失去欢笑的小姑娘,又有哪位小文人出来为他们讨个公道?
我也发自内心地可怜这些人。他们也许是习惯成自然,一向为所欲为伤害人家成了日常行为的一部分,竟然常常弄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往往在受害者诉诸法律或行政执法机关以后,又来抱怨人家不该依靠政府——这行为怎也不像是大男人所为,倒像是……所为,此情此景真是可怜复可叹。在此我还是劝他们到每个市、县政府都设有的“普法办”去领上一本不花钱的“普法常识”,支出一点“机会成本”,花一点时间,坐在家里看上一两遍罢,以免今后被别人与“政府合谋”因他们的诽谤罪施加法律惩治。
建立这一“资产负债表”,目的是立此存照,毕竟这是中国“文坛”的一大景观。如果不是我的“影响”近年来扩及到“文坛”,想要得到小文人的侮辱都还没处找门呢,人家造谣侮辱您是看得起您哪,这点“道理”我现在已然明白了。前十年我在两本只有思想界看的杂志上发了《现代化的陷阱》那么多章节,也没有人来招我惹我,看来这“文坛”实在是惹不起也躲不起。前一向有一位活了九十好几且因做汉奸坐过牢的人,翻出当年旧案,说明自己的历史不是以前定的那样,又是征婚,又是为自己平反,一时间好不热闹,居然还有几位年青女子应征,还有传媒大大捧场。看来造谣者还是好好保养为上,通过多种途径赚钱,活到千岁千岁千千岁,等到同时代人都去世了,那时他们老而不死竟成贼,可以翻出现在这段已通过行政执法板上钉钉的公案,红口白牙再写出点“内幕”“背后”来为自己“平反”。
“文坛”的风景线,多了这么几棵菜,煞是好看,也从而使得我辈必须将有用之精力从事无用之劳动,在“资产负债表”上增加支出,减少收益。但据我所知,依靠这类左道旁门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