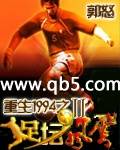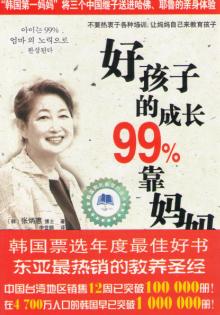书屋 1999年第六期-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争取政权应当依法进行,以求取大多数国民的支持。用武力推翻政府是不合法的,是暴乱。政府为了自己,有责任平定叛乱。”他曾表示:“在国家危难之时,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鲁迅称郭沫若式的革命文学家脚踏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环境较好的时候,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待到革命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变了纯文学家了。胡适的情况其实也颇类似,一直在学院和政府两者之间游弋,这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恒态。不同的只是,他表现得相当忠勇,一旦政府陷于危难,却是不惜舍身作陪葬品了。
美国学者周明之这样评价胡适,说:“他倾心于一种无行动的维持现状,使他得以进行一种‘最根本的建设’,‘为未来世世代代的建设打下基础’。而这实际上就是把无论何种环境中的行动都无限推迟,并无条件地拒绝承认任何反政府的行动。这便是胡适文化与精神变革的心理基础。”格里德指出,胡适的政治态度反映出他对自由主义理论有一种根本的误解。他明确而持久地把政府想象成实现公共目标的工具,但对于这类目的怎样才能由与他的民主倾向相一致的手段来决定,却没有清楚的认识。格里德还把胡适同他的老师杜威做了对比,说杜威是从特定的假定条件出发的,他的假定是根据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经验推导出来的;这些经验,几乎在每一个重要方面都是跟中国不同的。而胡适的民主宪政构想是建立在一种“普遍性的信仰”之上的,在他的自由主义信条中,最致命的,就是绝对排除对专制政治的自由反抗。格里德承认,这是一个危险的位置:“在公开反对现存秩序和无条件向现存秩序投降之间,正是胡适所走的狭窄的路。”但是,他毕竟明显地倾向后者。格里德说:“胡适对于现存政权的原则始终是十分尊重的,因而,尽管国民党无视他的合法性标准,他也不得不为国民党的统治权力辩护。”鲁迅说:“新月博士(胡适)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据说鲁迅是胡适的对头,不足为据;而洋鬼子对胡适的批评,却也都集中在这上面,结论是一致的。权力这东西,注定要劫夺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的。对此,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有一段话,结合福柯的情况,说得很好:“话语实践并不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行为是另外一回事。当一个知识分子被要求采取政治行为时,也就是说,当他被整合到权力机制之中时,他就完全站错了。……福柯便碰上了这样的问题。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高决策层的政治顾问,他也获得了这一职位。如果说有谁愿意这样的话,那就是福柯,无论如何,他作了尝试,却发现自己难以胜任:这是一次失败。”在这里,胡适就是福柯。
关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胡适研究专家格里德认为,并非因为自由主义者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而是因为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者需要秩序,中国却处在混乱之中;自由主义者理想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他们又不能提供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自由主义者崇仰理性,而中国人的生活是依靠武力来塑造的。简言之,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它无法为中国面临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提供答案。接着,他提出:“如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愿意与现存的秩序进行斗争而不只是设想借助这个秩序,他们很可能会成为现有秩序的更为有效的批评者。如果在他们看来,革命不是那样的意义不明和危险的药方的话,他们也许就会成为激进变革的更有说服力的拥护者。但如果他们是为另一种案情辩护的话,它们也就不再是自由主义者了。”格里德本来强调的是环境的关系,结果回到了立场的问题。中国的自由主义,首先关心的并不是人的境遇和自由选择,而是关心中国应当如何使国家——其实就是政府——对它与个人的合法(契约)关系实行控制和干预;正是为此,确认宪政的价值,通过修宪而把个人和政府联结起来。在此之前,它对政府本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不予考虑的。在人权——人的拯救——与党国/国家的拯救发生矛盾时,宁可舍弃人权而维护党国。宪政的存在,对于自由主义/好政府主义者来说,其实是一个间接控制权力的装置,借以维持一如古代谏臣所谋求的那样一种君臣间的恰当关系,而不是作成君臣/君民关系的消解,确保各个臣民作为现代个人的存在的权利。别尔嘉耶夫在阐释俄罗斯思想时,感慨总结道:“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始终是薄弱的,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道德上有威望和鼓舞人心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改革家们当然是有意义的,然而,他们的自由主义,仅仅是实践性的、事务性的,常常打着官腔。它们并不具有俄罗斯知识分子永远需求的思想体系。”中国的情况,大抵也如此。
鲁迅是特异者。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始终是一个孤独的战士。虽然,他也曾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为声援运动的先驱者而做过“遵命文学”,但从来没有个人的圈子。他很少从事组织活动,很少做宣言似的文字,但也论战,论战时经常使用匕首般的短文,随感而发,很有点像古代的独行侠——就像他关于复仇的小说中的“黑色人”——的作风。然而,更多时候采用独语的方式,记叙着他的记忆和梦境。他是听从一个其实很空洞虚无的历史的指示——他笔下的过客听到的那个“前面的声音”——其实是内心的指示写作的。即使是这样一个惯于担负黑暗的重担的人,在他曾经寄予希望的运动一旦烟消云散之后,也不能不深感彷徨: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离开,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新的战友在哪里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种境遇,确乎损伤了他的内心,却使灵魂更加粗砺。集体溃散后的空缺,固然使个体变得孤独,但也可以因此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他是撒旦的化身,不惮神的打击。且看他稍后记录的另一幅情景:仍然站在沙漠上,但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身上的凝血,犹自喜欢这伤创的斑斓……
五四退潮之后,鲁迅以自己的方式,坚持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想观念,从不考虑政党或者政府的立场,因为这是与五四无缘的。尤其是宪政之类的玩艺,由于它完全以现存的专制秩序为基础,所以什么立法,都是旨在膨大和加强国家权力,限制和剥夺个体的一种政治建设,而非壮大民间社会的文化建设。他要破坏这偶像,破坏与官方利益相关的一切。在他那里,始终清楚地存在着一个身份问题,界限问题;从来不曾偏离作为一个民间知识者的边缘的立场,不致堕落知识界自行设置的多元/宽容之网而放弃斗争,相反执著于战斗的一元态度。没有一元也就没有了多元。他所要的是“在场”,而不是自我逃逸——所谓“缺席的权利”。
对于鲁迅,权力和权力者是一生攻击的主要目标。他抗议他们赤裸裸的屠杀罪行,揭露独裁、专制、卖国,种种的欺骗性政策,嘲笑他们的无知。他攻击传统文化,也主要是历代统治者所着意保留的部分,各种神圣的经典,万世一系的训谕,最毒辣的手段和最巧妙的戏法。譬如反孔,他反对的就是“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而不仅仅是僵尸。他批判国民性,也都是为统治者所渗透所改造的改变中的性质。其实仍然是“治绩”。包括自我批判,他追踪“毒气”和“鬼气”至自己体内,因此必须割除与统治者有任何沾缠的东西,哪怕切肤之痛。这是一种彻底,一种五四式的洁癖。他坚持自由思想、自由写作的权利,而与权力者相周旋,原因就在于,权力者始终是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死敌。他对待大批的知识界同行,尤其学者,甚至不惜在自己的周围树立“私敌”,都因为他们不同程度地为权力者及其意识形态所同化,从根本上背弃了五四的立场。在表达中间,他不避“褊狭”、“刻毒”的恶名,直击猛人、阔人、流氓,形形色色的小丑,捣毁“文明”的面具;然而,也不断变换笔名,使用反语,曲曲折折,吞吞吐吐。说到底,他要在已经被大量侵吞,而且将继续被侵吞的话语空间中,护卫自己的独立性;在夹缝中左冲右突,亦唯在伸张内心的自由而已。他是弱势者,独战者,是后五四时期的唐吉诃德。
关于启蒙,五四以后不断遭到来自知识分子的攻诋。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实在只配关心知识专业问题;什么启蒙,都是狂妄的表现,一种自我扩张的行为,甚至是反角色的。于是,他们叫嚷回到知识分子自身。但是,鲁迅不然,他站在广大的哑默中间,却无时不觉得权力的压迫,无时不觉得有一股黑暗之流贯穿自身,从而产生本能的反弹和对抗是必然的。他无法与一个专制社会安然相守,因为诉诸痛觉的现实的东西是那般巨大、深刻和尖锐。在压力面前,当被压迫者不能已于言时,其话语形态一定是不平的,阴郁的,反拨的,击刺的,动荡的,粗犷的。他就是这样。世上有所谓恬静的、精致的、旷达的、隽逸的、典雅的话语,其实那是变态,一种卑怯的风格。
当革命或者救亡成为一种主体话语的时候,启蒙是否成为必要?如何启蒙?启蒙是否有可能深入目标明确的群众性运动,并产生持久性影响?至少,从鲁迅的身上可以看到,无论环境如何迁流,他仍然坚持作为一个启蒙战士的立场。对于一些革命论者提出的关于他的思想“突变”之说,他是不以为然的,甚至是反感的。一九三六年,日本侵略军攻占我国东北,民族存亡迫在眉睫,这时,左联领导人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以使文学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在这个口号已经在文艺界产生很大影响的情况下,鲁迅却支持胡风提出另一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长期以来,文学界一直把“两个口号”之争看成是宗派主义之争,或者无谓的纠缠,其实不然。由于“国防”这个概念容易产生障蔽,“一切通过国防”,“国防”也就成了政府的一个代名词,通过国防的最高机构,最高统帅,这是鲁迅所不愿意认同的,虽然从形式方面的判断完全有可能如此。救亡是大众的,这是他的思想。民族问题往往掩盖阶级压迫问题。战争需要一种集中制强化的群体形式,这是专制政治的最好保证;正如齐美尔指出的,外部冲突将使群体的内聚力和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因此,民族主义的宣扬永远是有利于统治者的,尤其在战争时期。“与其做外国人的奴隶,倒不如做本国人的奴隶好”,这就是当时流行的民族主义论调的内核。问题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奴隶的命运,而不问主人为谁。因此,鲁迅强调“大众”在民族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其实质仍然是一个民主性问题。民主思想,是五四的遗产。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