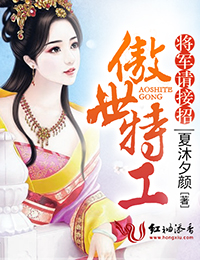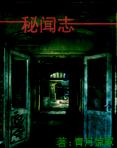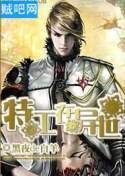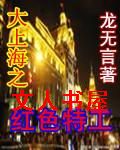特工秘闻-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国日报》,由康泽任社长,这便是复兴社的机关报。同时还有两个小期刊——
《我们的路》和《青年旬刊》。到1933年1 月,又将这两个刊物合并改为《中国革
命》周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机关刊物。《中国革命》周刊创刊号的发刊词说:
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
倭寇对我民族的凌侵,侮蔑备至;赤匪蔓延数省,民不聊生。攘外安内,实为
目前国家至迫切之要求。……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复兴中国革命的因素,是集中革命分子,凝成革命力量,
巩固革命政权;从现在的生存上的需要,是发展国家资本,充实民生,建设国防,
收回失地,报复国仇;从将来的国际形势的演变,是积极备战,准备应战,适应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力求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自由。
但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的客观条件所决定之复兴中国革命的要求,只是意
识着还不够,必须有行动,而行动的精神,又必然是铁与血。……
这个刊物所有各期的内容,也就不外是这个范围以内的东西,撰稿人也大多是
复兴社的上层骨干分子。但是它一直并不公开标榜实行法西斯主义,而只是愈来愈
多地介绍法西斯的理论和德意法西斯统治的各种情况。直到1934年7 月在我主编的
时候,我还在答读者问的通讯中说:“我们还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于中
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但是我们应该研
究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借镜。”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毕竟还不敢公然承认我们主张
实行法西斯主义,还是觉得抱着三民主义这块招牌较能迷惑视听;同时我们也实在
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
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在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
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
词了。
在《中国革命》周刊在南京创刊的同时,由贺衷寒于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出资,
在上海创办了《前途》月刊。这是一个“理论性”的大型刊物,与《中国革命》周
刊相呼应,同为复兴社的主要喉舌,由复兴社骨干分子大学教授刘炳黎主编,复兴
社分子大学教授孙伯赛、茹春浦、倪文亚、张云伏等共襄其事。最初面目尚不鲜明,
在其发刊词中所表示的态度,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将传统的个人本位的残骸,
迅速地葬送了去;将集团主义的新兴势力,严肃地建立起来;为民族的存亡而斗争,
为正义的存亡而斗争。”因此徐懋庸及其他一些较进步的教授,也在最初几期中发
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撰稿人多数是复兴社分子,他们对世界和中国前途的观察,显
然都是有着一致的看法和倾向的,但都有意识地说得不太露骨,只是从资产阶级的
一般观点出发,还没有明显地摆出封建法西斯的面目来。这是因为上海当时是全国
文化的中心,为上层知识分子汇集之地,他们不能不首先采取试探的态度和渐进的
方针。直到该刊第六期,贺衷寒才露面,开始刊载了他的文章,接着,蒋介石的训
话也就老是在该刊占着第一篇的地位了;同时关于法西斯的译述,也逐期增多。其
他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论著,也逐渐更多地表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显著倾
向。其撰稿人除蒋介石、贺衷寒、邓文仪、萧作霖等人外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教授和
作家,其中还有少数是名教授、名作家、名艺术家,并且将近半数是复兴社分子。
因此,这个刊物在当时的上海文化界也颇有一定地位。
此外,大型日报有由余洒度主办、在北平发行的(北方日报),有由贺衷寒主
办、初在南昌发行、后迁汉口的《扫荡报)。期刊有由刘健群主办、张佛千主编、
于1933年8 月在北平创刊的《老实话》。这是一个小报型的周刊,没有什么理论性
的论著文章,专门刊登对共产党与其他较进步的党派和人物造谣诽谤。耸人听闻的
报道以及一些内幕秘闻之类的社会新闻,借以迎合一般有闲阶级和中下层知识分子
的趣味,发行量颇大。此外,还有由蒋坚忍主办、在杭州发行的《人民周报》和由
我主办、在南昌发行的《青年与战争》周刊,都是先后创刊的复兴社重要刊物。《
青年与战争》周刊最初每期只刊载一些关于“剿共”的宣传鼓动性的短文,其后改
为大型的理论指导性刊物,内容与《中国革命》周刊差不多,到1934年7 月合并于
《中国革命》周刊。
其他先先后后、直接间接与复兴社有关系的各地报刊,也很不少。有由复兴社
分子主办的,如黄雍在福州主办的《南方日报》和开封的《河南晚报》;有由复兴
社分子参加合办的,有由复兴社分子担任编辑的,有为复兴社地方组织所运用的,
计有杭州的《国民新闻报),青岛的《新青岛报》,汉口的《新中华日报》,南京
的《中华周报》、《国际译报》、《中国与苏俄》月刊、《际周报》,上海的《新
社会》半月刊、《思想》月刊、《民族文艺》月刊,天津的《现代社会》周刊,西
安的(西北评论》半月刊,长沙的《乐群》周刊,还有其后我在南京主办的《内外
杂志》,等等。各地组织和会社员个人还办了许多小型报刊。各军校政训处和各级
部队政训处也办有不少大小型报刊,如中央军校政训处发行的《黄埔月刊》,连同
各级军队特别党部和各省市国民军训委员会及其他有关机关团体所办的各种定期刊
物在内,估计至少在100 种以上。
图书出版机构,有最早由邓文仪主办的拔提书店。这个书店总店在南京,并在
汉口、南昌、长沙、贵阳等地设有分店。1932年它发行过由汪漫挥主编的一种文艺
月刊和由程拂浪主编的一种关于国际问题译述的月刊。它所出版的书籍约有二三十
种。它的主要业务,是大量出版蒋介石言论集、蒋介石传记及其他为蒋介石个人作
宣传的小册子。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后,于上海环龙路50号设立了一个中国文化书局,出版了一
部国联秘书厅编辑、内外通讯社翻译的《国际联盟军备年鉴》(1933年的)及《青
年丛书》、《军事丛书》、《名著丛书》等共约20种,此外还出版了内外通讯社编
译的《内外类编》小册子共40余种。“内外通讯社”是南昌中国文化学会总会所设
立、由吴寿彭主持的一个编译机构,主要是编译有关国内外大事和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动态的专文专论。这个书局设立仅半年之久,即随着中国文化学会的被取
消而停闭了。此外还有刘炳黎在上海筹办的前途书店,也出版了《民族革命文选》
及其他几部书,但终于没有正式办起来。复兴社在出版事业方面,较之CC团是远远
不及的。
复兴社的各种报刊,遍布全国各地,对于散布法西斯毒素确实起了一些作用。
但是复兴社本来就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可为依据,总社又没有一套全面的计划和
集中领导,而只任凭各个报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而许多报刊又都是任由主编人
胡乱发表言论,而且翻来覆去,总不外是“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拥护一个党、
一个领袖”这一套滥调。因此,这些报刊的宣传效果越来越小,连那些编辑者和撰
稿人也都不免有点不大起劲了。到了前面所提到的1933年12月25日在南昌成立中国
文化学会以后,复兴社的法西斯宣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的经过是这样的:最初是我认为有必要开展一个全面的新的
文化运动,以转移风气,振作人心,而首先应从革新生活作起,并先由复兴社组织
的会社员带头作榜样。因此,我写了十几条意见和邓文仪商量,经邓拿去给蒋介石
看了,蒋大以为然,说这不仅可行之于复兴社的会社员,并应推行于全国。于是他
就拿去搞起所谓“新生活运动”来了。但是我们仍然决定成立一个中国文化学会来
搞我们自己的一套。经邓文仪、贺衷寒、吴寿彭和我及其他几个在南昌的复兴社高
级骨干商讨决定,并征得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那些号称“专家学者”的人同意参加
发起,便起草通过了缘起,筹备成立。虽然列名发起的几十人中知名之士很少,号
召力太弱,但是我们决定先成立起来再说。成立会奉蒋介石为名誉会长,推邓文仪
任理事长,我任书记长,并在南昌戴家巷14号把牌子挂了起来。首先第一件事,就
是提出和宣传“我们的主张”。这个“主张”除了标榜“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
动之最高原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吸收各国进步文化,创设新中国文化”之外,
还列举了十几条细目,但是它的中心内容在于“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
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根据三民主义指斥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谬误,辟除
阶级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为了推动各省市成立二十会,大家认为上海最重要,
如不能在上海打开一个局面,造成声势,将很难在全国各地吸弓!文化界人士参加,
普遍展开运动,因此决定由我去上海会同刘炳黎等筹备成立上海分会。
我于1934年2 月到上海,即与刘炳黎、孙伯赛、倪文亚等及复兴社上海市组织
的负责人共同商讨进行,首先征得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
大学校长黎照寰、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等参加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设于环龙
路76号),并通过全体筹备委员及文化教育界中原有复兴社分子,广泛展开征求会
员的活动。不及一月,即征得约七八百人人会,其中半数以上为各大专学校学生,
大学教授也约有百余人,余为中小学校长、教员、机关职员及少数作家和报刊编辑、
记者,随即举行了成立大会,选出吴铁城等20余人为理事,组织理事会,并推吴铁
城、刘炳黎、萧作霖为常务理事。这样,在上海的局面算是初步打开了。同时我即
将《青年与战争》周刊移沪发行,《中国革命》周刊也迁沪由我负责主办;又将我
与左曙萍合办、在南京出版的(流露》文艺月刊改为《中国文学》月刊移沪发行,
撰稿人有赵景深、宗白华、段可情、高植、张天翼、徐仲年、陈梦家、庄心在、汪
漫锋、王一心、陆印泉等,此外,还办了一个《文化情报》周刊。加上原在上海发
行的《前途》月刊,我们共有五个刊物集中于上海。我们在上海展开了这样一个局
面,对各地文化学会分会的筹备,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杭州就紧接着成立
了文化学会浙江分会。
文化学会浙江分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文化前卫队”,这个组织还举行过宣
誓典礼,请文化学会总会和上海分会分别派员去监誓和观礼。当即由我一人同时代
表总会和上海分会前往参加。我买了一把剑、一把大刀带去,剑作为总会授予,刀
则作为上海分会的赠礼,用意是以刀和剑象征铁和血和“文化前卫”的精神。宣誓
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会场布置得很庄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