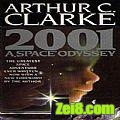书屋2001-11-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为强调民本主义,便是对君权的限制,却想不到民本主义只能规范个别的统治者的胡作非为,却不能限制整个统治集团和传统的权力体系对民众利益的侵夺。更为严重的是,民本主义既加深了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又使中国历史长期处于恶性的周期动荡之中。因为民本主义之可能,往往同“汤武革命”、“替天行道”等革命话语和行为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话语和行动在中国古代,只能恶化权力之争,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命运。这里面的联系,中国知识分子是看不到的,其结果便只能使他们的社会关怀带有强烈的悲剧意味。一方面,他们极力鼓吹民本主义,视“汤武革命”式的权力之争为正义的事业,并将其同自己的是非观价值观相联系;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努力却很难解决社会的正义问题。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手里拿着两面盾牌,一面是防范统治者对民众的侵害,另一面则是防范民众对王权政治的危害。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和是非观里,既要对王权负责,又要对民众负责。对王权负责,是因为王权代表秩序,并且是天意和民意的体现;对民众负责,是因为他们是社会的良知,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如此又决定中国知识分子手里的两面盾,又可理解为两支矛,一支投向王权,意在保护民众;一支投向民众,意在维持王权的神圣。这样一种互为矛盾的社会角色,直接使得他们左右为难。一方面,最高统治者将他们视为异类,并尽可能将其奴化和工具化,对那些不驯服者,则采取各种分化与迫害的措施消除他们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很大一部分踏入仕途,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同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连为一体,并因此而损害民众的利益,故人民大众并不将他们视为代言人,而是将其看做统治集团的成员,同样是革命的对象。此种处境,可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在君权与民本的关系方面,更为可悲的还在于,每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由于认识不到内中的真正原因,故将其责任尽可能往自己身上揽。在他们看来,统治者的荒淫无道,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到“王者师”的责任,有愧于为臣之道;而百姓生活困苦,同样是他们的责任,没有尽到“治国平天下”的义务,有负于儒家的宗旨。这样一种原罪心理,落实于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便是道德理想主义情绪的高涨,试图通过改朝换代的形式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的正义问题,从而使在上的为政者贤明仁厚,使在下的民众可以脱离苦海。由于理想的崇高,他们也就不惜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而投身于实际的斗争之中,却不明他们的代价所换来的究竟是什么。
(三)道统与政统之间
在中国思想史上,“道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道统是相对于统治而言的且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同的一种理想的观念形态。狭义的道统则是儒家内部侧重于心性之学的正统派别,其说法开端于韩愈的《原道》。本文所言的道统,主要是其广义。
道统与政统的关系,按照中国传统文人的用语,又可简称为道与势的关系。
前文已述,先秦的士阶层之所以重视一个“道”字,并非出于本体论或宇宙论的理解,而是出于政治伦理的需要,确切地说是想用一个“道”的范畴来实现规范为政者的施政行为。所以在当时,诸子们都把“道”的地位置于王权之上。孟子的一段话最能反映士人的普遍看法:“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12〕孔子说:“道不合,不与为谋”,这不仅是他的为人准则,也是他对待道与势之关系的态度。他周游列国,屡屡不能得志,甚至被人骂为“丧家之狗”,并非他的才智有限,而是他所尊崇的道不为诸侯国君所理解。也就是说,孔于是不愿意屈道而求官的。他的“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种种说法,皆可说明在他的心目中,道是高于一切的,为之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曾子和孟子才有“死而后已”和“以道殉身”的豪言壮语。
先秦诸于特别是儒家道尊于势的理念,直接为后儒所继承,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后儒对道与势之关系的义理表述,更是多矣。让我们看看明儒吕坤的一段话,就可略见一斑:“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也,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13〕
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多年来一直抱着道尊于势的理念。所以他们才会有“志于道”的理想,才会有“王者师”的自我定位。因为在他们自己看来,“道”虽是先王之道,但自己却是道的使者,或曰道的“肉身载体”,如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上帝的肉身载体一样。这样一种信念,无疑使他们显得崇高,但同时亦使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而显得非常难堪。
无可否定,在战国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确体面过百余年,尤以稷下学的盛期为典型。当时,各诸侯国君大多将其作“王者师”看待,且给予优厚的待遇,真可谓“礼贤下士”。孟子的一生,最可说明这一点。他周游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尽管国君们对他毕恭毕敬,但孟子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还时常予以挖苦和嘲弄,并说“说大人侧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意思是说,不要以为那些国君位高权重就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根本不要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且在那时候,国君们非但能够容忍士人的倨傲不敬,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段时光毕竟只是昙花一现,只是一段美好的记忆。他们在这段时期的风光和体面,主要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一旦此种历史环境不复存在,他们的处境也就江河日下了。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虽然秦汉以后,政治环境日趋恶劣,但他们并未放弃道尊于势的理念。而且情况还恰恰是,政治环境愈是恶劣,他们的社会关怀意识愈是强烈,愈是感到道尊于势之必要。由之而决定着在道与势之关系问题上,他们是不可能将其解决好的。或更确切地说,从主观上,他们希望道尊于势,甚或以道压势,但由于他们的实际社会身分和对道的政治伦理化的理解,又从客观上导致了以道助势的结果。其缘由是;
第一,如前文所言,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荣辱进退全赖于朝廷的是否起用。这样势必使他们将自己的前途置于道义之上,从而很难做到“谋道不谋食”和“忧道不忧贫”。更有甚者,他们为了仕途和利禄,还极有可能迎合权贵,全然忘了自己的道德良心。对此,徐复观曾作过非常精彩的分析:
“知识分子的精力,都拘限于向朝廷求官的一条单线上,而放弃了对社会各方面应有的责任和努力。于是社会既失掉了知识分子的推动力,而知识分子本身,因活动的范围狭隘,亦日趋于孤陋。此到科举八股而结成了活动的定型,也达到了孤陋的极点。同时,知识分子取舍之权,操之于上而不操于下;而在上者之喜怒好恶,重于士人的学术道德,于是奔竞之风成,廉耻之道丧;结果,担负道统以立人极的儒家的子孙,多成为世界知识分子中最寡廉鲜耻的一部分。”〔14〕
第二,中国知识分子所信从的道或道统,主要的是先王之道。按照韩愈的理解,乃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于传之孟轲”的心法。由之可知,道统是同圣王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尧舜禹汤等人物既是道的化身,又是世间的君主。而且在儒家看来,凡王者都是道德高尚之人,所谓“有德者王”、“惟仁者宜在高位”等等说法,都是指的这个意思。虽然儒家此种话语是从应然的角度而言的,但其作为一种政治伦理规范一经提出,便是人们思考政治问题的价值标准。如是,其结果便是将道统与政统作一体看待,将道统所应抑制的对象视为与道统相同一。这样一种话语,实则是从观念上打通了政教合一的关节,使道统与政统不再是一种孰高孰低的关系,知识分子亦由之而失去了以道制势的使命感,甚至还会认为他们的奴性是必要的,是“志于道”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注释:
〔1〕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2〕参见拙著:《中国文明史》上卷,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3〕关于“士”之初见,学界说法颇多。吴承仕和杨树达二先生认为“士”之初义为农夫,不确。顾颉刚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虽无谬解,但却没有说出个究竟。依我看,周代的“士”为武士,主要是由于当时等级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周代的分封实为殖民,诸侯在其封地上,必有自己的军队,而殖民者贵族集团中地位最低的士便是其主要的兵源。再者在远古社会,人们皆以作为战士为荣,平民是没有资格打仗的。执干戈以卫社稷既是士这一等级的义务,亦是他们的荣誉,同时也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价值所在。到春秋时期,士主要是文士,而作战的主力则转为平民。
〔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336页。
〔5〕我疑《尚书》中的夏书和商书,多为周人的伪托,其类似于“恭行天之罚”的话语,乃是周代才有的政治观念。
〔6〕参见拙文《儒家德治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周期动荡》,载《开放时代》1996年第5期,另见《启良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5页。
〔7〕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8〕参见拙著《神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34页。
〔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10〕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8页。
〔11〕将民本主义等同于民主政治是二十世纪中国学者的一个误识,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再到现代新儒家,都犯有这样的思想毛病。关于二者的本质区别,可参看拙文《关于我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思考》,载《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此文亦收入《启良集》。另见收入本文集的《传统民本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一文。
〔12〕《孟子·尽心上》。
〔13〕吕坤:《呻吟语》卷一,《谈道》。
〔14〕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关于周扬的思考
? 叶 凯
周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这种复杂不同于我们往常遇到的作家、思想家或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家,虽然他们的思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