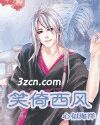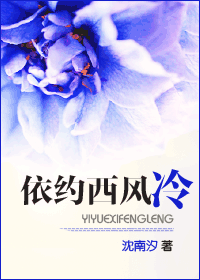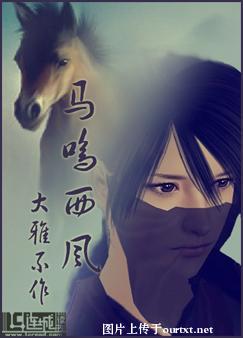西风吹书读哪页-纽约时报书评 100年精选-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成为一个不寻常的引人入胜的故事。这些米切尔小姐都以绝对真实的态度
告诉了我们,最后有了一个符合逻辑毫不牵强的结尾。嫁给艾斯利的美兰妮
和艾斯利不过是这两个人的陪衬。他们两个才是米切尔小姐细致描写的人
物,是她故事的核心。她当然还有其它一些粗线条的人物。事实上,她是在
战前,战时和战后重建这一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她的人物的。
现在对米切尔小姐的未来做任何预测都为时过早。她已为自己第二本书
定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目标,我只希望她不要考虑太久。
(佚名,1936 年7 月5 日)
特别的K──《审判》,
弗?卡夫卡著
几年前,已故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的《城堡》在美国出版时,没有引起
普遍的轰动,但立即被少数人认定为一部杰作。岁月迁流,其他的人——尽
管依然人数甚少——也同意了这种观点。我得承认还没读过《城堡》,但已
有这个打算。我读了《审判》,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读过一部比它更令人震
惊,但又绝非那种粗俗的故作惊人之语的作品了。
《审判》并非人人能读。它令人激动的独特风格对那些习惯于“刺激的”
书的人来说,的确显得平淡乏味。许多小说通过恶心可怕的形象令人毛骨悚
然,而《审判》却像少数小说那样,通过真正的危险或悬念而令人恐惧。它
揭示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世界里扭曲、怪诞的形象。它一只脚坚定地站在大
地上,你很难找出几本双足比它站得更稳的书来,然而它的另一只脚却伸向
无垠的太空,由此赋予表面上的动作以深层的涵义——或者说是暗示的能
力,因为涵义这个词往往含混不清——这种深层的涵义称为梦幻最为恰当。
小说的特色由其情节可见一斑。约瑟夫?K,一位年轻的银行官员,有天
早上起来时发现自己被捕了。他自知绝没有犯罪,而且当时乃至以后他都未
被告知其罪名是什么。他还拥有自由,只是必须定期去法院。法院是个怪异
的地方,充满了其他的被告和数不清的低级官员。在法庭上,K 可以慷慨陈
词,但对他的审判却从来没有任何进展。
故事叙述的不仅仅是对K 的“审判”,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他在
银行工作的情况,还有他和房东太太以及隔壁住着的年轻女人的关系。在所
有这些问题上,K 都感到不确定,感到沮丧,正如他的审判一样。这本书梦
幻一般的特色首先得归因于那种沮丧感。这正是我们在恶梦缠身,驱之不去
时的感觉。
任何摘要都无法传达出卡夫卡巧妙提炼出来的氛围——K 被迫漫游其中
的、像白痴、像地狱的迷宫里的氛围。他越是想控制局面,被困也就越深。
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也具有独特的力量和成就。但《审判》在
道德上的影响远胜过它在心理学上的影响。卡夫卡本质上是一个宗教作家,
具有强烈的对与错的观念以及不可泯灭的了解事物未知本源的愿望。因此他
的小说是一部伟大的普遍的寓言书,这部寓言书并不平淡,也充满了人类生
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这正是作为小说家、幽默大师、证理学家及
讽刺作家的卡夫卡在这些方面的天赋的又一佐证。在象征地写作的同时,竟
然能写到K 的律师的滑稽地鼓起来的衬衫,接着又在稍后的场合以风琴一般
深厚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感——这样一位作家的逝世,实在是文学的一
大损失。
(路易?克罗农伯格,1937 年10 月24 日)
干旱尘暴区的布鲁斯──《愤怒的葡萄》,
约翰?斯坦贝克著
这是一部鸿篇巨制,是斯坦贝克的作品中最长的一篇。然而读起来却像
是一蹴而就,从打字机上扯下来,像最后通牒一样被送到公众的手中。思考
时它是一部很长的有思想的小说,感受时它则是一个短暂而生动的场面。
旅行安排得天衣无缝,精妙的短篇小说一篇接着一篇,并熔为一体,铸
成这部远足式的长篇巨著。
加利福尼亚人是不会喜欢这部小说的。美丽富饶的加利福尼亚藏起了人
类的恐惧、仇恨和暴力。西部的农民管她的居民叫“Scairt”,他们被络绎
不绝的急于找到工作的工人吓怕了,在感到害怕的同时他们变得恶毒和残忍
起来。这一部分故事读起来就像是来自纳粹德国的新闻。来自俄克拉荷马州
的家庭,人称“俄克佬”,工作时他们就住在与集中营无二的房子里。在成
千上万涌向西部的人当中,只有极少的几百人能找到工作。他们的工钱也从
每小时30 降到了25 美分,甚至20。要是有人表示异议,那他就是一个绝种
人,煽动者,一个喜欢寻衅滋事的家伙,因此他最好从这个地方滚蛋。代理
治安长官到处都是,他们带着枪和大棒,合法地枪毙或是打死来自其他州的
胆敢对加利福尼亚法律提出质疑的任何人。在这片充满恐惧和暴力的土地
上,乔德一家人在某个政府的营地上发现了唯一一个讲道理、有尊严的地方。
当他们星期六晚上洗完澡去跳舞时,跟着他们真是一种快乐。然而即使在这
里,由操纵农民协会的银行雇来的代理治安官也拨弄着枪支,借口是有人试
图挑起暴乱,因此有必要采取保护性的管制措施。乔德一家在加利福尼亚辗
转迁徙,在无名枪弹的追逼下摘着2。5 美分一架的桃子。她们只渴望拥有一
小片没有枪的土地,一片他们可以定居下来,可以像过去一样劳作的土地。
加利福尼亚希望的葡萄已经变成愤怒的葡萄,随时都可能成熟。
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实,无论哪个评论家都说不准。但我们可以很容易
补充说:小说没有结尾;牧师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破坏了罢工;汤姆从加利
福尼恶的法律下亡命而去,无影无踪;小说以感伤的小调结束;在洋洋洒洒
600 页之后,小说嘎然而止,仅仅因为是部小说,就总得有个结局。这些都
不假,但更真实的则是斯坦贝克从自己心灵的深处,倾注了罕有其匹的真诚,
写出了这样一部小说。也许它是有意夸大,但这是一位诚实伟大的作家的夸
大。
(P?M?杰克,1939 年4 月16 日)
犯罪与惩罚及其剖白──《土生子》,
理查?赖特著
最简便地表达这部小说的重要性的方法就是把它称作一部黑人的《美国
悲剧》,并把它大致与德莱塞的杰作相媲美。两部小说都严肃有力地描绘了
社会失调、环境和个人行为等问题,并由此描绘了犯罪与惩罚。两部小说都
是悲剧,德莱塞的白人孩子与赖特的黑人孩子都同样被施以电椅处死,但并
不是因为他们是罪犯(因为他们都没有犯罪预谋),而是因为他们是社会的
杂质。两本书的模式很相近:家庭、青少年、金钱与性的诱惑、审判和死亡。
两本书的结论都是:社会应受到谴责,他们每个人生下来所处的环境把犯罪
强加在他们头上,他们是一个普遍不公的制度的牺牲品。
赖特先生的《土生子》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不公是种族不公而
不是社会不公。德莱塞小说中的克莱德?格利菲斯代表了一种社会“情结”,
这种“情结”能得到一定的注意。赖特先生小说中的比格?托马斯则远处在
社会力量之外,他代表的是一个僵局,而不是情结,他的悲剧是和一个永远
不变的黑人少数民族与生俱来的。从字面上,用他的话说,是“在出生之前
就受到了鞭笞”。赖特先生在比格最终被鞭逐出这个世界之前给了他一个短
暂醒悟的时间。
比格的生平叙述以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象征性的事件开始。他20 岁,和
他的母亲及妹妹维拉和弟弟巴迪一起住在芝加哥南边黑人聚居地的只有一间
房屋的公寓里。他们每周付8 美元的租金,靠救济生活。在他的故事中,比
格清晨起床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去打一只钻进屋子里的大老鼠。他神情专注
地追打老鼠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动作。
后来比格在同一天接受了救济机构给他的一份工作, 给一个仁慈的芝加
哥的高级行政人员做司机。这位达尔顿先生为了社会福利,尤其是为黑人的
事业,向国家有色人种发展协会捐献了上百万的钱,虽然这些钱的绝大多数
都流到了社会上一些典型的俱乐部之类的机构里设的乒乓球台上。比格对此
一无所知,更不知道达尔顿的慈善捐款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向居住在他拥有
的黑人聚居地的黑人们勒索的房租,而那些黑人们的住所却是拥挤不堪,鼠
灾泛滥。比格还不知道,这笔钱正来自于达尔顿向他勒索的他今天早上刚刚
离开的那个房子的租金。
第一天晚上,比格要驾车送达尔顿的女儿玛丽到一个大学听讲座。玛丽
在实践社会学上已经比她的父母走得远了一些,她指使比格把车开到“共产
党总部”,而不是学校。在那儿她碰到一个几乎很完全的“共产主义者”。
他和比格握了手,希望他叫他的名:若望。他们一起坐在前排驱车到一家黑
人饭店,喝了很多酒,绕着公园兜圈,而若望和玛丽却在旁边做爱。最后,
比格在大约早晨两点钟才把酩酊大醉的玛丽用车子带回家,他口袋里塞着一
摞从若望那里得来的宣扬共产主义的小册子。
比格是怎样无意中杀死玛丽的经过,只能用赖特先生的话来解释。需要
指出的一点是:他发现自己惊惶之中杀死了她,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被人(不
公正地)怀疑强奸了她。当她失明的母亲来到比格刚刚把玛丽抱进的那间卧
室的时候,比格拉过一只枕头压在这个姑娘的脸上,以阻止她说出他在那里。
他下意识地用力按着枕头,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用力过大。当达尔顿夫
人离开卧室的时候,她的女儿已经死去,而她却以为女儿只是喝醉而已,她
更没有发现比格也在卧室里。
这就是比格悲惨历史的始末。他把她的尸体扔进了熔炉。因为她的头部
无法进去,他便用斧子砍了下来,之后,他打开排气扇以消除地下室里尸体
烧焦的气味。比格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寻求对策。作为一个黑人,他将是第
一个嫌疑对象。比格想,“共产党人若望”,几乎和他一样是众矢之的。他
从政治家那里得知,“红色分子”是最卑劣的一种犯罪分子。比格可以轻而
易举地把罪行推卸到若望的身上,宣称是他和玛丽一起回的家。他甚至可以
勒索绑票钱,用以伪称玛丽仍然活着。或许我们可说,这是一个典型的犯罪
心理,但这是赖特先生为了说明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和种族条件的有意安
排。比格的罪行很快昭然于世。为了掩盖他的作案痕迹,他又一次犯罪(这
一次只不过是杀死了他的黑人情妇),然而从他逃遁到命运的审判只是一个
时间问题。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犹太律师为比格做了一次很精彩的辩护,但
除了做一次解释的尝试之外,他再也无能为力了。
有人争辩说——我相信的确如此——他的主人公比格的表达太嫌清晰。
他在小说的后半部过于清晰地解释比格是如何接受命运的:“看起来有点合
乎自然,我就在这儿,面对着电刑椅。现在我开始考虑这件事了,这似乎是
非这样不可的事了。”后来,他把自己的话浪漫化和合理化,宣称:“我之
所以杀人,一定是为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