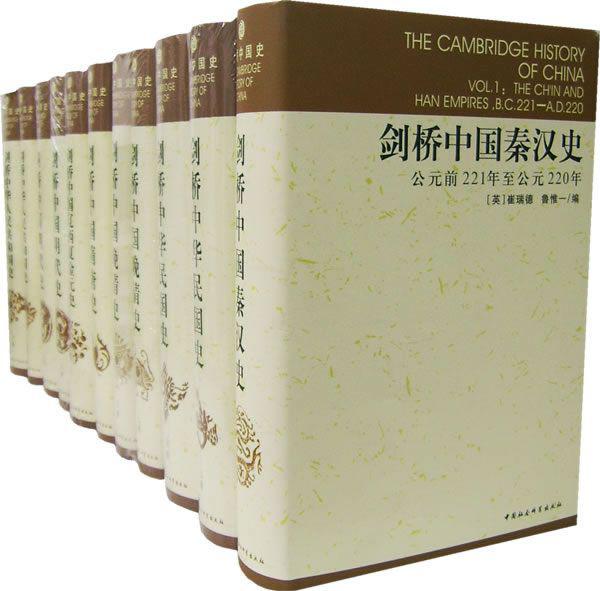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9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
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
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
(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们如魏野畴执
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连同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法国的俄国。思想影响
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
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
思主义的接触。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社会状况所验证,并在上海和北京这
样的大都市里被表述出来,远在国家内地的一些地方如成都和榆林引起反
响。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皈依者屈指可数;其中一些人年龄
较大,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知道1913年内战中的起义以及1915
年和1917年复辟帝制企图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至
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能称为研究学术的学者。对于他
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讲,知识总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地
学习的收获。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
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
①他们卷入和干预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胡适博士是个例外。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探求知识方面不那么勤勉,或者不那么细致,虽
然他们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学会中集体学习。他们反对传统,意识到传
统将被废弃,并在寻求一种将其彻底铲除的方法。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
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异化,这或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威信
的社会地位。
他们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方法使国家值得他们为之献身,在
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
人们热爱中国,因为她可以变成值得爱的国家,①不只是因为他们生来是中国
公民。②这种落后状况集中体现为经济的停滞,如陈独秀于1918年指出的那
样,或者如毛泽东大约10个月以后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
所写的那样。③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
① 关于这一点,我要感谢阿德里安〓陈:《1925年以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特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博士论文,1974年),第39—40页。但是,他在这个部分将其研究仅仅局限于陈独秀,而我认为李大钊、
董必武、吴玉章、林祖涵,更不必说毛泽东,无疑都有同样的倾向。又见迈斯纳:《李大钊》,第106页。
① 关于“爱国”的最完整的说明,见于陈秀独所作《新青年》的《本志宣言》,7(1919年12月1日),
第1页。
② 李大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1915年,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
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显然李没有为这些不足辩护;也没有试图
为其辩解。他的困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不足最终将使一个爱国者的努力成为徒劳,而且只要这些
不足仍然存在,他的爱就将一直得不到报偿。为使他从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脱出来,他聊以自慰的是著
名的凤凰涅槃式的中华复兴的观念。但是后来,在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信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由于
将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他从其狭隘的、先验的民族主义,转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人类的伟大使
命上来。迈斯纳:《李大钊》,第22—23、27和180页。
③ 陈独秀:《文存》,2(1918年9月15日),第275页,及竹内编:《毛泽东集》(以下作竹内本),
1(1919年7月7日),第53页。
她探索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向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
思主义者之一。她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④
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腐败的官僚和无
耻政客的扈从们所助长的精神消沉、道德沦丧①和不受约束的军阀主义。②这
些军阀及其支持者,毛泽东含糊地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③中国的这些
强大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靠山,获得这种认识对于这些激进的思
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的、极其重要的发现。④这为后来诸如阶级斗争、剩余价
值的剥削、受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类概念的应
用,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根本认识方面的变化还是逐步的,
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十月革命以及对于巴黎和
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加速了这种转变。
如陈独秀以颠覆罪受审时,在他自己的辩护词中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
标志了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日子以前,他重新振兴中华的呼吁
是针对知识阶层发出的;此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劳动人民身上。“盖以……
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1919年早些
时候,由于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日益敌视,其
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
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反对资本家的剥削。①确实,李、陈两人对
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而言。按照他们的理
解,他们的“民主”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要求广泛得多的群体参与。
在那年1月,陈在《每周评论》——一种激进的期刊——著文,主张需要一
个有群众追随的政党;到3月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的思想更达到了某
种类似于人民专政的程度。②在这两篇文章之间,这份刊物登载了一篇题为《中
④ 见李立三的文章,载《红旗飘飘》,5,第28—31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2,载《五四时期期刊
介绍》,1,第154—155页。
① 陈独秀:《文存》,2(1916年10月1日),第85—86页;和4(1917年3月1日),第52页;石峻:
《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五四时期主要论文选》(以下作《思想史资料》),第1906页,1917年2月1
日;关于李在1915—1917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迈斯纳:《李大钊》,第24和34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81—82页,原载《甲寅日刊》,1917年3月29日;陈独秀:《文存》,1(1916
年2月15日),第53—54页;《新青年》,3。4(1917年6月);及陈独秀,同上书,1(1918年7月15
日),第222页;和2(1919年11月2日),第387页。
③ 《民众底大联合》,1919年,竹内本,1,第61—64页。
④ 陈独秀的两篇文章,载《每周评论》,4(1919年1月12日)和8(1919年2月7日)。同时,李大钊
从他1915—1916年的达尔文式的内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1919年1月的坚定的反帝立场,见边斯纳:《李
大钊》,第24页,以及李的社论《新纪元》,载《每周评论》,3。
① 陈独秀:《辩诉状》(出版处不详),标明的日期为1933年2月20日,第1页。还可参见陈于1919年
3、4月份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文章,它们预示1919年11月2日的那篇经常被引用的文章《实行民治
的基础》的出现。对于陈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日期在李大钊之后一年或两年的看法,如许华茨的《中国共产
主义》第22页和迈斯纳的《李大钊》第112—113页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是知道的。然而,尽管陈对J。
杜威的论述是很客气的,他11月份的文章不仅批评杜威的民主观念“还有点不彻底”,而且明明白白地将
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置于其经济基础之上。参见《文存》:1,第375页。关于李大钊的观点,见《晨报》,
1919年2月7—8日。
② 《文存》,3(1919年1月19日),第589—591页以及4(1919年3月26日),第646页。
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的社论,号召一场推翻士大夫统治的工农社会革命。
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和李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他们的
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但相继演进的过程是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
政。到那年年底,陈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
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
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6个月以后,陈
以一种肯定的口气写道,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由工人创造但被资本家从他
们那里盗走的剩余价值。①
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
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们注意焦点的这一转
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他们的视野更为宽广,他们
的同情现在推及所有的穷苦人。对外,他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他们跟随《每
周评论》的榜样,《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个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
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涉
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和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悲惨境
遇的一系列论题的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涌
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就已经有为了劳动者或者关于劳动者的专门杂
志,它们提供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扶植对劳动的新态度,并且引起人们
对于一些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注意。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
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工作,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
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
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人们一定要问:不依靠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
社会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呢?当权人物会让这些目标通过和平的转变过程而得
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那些被觉察了的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者、
军阀和腐败的官僚,已经被确认了,但是,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
民大会”是无法将他们从掌权的位置上赶走的。②在这一点上,1911年(中
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在陈的头脑中,
欧洲的繁荣是其历次革命的结果;在李的头脑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牺牲之
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①如同《每周评论》著名的社论《新纪元》(载于
1919年1月,第3号和第5号)解释的那样,进化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由于驱使人去剥削人的少数人的贪婪造成了一种竞争的而非合作的状态,其
后果便是社会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通过革命以外的其他手段是无法消除
的。对于李、陈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