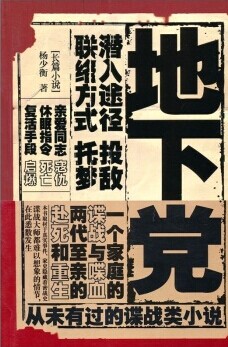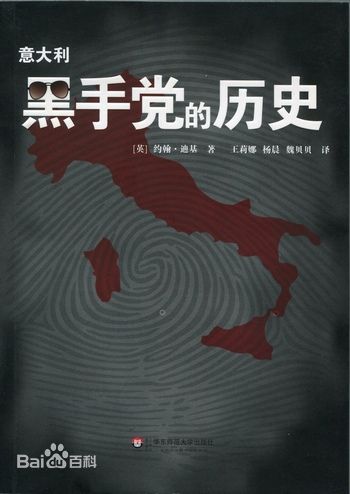���µ�-��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һ��Ʈ��������ʱ�������ţ�ʱ����Ȫ�ݣ������ܵ���̨�塣��ˣ����Ǽҵ����Ӷ����Ƕ���������塣
ĸ�������ʱ��ȫ�ҿ�����Ҫ�����������������֮���������ϵ�һ�ж��ӹ�������Ϊ����ҵ���Ҫ���������������С����ͷ��֮˵������Ѵ������ͷ���ã������������ͷ������Ϊ�������˱ص��Ǵ��ͷ�����ϳ������ܹ˵��ã����½������⡣���ǼҴ��Ǯ���������ִ��ͷ��
����ĸ�ʹ��ȴ��һ��ԩ�ҡ�����������֪�����˶�˵��㳤�ø�����ʱ��ĸ��һģһ�������ߡ���ͷΪһ��ģ�ӷ��棬����������Ҳ���һ�ޣ����������ù��£������ӣ��������������ˡ����СС���ʱ�ͻᶥײĸ�ף�ĸ���������Ǹ������Թ�����Ҳ�������Ӽ��������Ǻ������������������������ġ������Լ���������ë�������ζ��Ƶ�ĸ�����ϣ�����ĸ�״������⣬��Ҳ�����Ŀڡ�����������ˣ���ɼ��е�֧����ĸ�������ٶ���ָ��dz⣬ȴҲ�ܻ�˽�±�Թ��������������Ǹ����ԣ���ô��������������������˻��ᷴ��������ķȥ���Լ�����������֪��ĸ�ʹ��֮����һ���Ľᣬ������йأ���ô�����ȥ������˭����������ȴʼ�����������������ĸ�۵����������к�Ů����Զ����Դ��������к����ط��ʱ��һ����ĸ��ǣ���ְ������ͽ�ѧУ�������ж������ѣ��Ĵ���ǮҲҪ��������ѧ��Ů����ͬ����ν��Ů���ű��ǵ¡�����ȥ��Ů���ó�ȥ��ˮ���αض��飿ĸ���Լ��Ǹ���ä�������Լ������֣���������ʶ�������֣�������һ��������Ů�����Ǽ���������ѣ������˳Դ��öȣ���Ҫ��ĸ��һ�����ĸ��û���������ܣ��Ը���ϴ�·�ı����ÿ���������������ں�ͷСԺ�ǿھ��ߣ���ˮϴ�£���ɹ���̣��������£����峿æ����ҹ�����Ǽ�ˮ������һ������ʯ���ƵĴ�ϴ���裬������ʹ��ĥ���ܱ�����ĥ�ù⻬�ޱȣ��ǹ⻬ȫ��ĸ���������;�ˮ��ĥ�����ģ�������������⻬��ĸ��Ҳ�ս��㲣�ֱ�����������ӣ���Ҳֱ�����������Ҿ���ˣ�����������Ů�����ô��ȥ������
�����Ǽ��ĸ���С��������ĸ��ѵ���㡣
���û��С�����������Ǹ������Թ�������ǿ��ʤ��������ĸ��һ����ӣ���С��ĸ��Ϥ�ĵ����£�ÿ���ĸ��һ�����𣬰�����ˮ���£���ĸ��ͽ�������֣��������ͯ��ϱ���ô����ѧ�����Ǯ��ĸ�����˰��֣���˴�������������ѧУ�ġ���������ȴ����ѧ��ԭ��Ҳ��������Ů������ĸ�����ŷ���������Ů���Ӧ����顣��
������ֻ��д�֣������Ǯ�����ַ�����飿��ĸ�ױ�Թ��
���ܲ��ϱ�Թ������ȷʵ���ѣ�ĸ���ǹԹѴ���ͽ�Сѧ����ʱ���׳����������ⱼ����ż������ͻȻ�������������߲�ʱ��һ���ţ����ʴ�С������ָ�������һ��֮����������������Ӱ����֪���˼��η���һ��Ǯ��û���ؼģ�ֻҪ�����˻���ĸ�Ͳ��ò�����û�а취��
���϶���������Сѧ��ҵ�����������ͣѧ��Ȼ����Сѧ��ҵ�Ѿ������㹻�ĺ��֣��������·����ö����ƣ��������ֵ�����Ů�����������С�ˣ�����ˣ��Ը����Ѿ����Խ�����ĸ�ײ��ô�������ѧ����������������������ϴ�£���Сͯ��ϱ�����һ����Ҫ���飬�ڼ���������죬ʱ�����С�����û��ë����Ҷ�ײĸ�ף�ȴ�����������ˣ����ʹ��ѧ��
��ʱ���Ǽ�����һ�����Ӻ�����˵�˻��������������ţ�����ͷ���������ȸ����ܸɣ�����֪��������Ū���˼�����Ԫ�ŵ�ĸ����ǰ��
���������飬��ķ���������������������ĸ�ס�
����Ҫ���˰�����ĸ�������Ҫ��ܡ���
�����˵�������Ǵ�磬�ҹ�������
ĸ�����ڻ��ǵ���ͷ����ν�������ĵ¡����������ӣ����ǹ�ء��������ִ�ԣ���ŵҪ�������ѧ������ֻ��һ�����Լ����뿪���ţ����ٹܼ�����¡��������̰�ڣ��߾�ȫ������ĸ������Դ˻�ȡĸ���Լ����������Ĭ����
���������꣬���ʮ���꣬���б�ҵ���������Ǽ��Ѿ���������ˣ���������˼�顣��ʱ����磬��������������Ǯ�������ڶ�Сѧ�����ڳ��������ر��ܳԣ����������ಡ����ĸ������Ե�ҩ���Ⱥȵ���ࡣ��������£���㲻���ܼ�����ѧ������Ҳ�������ĸ������㹻�����Ӻ�Ϊ֮��ͷ����������ĸ�ľ��ġ�ĸ���ô��ؼҵ����֣�����ʼΪ�����ɫ���˼ң���������ȥ����νŮ�ޣ�ĸ���Ѿ�Ϊ���Ů��������������ó�ȥ������ˮˮ���������绨���������꣬����һ�ų��б�ҵ��ƾ���õó��֣������������˼��Ѿ��dz�ϡ����
��㲻�Բ�����û�ж�ײĸ�ף�ȴ��ijһ����ҳ��ߣ�ͻȻ��ʧ������
����ĸ������һ�����������ĸ�⽨��˵���ǼҸ���ߵ����һ���ڰ�����Ҫ������Ѱ���Լ���ǰ;���������������������õ������ģ�ĸ�����մ��Ȼ���ޣ����IJ��ѣ�ʹ����Ů�����ã�����������û�����ġ������ȥ����Щ���ĸ��ʧ�����ǣ��Բ���˯���ţ�����ȫ�ǿֲ�������˵����Ư��һ��ʬ�壬��Ҳ���ľ����������²�ֹ��ֻ���������Լ���Ů����Ҳ�����Ǹ�ʱ�����ŷ����������ޱ���Ҫ��Զʤ�����Ǽҵ��κ�һ�����ӡ�
����º�˴������������ţ��������������Ϣ��
ԭ����û��Զ�߸߷ɣ�ֻ�ܵ������Ű���·�̵����ݡ�������һ��ʡ���ڶ�ʦ��ѧУ��ѧУ����һλ��ʦ�Ǵ��ͬѧ�����壬��ͨ��ͬѧ��������ȥ��������ѧУ����ʦ���ǹ��ѣ�ѧУ�ܻ�ʳ�����������ѡ����ĸ���������ˣ����һ��ס���������Ͻ�����Ӻϲ�һ��С���������С����Ϊ������㵽���ݺ�Ͷ����ˣ�ס���˼Ҽ���ѳ�ĸ������������ˡ�������û���⣬һ��ʮ���죬����Ů������ڼ�����飬�Ȳ����������棬Ҳû�ߵ���˼����˸о����Σ�һ�ʣ���֪����ϸ�������֪��ĸ��һ�������ˣ�Ҫ���������ţ��������ߣ����������ؼҡ�һ������ʦ�������ͰᵽѧУȥ��û�������Լ���취������һֱ�鷳��ˡ����֪����Ů���Ը�������ĸ��ǿ�Ȳ��ã�ֻ�ܷ����Լ���ͷ�����飬���ŵ����С���֣�˳�����������ݾ�ʯ���ܵ����ű��š�
ĸ��һ��������Ϣ����߷���һ���ģ��DZ��ֻ�ð���ɡ�
������ȥ���������������ô������ô���������̣���
����Ȼ����һ֧������Ҫ����˵����ݣ����Ƕ���ʹ���㡣���Ȱ��ĸ�����ˣ��ú������������ס���죬�Ȼ���ת�⣬���������ؼҡ�ĸ��ҧ���г��ô�˴�����������������ݶ��飬��������������Ӵ��ٲ������Ů����
��㻹���Ǿ仰��������Զ����ȥ����
������ʡ���ڶ�ʦ��ѧУ�����������ѧ����
�����Ժ������Ǽ��в����ᵽ��㣬ĸ��һ���������־ͱ������ף����������ǹ�������ڣ�����û��һ�������ۡ����־��������һ��࣬�������Ѿ���౻�����Ǵ����ڵ�ʱ��ĸ���Լ���ʼ��Ĭ������ٶ�����������ֻ�Ǿ�����Թ�Լ����࣬��Ů����һ����һ����û��һ�������������ڼ����������֪����ʱ���Ѿ��������㣬�Ҽ���ײ��ĸ���ڳ������Ժˮ���߶����д��ᣬ���ܲ³�����Ϊ��ʲô�����Ǽ���Щ����������������ײ����ʵҲ��������
��Ϧǰ����˰Ѵ���ͻ������š�
���˵���������ˣ��ི����������
���²��ǹ��꣬������ĸ�Դ��Ҳ�Ѿ�ʧȥ����������ɱ������ĸ��Ƣ���꣬����һ��û�кû������Լ������������������Ӳ���ڣ��ñ��ػ����ݣ��Dz�����ǡ�����������������˴��ؼҵ����ʱ��ĸ���Ѿ�û�����
����˵�������Ҳ��˵�������Ȱ�����䣬���̸ϻء�
�ڶ����賿��ĸ������ϴ�£���Ժˮ���ߣ�����Ѿ��ڴ�ˮæµ����ʱĸ���ˣ����Ҳ���ſޣ�ĸŮԩ����ˮ���߿���һ�š�
���ٹ������ѧУ�ϿΣ�ĸ��Ϊ����ʰ���û����ͼ�����������������������һ���������������Ͷ���Сѧ��ѧ�Ƚϳ٣����������ҵ���˼��棬ĸ��Ҳû�������Ҹ��Ŵ�������ֵ������ݣ��ڴ�˼�ס��һ���ڡ�
��һ�����䣬������´Ҵҳ��ţ��Ҳ���Ҫ��ȥ��˵�Ǵ�˼Һ��Ӷ���û��˭�����档�����˵�������䣬���Ϻܺڣ������Ҹ�����������ʧ������������һ����������Ҵ����ް��������ҵ��ֳ��˴�˼��š�
��˼ҽ�ͷת����һ���ֱ�̯�������ֱ����ø�ֽһ�������һҧ���飬�Ⱥ����ĸմӼ����������ֱ����ֺóԡ�ÿ�θ���㾭���Ǹ�̯�ӣ��Ҷ������ֱ��۾���ֱ���ܱ���������������ҳ��Ÿ����ߣ�ʵ����Ϊ�����
�������ҵ���ȥ���ֱ�̯�����˸������������Ȼ�����һش�˼ҡ���������Ҫ���㡣����������
��ֻ�ô����ҡ��������˺ó�һ��·��;��һ�����ã������˳ơ������á����ٴ�һ��С�����һ�����ӡ�
�������˾��ڷ��������ŮŮ��������������¡��ҿ������Ǹ�������һ�����ף���������һ�������ӣ���������һ�����������������£�������һ��С���ӳ��衣��Ȼ����һ�������ó����ӳ�����һ�������˴���Ⱥ�������������������еı������ߣ���˵�˺ܶ��������һ������ϣ�����Ŀ�ɿڴ���ԭ��������Ϸ���������ݣ��������������ŵ�Ϸ������������ı��ӡ����ǿ���Ϸ���ձ��������й����й���Ҫ�������գ�Ϸ�イ����������������С����������̫�����dz�Ϸȴ����ӡ���ر����ΪϷ�����ͷ���˲��ӣ����ñ��Ӵ������������촽��ճ����Ʋ�ٺ���ͻȻ���䣬һ�Կ����˶�ʱ��Ц�����ô�㳯�����¡�����Ϸ�������������ӵ������������ҳԾ����Ҽǵ����Ǵ��Сѧ��һ��ͬѧ���缸�����������ǼҼ��Σ������ʲô����������û�뵽��Ҳ���������������
���Ǵ�����ǵľ��磬������������Ϸ����������Ϸ�ﵱ���ݡ����������ܺ���������һ�����������������˾��ġ�����һ��һ�����ر�ÿ�������ɢ���Ź�ʡ�
�������ң���ȥ��ǧ���ܸ���ĸ�ף���˵��������μӾ��磬������ݿ���Ϸ����Ҫ˵����Ҳ�����ʲô����Ҫ˵��
����ð�ķ��������������˵��
��������Ϸ��������˵�������������ô��ȥ�������Dz���Ϊ����Ϸ����Ϊ�˻������ڿ��գ�����������ƥ�����𡣲��ܽ�ֻ����ĸ���ġ�
��������˿�����Ц��˵��С���۾����ģ�����������һ���ͻ���Ϸ������Ҳ������ɣ�����һ����ɫ���ԡ���㿪��Ц˵�����������ǼҰ��ó����ˡ���ʱ��ҹ���Ц����ͦ��û�뵽ת�۾ͳ��˴��¡������������ң������С�����������ھ���붮���������ݣ�ֹ��ס�˯����㿴�Ҳ�ͣ�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