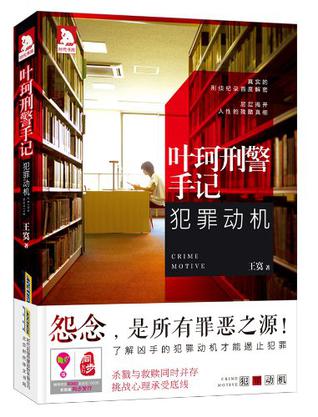�߾�����ּ�-��6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ǵ�����������60���������ñȱ߷�Ѳ��ͧ���죬�����������ݣ���ʹ�죡
�����߷������ٺٵس���ЦЦ��������˼�����ŵ��������ˡ�
������ǹ���ڣ����ǵ������Ӵ˳�Ϊ����ʮ�ﳤ����һ�ԡ���һ���ڽ�������ʮ����ľͷ����һ���ɢľ�ţ��ø��ӽ����������ġ��;⡱��һ�ֹ��ε����̣����ϣ���Ȼһ����ȫ�����˻�����
��������Ժ����Խ��Խ�ߵ�ľͷ��������֪��������֪��㲦��7000��Ԫ�������ͬ��ǰʣ�µ�3000��Ԫ��������10800Ԫ��������������֪����������֪���������ӱ߷�վ��¥�����һ��յ��ϣ���һ��200ƽ����ȫ��ˮ��ש�߽ṹ���·����ⴱ�·��������ϰ��ˣ�����֪��ʳ��Ҳ�������ӵĻ����ҡ��·�Ҫ����Ƴɹ������ٽ�һ��Ĵ�Ϊһ��������ܽ�ʮ�ﳤ��һ�����ࡣ
�����������ָ������������
����1976��9��9������4ʱ����̨������ë����ϯ�ڵ����賿0ʱ10���ڱ���������ج�ġ����������绹��֪�࣬�������ڼ���ı�ʹ֮�С�
���������ٿ�����������ġ��̳�ë��ϯ��־��ʦ��ᡱ��
������������ĵ������ҳ˹���Ŀ����������ӣ�������һ�־��˵��º��ѹ������úܶ࣬����ʲôҲ˵��������
����������֪��ѧϰС�����ᣬ�����ʣ���ë��ϯ�������й�����ɫ����
���������ʵ�̫��ˮ�����µ��¶��н�ɱ���������100�Ⱥ��������������������������ܿ������ģ��������ϵı����������������������������ܿ������ġ�
������˵��ʲô�DZ�ɫ�����·ֱ�Ҳ���ѣ�������Щ��ƫ���й�һ���ũ���֪��˭����˵�����أ�
������ϴϴ˯�ˡ�����Ҷ���ô���������Ȼ����Ϊ���ش�ѧϰС��ɢ�ˡ�
����ҹ���˾��������ڿ��ϣ�����������֪������˽��ᷢ��ʲô���ı仯��
���������↑��ʱ��һλ���Ա����ļ��߸����ң���ɽ��������Ժ֪�������Ļ㱨�ᣬǨ����ʱ����ĵ������ڼ����������������ѵ�������д���˻㱨���ϣ���˵�ڽ���11��Ҫ�ٿ�ȫ��֪ʶ������ɽ���繤�����顣�����Ѿ���8�µױ���ë��ϯ���������ˡ�
������ôƫƫ����ô�����أ�ʮ�����ë��ϯ������
����ȫ�й�һǧ����ʮ�������ѧ����һ���ֱ���˺���������һ���ֱ����֪�࣬��������Ѿ���ʮ���꣬����̸���ۼɼ���ҵ�������ؼ�ʱ�̣����ٵ�ȴ��������δ����Բ��������ì�����صľ��档����·�����������ȥ���Ѿ�����֪������⣬�����й���һ��������⡣
����Ȼ����ʱ���˵����ˣ����µ���ǧǧ�����������ش��֪�ࡣ
����ȫ��֪������黹���ٿ���˭���ó����õ�������˭����һǧ����֪������������
������Զ�붼�еı߾����ϣ���Ψһ�����ľ������ĵȴ��и������Ѷ������
�����������ġ�163����˪Ũ��
��������������������ʱ�䣺2015��7��5��19��20��57������������1961
1976�꣬��¶�չ�����˪�����ˡ�
�������³�˪�ľ���ˮ�������ڹཬ��ʵ�ڵ�ˮ����˪��֮���ֹͣ������������3��5�ɣ���������������
�������������й�����ĸߺ�����������˪��ֻ��80��120�죬��ˮ���İ�ȫ��������100��120�죬ƽ��ÿ�����굱�ؾͻ����һ������˪����ɵĵ����ֺ���
�����������磬����˵ҹ�����»ή��0�����£����Ѹ�������ע���˪��
������˵���������Ϸ粻�÷������챱�����˪�����������磬ҹ���磬���������ж��������Ǹ��������죬����ϰϰ���磬�������ҹ�ػή˪��
�����������ﶯԱ�����������������������ϸɲݣ�ȥ�����ˮ����Ѭ�̷�˪��
��������ˮ����ͷ�����Dz��������Ϸ�ͷ�ĵ����ԣ�ÿ��10����һ��СԲ�ӣ��ȰѴ����ĸɲ����ϣ�Ȼ��͵ظ�����÷��̵�����
�����賿1�����һ�����£�������Ѭ��һ���ȼ�ɲݣ����ϸո��»�մ��¶ˮ����ݡ���ʱ�䣬�¹���Ũ�̹�����˳���磬������Ұ��������ȫ����40��ˮ����ʮ��׳�ۡ�
������ȷ���������㶼��ȼ����������أ�ֻ����ˮ������Ա��ҹ�غ�����Ļ������̫������Ϊֹ��
����һ����˵�������ij�˪���¹�������һ��תů��ʱ�ڣ�ֻҪˮ��������һ�γ�˪���ͻ���תů���ڳ��죬�ȴ��ո��ˡ�
������˪��ҹ���������������������ˡ��������ֲ����Ҵ���������ǿ�����ڼ���Ϣ��ʮ�죬ֱ������ȫȬ����
������ͻȻ������������������ǰ�����ˣ�����������һ��Ҫ��������ң��ɻ�ʱ�����о�������˱ȱ��˶������������أ�һ���۵ĸо���û�У�ÿ�����Ͽ���ѧϰҲ�������档
�����������ڼ䣬�Һ����й�һ�����졣
�������첻֪��ô̸����һ���£�һЩ֪���������ű�ʾ������ũ�塢����ũ�塱�ľ��ġ��������ң������ŵ�֪���У�һ������**ǰ����ģ�������**�С�һƬ�족�����֪��һ���𣿡�
�����ұ����ʵ�һ����û�ش�����������һ�룬���ҿ϶���˵����������Щ��һ���ɣ���**��ǰ�Ƕ�Ա���ֳ�������ѧ����ҵ������ѧ�����磬��Ҫ���Ǵӷ�����ҵ����ġ���68��69����ѧ������û���κ�ѡ����ص�һ�ɡ���ũ��ȥ����ƶ����ũ���ٽ���������
����������70�죬����ӲҪ���������������Ž��һ������������˵������ʱ���Լ����á�һƬ�졯������������ѧУ��ѧũ��ѵһ����ֻ��һ�ֽ���;�������������������ٻ�ȥ��������뵽����ôһ���ӡ�������ũ���ˣ���
����ȷʵ������һ�������70��ͬѧ���䲻���ǡ�һƬ�족�����Ϻ�����ͳ���ũ�������ǵ������Ϻ���ѧУ��Ҫ��ָ�70����У���������·���ʱ������û�������������ֻ�����ε��ٻغ�������
�����Ҷ���˵������Ϊ�Լ������ٽ������þ��ܹ��������Ϻ����뷨̫�����ˡ�Ҳ�ѹ֣���ʱ���ʮ�����꣬����Ҳ��ʮ�����꣬��ʲô����
��������˵�����������ڣ��Ϻ��й������е���ʡ�����֪�����ȥ�ˣ�ֻ����Ӧ���ҵ����������ְȨ�ļҳ����п���Ϊ��Ů���ߺ��š��سǣ�������Щ������Ӧ���ٵ�֪����˱������Ľ��䡣��
������Ȱ��������ɧ̫ʢ�����ϣ����ﳤ�˷�����������֮���ٻ�����ɽ�����˶���һƬ�졯�ˣ��������ǵ����磬���ǵĵ��ó��˷����еġ�Ӳ�������������ˣ�Ҳδ���Ǽ����¡���
������֪���ҵ�Ȱ˵���ã�ֻ���뻺��һ�������е����ơ���Ҫ˵�ң����ڸ�����֯��֪���г��ֳ���ʧ���������������������Ҳ�е��������ġ�ֻ�м�����֪�࣬�������ܿɹ�������Լ�������ũ�塱�ı�̬������ؾ��Ķ�ҡ����ɽ�����˶����Ҷ�һЩ��֪�ࡰ�������ľ���ʮ�־��壬���Լ�����Ҳ����ũ�塰��������ȥ������ͬʱ����Ҳʮ������������֪���Ѿ����ٻ�����Ӧ���������������ˡ�
����Ҳ����һ���ɺϣ�
����10��5����ҹ23�㣬�ϼ�ͻȻ����߾����ϵ���װ������в�ҹ�����������ߣ����������ųǵľ��ű����ƣ����´�������Ȯ�͡�
�����ڶ��죬10��6�գ�ZG��������ˡ�***����
���������ҹ�����������߾����ϴ������ϼ������������װ������뵽�������У���ʱ������
��������ҹ��ӵ�֧��֧ίֵ�������ֵ��ҡ��Ѿ����°�ҹ�ˣ���ʱ��������ʮ�����װ���������ǹ�����¶�˯������ȥһ�ж�����ôƽ����
�����Ҹ���û���뵽��һҹ�й�����̳��ʼ�˷��츲�صı仯������Ϊ�Ƕ�������ʲô�쳣������ֵ�����ǰ��������������ǰץ���������һĻ��
�����������ġ�164��Χ������
��������������������ʱ�䣺2015��7��5��19��20��57������������1930
����1974���6��23�գ����ںں�ʦ��ѧϰ������ҵ��������ѧУͻȻ�����30����ͬѧ�������һ������ţ���������װ��������
��������װ���Ĵ�Ժ�ÿ������һ��ȫ�Զ���ǹ��20���ӵ������ϳ�ֱ�������ӵIJܼ��ʹ�����
����ѧУ��һ������Ա����Ա�������ų���ֱ����ʱ��������������������������ץ��������˵���ڸ���������ɳ̲�Ϸ����˸����µ�һ˫��ʽ��Ь�����������ǴӴ��Ͽ��շ�һ����ˮȻ��DZˮ�����ġ�
����ҹ��11�㣬���ǴӴ�������������о���30����أ��������ӡ����������������͡������Ӵ��·��С��ʱ��Ϊ��ɢ���ӣ����˵������̡���ʱ���Dzŷ�������һ���ġ�ө��桨���ж����ﳤ�������һ��������
������Сʱ��ǰ����鶯�ˣ��������Ҳ��������վ��������ǰ������һ����վ���ڴ�ڣ������ظ�������ÿһ���ˣ����������ˣ������ǵ�������һƬ��ͷ�������ţ���������ϵ���������ܼ�����һ�顣
��������ɽ��һƬ�߹���ͷ�Ĺ�ľ��ǰʱ������6��24���賿2��ࡣ̫����û���𣬵������������Ѿ��ҿ����硣���������п��Ըо���������������ܽ���
�����賿3�㣬���Ѵ������ϼ������������Ѳ���Ƭ��ľ�֡�
��������ѹ��ʵ����̤�������ظߵ�Ұ�ݺ�û���Ĺ�ľ��¶ˮ���������һ���������������ϣ���̣�ȫ�����´��ﵽ��ȫ��ʪ����Ь�ӵĽ�Ƥ����ϴ��Ư�ס�
����3��Сʱ������������һ��Сɽ��ǰ�����ǹ�ľ�ֵľ�ͷ��ʲôҲû���֣�ֻ�����˼�ֻ���ų����������ٴӹ�ľ��ԭ·���ء�
�������ư�̫����ס�ˣ��dz��䡣�������������ϵȴ��µ����
���������������·�����š���������ˮ����֪˭����������ȡů����Ҹɴ��ѵþ��������š���·���ˮ�����ڻ��Ϻ濾��һҹ�о������ֶ�������˯���ˡ�
���������ű�ǹ����Զ����ɽ���µĵ�·��ͬϸ��һ�㣬�ܿ�����ʱ·����Ѳ�߳��Ӻ�һ�Ӷӿ�ǹ����������������䶯��ư������ϡ�
����ͻȻ��һ��С�ͼ��ճ���������ǰͣ�£�����һ���������ꡢ�ֺ����ľ��ˡ���������������̧�žͳ����ڵ��ϵ��ų��������š��ų����ŵ�ѩ��ƨ������������������ֻƤЬ��ӡ��
�����ų���������������������˯�ۣ���ûŪ������ô���£�ֻ�����ּһ�������������Ϊʲô������ָ�ӵ�����Ϊʲô��ȥ������ϣ���
����Ȼ�������´�����һ���ų����������***�����Ǹ���Ա�����أ���
����ͻȻ����Ƴ���м�֧�����ݵ���ǹ�����ڵ��ϣ�ǹ���������·����������������ˣ������ܹ�ȥ���·�˦��ԶԶ�ģ�����ǹ�ӽ��˼��ճ��������ֵĶ����߳��˺��飬�۵ú������ֱ����˫�ֲ����������������***�����ǻ�Ҫǹ��Ҫ��ƨ�ɣ���
�������꣬��ת���ϳ���С����������ȥ��
�����ų���ƨ���ϵ�ЬӡҲû�������ϻ�ʪ�����Ŀ��ã�Թ��ʮ��ض�Զȥ�ļ��ս��ţ������ǰ�ǹ�����˰ɣ�***����
�������������Ҫ��������ɽ��һҹ���о����ټ��������ľ����ȫ��ʪ������·�ϣ�����ä���������۵��ڵ���ֱ����������ߺߡ��������������ֱ۰�ֵ���֦�������·����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