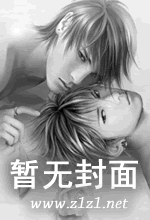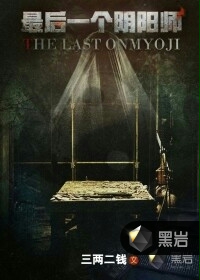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施韦泽是一个法文教师,家中藏有丰富的法文书籍。萨特自小没有同龄的玩伴,十分孤寂地生活在一个老人(外祖父)和两个女人(母亲和外祖母)中间。他的注意力很自然地转向外祖父的书房。
大约四、五岁,小萨特就开始翻看外祖父书房里的那些大部头书,先是看书中的那些插图,觉得十分有趣。翻得多了,安娜…玛丽发现儿子对书的兴趣,就将那些通俗易懂的文字念给他听。听着听着小萨特不满足依靠母亲的声音来了解这个词语的世界,他要自己来,在母亲的指导下他结结巴巴地拼读这些文字。
随着认识的字不断增多,他开始独自阅读,在词语的海洋里任意遨游。他发现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与自己实际上孤寂和单调的生活正好相反。于是他有更多的时间沉迷于书本之中,久而久之,书本对他而言成了真实的世界,而现实世界倒成了书的摹本,显得虚幻不实在。他在自传中说,作为一个孩子,他从没有爬上树掏过鸟窝,从没有在小河边拣过石头。而书本就是他的鸟蛋,就是他晶莹剔透的鹅卵石。
比开始读书稍晚一点,大约六、七岁,萨特开始写作。最初是信笔涂鸦,随便写画,后来开始改写自己看过的故事,再往后则自己编造一些东西。而文体是既有诗也有散文。在写作中他有一种强烈地占有词语的感觉。
他晚年回忆说:“很长时间以来──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看的──我往往把词语同事物混为一谈。我的意思是,桌子这个词就是桌子。我就是带着这种古典的想法开始了自己的写作活动,而且总是停留在这种阶段上。我总是认为,要使这个桌子成为我的,就要去发现作为桌子的词。这样,在词语和我之间就有一种亲密关系,但这是一种所属关系。在我对语言的关系中我曾是所有者,我现在还是所有者。”(《作家和他的语言》)他将词语、文字看成一个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些符号或象征;这些词语的存在甚至是可以触摸的。这一感受我们一般人很难体验到。
童年萨特这种将词语视为真实事物的感觉使他以后在写作具有十分独特的、别人无法模仿的风格。例如他的小说许多描写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在他的成名作《恶心》中,他写人的手,形容为“肥白如虫”,刻画人的脸,说是“如起伏不平的丘陵”,描写一棵树根,则将其说成是“一个黑色的精灵”。
萨特自我分析这种占有感,认为是一种移情的表现。他当时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儿童,但又一无所有。作为一个儿童,他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任何东西。从他跟外祖父一起生活时起,他就只是占有那给他的东西。于是他就处于一种难解的矛盾之中:就一般的占有而言,他也可以说是富足的,就是说,他有一切东西而不知道缺乏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又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占有过任何东西。他不缺什么,但任何东西都不是他的。在现实中无法占有,那么就在想象中实现,于是就发生了这种占有词语的移情现象。他是以占有者的身份来投放词语;对他来说,词语一开始是一种占有的工具,只是到后来,它才成为集体交流的手段。萨特最后总结说:“这对我曾是最重要的事情。语言是属于我的某物,一半是被表示的事物,一半是外在于它们的表示者。‘桌子’这个词一半在桌子中,一半在我的智谋的工具性的延伸中。” (《作家和他的语言》)
萨特分析自己如此痴迷于文学和写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把文学当成了自己的上帝,在写作中倾注了自己的宗教情结。家中几个人宗教信仰各别:外祖父是新教徒,外祖母是天主教徒,母亲不信仰任何教派的宗教,只是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宗教情感。外祖父和外祖母常常在餐桌上拿对方的宗教信仰开玩笑,虽然不含什么恶意,在不经意间让小萨特觉得,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是没有价值的。尽管大人们一致决定让萨特上教堂和领圣餐,但宗教在他心中已经失去了分量,他实际上缺乏信仰。没有信仰,就会有对死亡的恐惧。为了摆脱这个,他把对于不朽的渴望倾注到写作之中。他所想象的文学生活实际上是以宗教生活为榜样,他唯一的梦想是通过文学、写作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除了这两个原因,萨特终生以文学为业,还有一个十分偶然的因素:他对外祖父意思的误解。
小萨特的写作活动获得母亲的赞赏和鼓励,她常常将儿子的作品念给大家听,而大人们也都称赞不已。但看到外孙越来越痴迷于写作活动,外祖父开始担心起来。在他看来,当一个专业作家是没有出路的,作家中有不少穷困潦倒终其一生的例子。他不希望小外孙走这一条路。由于他一向不强迫萨特做什么,这次也不打算断然反对外孙的意向,于是采取一种委婉迂回的劝诱方法来打消外孙的念头。
一天晚上,施韦泽将女人们赶出室外,说是要跟萨特进行一场男子汉之间的谈话。他把外孙抱在膝上,十分严肃认真地同他谈了一席话,大意是:他萨特要从事文学写作,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本来是很不错的事情;但作家是一个生活没有保障的职业,不少著名作家挨饿而死,或者为了糊口而出卖灵魂。为了顺利从事文学写作,他应该另有一个职业,这就是当一个大学文学教师。教书有稳定的收入,还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相辅相成,他完全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
外祖父说这番话可谓用心良苦。他的本意是,萨特听到作家困苦不堪的境况后会知难而退,慢慢打消当一个作家的念头。然而萨特完全错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要自己坚持走作家的道路,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另外兼顾一个第二职业。
外祖父这样严肃认真地同自己谈话,对萨特来说是第一次。以前他俩在一起时总是闹着好玩,他从来没有把外祖父的话当真。如果这次外祖父还是跟以前一样,在说说笑笑当中谈及此事,他肯定不会当一回事。但这次谈话跟以前完全不同,萨特不禁想起平素外祖父对其子女(包括安娜…玛丽)的严厉命令,那是不得不服从的。因此,他必须当一个作家,这既是他自己的意愿,也是外祖父的命令。
年近60岁时,萨特在自传中回忆说,正是由于他把外祖父的“反话”正听,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写作写累了想歇下来,外祖父的话就立即在他头脑里响起,催促着他回到书桌旁继续奋笔疾书。到现在回顾此事,特别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不禁想到,自己花费一生心力、夜以继日地埋头写作,花费了那么多笔墨纸张,抛出了那么多写出的书,其实并没有任何人请他来写,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早已去世的老人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却是被完全误解的,不禁让人啼笑皆非,深感人生之荒诞。
除了立志当一个作家,这种童年的过度阅读还对萨特成年后的一些生活习惯产生影响。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长年沉迷于书本,小萨特已经通过图画和文字,在世界各地漫游了一番。很有意思的是,他读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看来萨特很早就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遨游了。当然,他实际来到中国,是在四、五十年以后。成年后的萨特,除了写作,唯一的爱好是旅行。这跟他童年的阅读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童年的阅读习惯还影响到他旅行的方式。一般旅游者每到一地,大都是直接奔向该地著名的自然景观,逐一游览,惟恐漏掉什么。萨特则不同,他对自然景观并不特别感兴趣,想必是早在书本上看过了。更多的时间他是坐在该地一个广场上,默默地抽着烟斗,看着人们来来往往,在心中体会着这里的人文氛围。
我们甚至可以从他成年后的日常生活习惯中看到童年受到的人文熏陶的影响。例如,他不喜欢吃那些生的东西或呈现自然状态的东西,如水果和血红色的牛排。他在日本访问时出于礼貌,勉强吞下主人敬献的生鱼片,回到旅馆就全吐了。他喜欢吃的都是经过人们加工的食物,如水果罐头,如香肠。凡是跟人有关系的东西,他都能够适应,而那种纯粹的自然,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童年(1905…1917):占有词语(2)
阅读和写作激发了萨特的想象力,使他在孤寂的生活中获得安慰和自信心。童年生活中,还有一个东西同样起到激发想象力的作用,同样给了他精神抚慰,这就是音乐。
外祖父家可以说是一个音乐世家。外祖父会作曲,创作的乐曲带有门德尔松的风格,他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母亲安娜…玛丽同样钢琴弹得好,她能演奏肖邦、舒曼等人的难度极大的乐曲。此外她还有一副好嗓子,而且经过专门训练,唱出的歌真可以说是宛转动听,余音绕梁。外祖母、舅舅、舅妈、表兄弟们,人人在音乐方面都有一手。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萨特自然而然地喜好上了音乐。他很小的时候就随着母亲去体会音乐之声。往往是在晚饭后,母亲开始弹奏钢琴,小萨特站在一旁,随着钢琴的节奏和旋律,陷入丰富的想象之中,以前看的那些爱情和战争故事浮现在脑海里,他自己成了主人公,成了救美和杀敌的英雄。想象到得意处,他情不自禁地抓起外祖父用的尺子和裁纸刀,把它们当成剑和匕首挥动起来。这时他充分感受到自己的强大和无所不能。
大约10岁左右,萨特开始练习弹钢琴,并且是上正规的钢琴课。到后来,他已经能够弹一些难度较大的曲子了。当他弹到一定水平时,母亲和他一起弹,两人合奏,这应该是萨特一天最快乐的时光。这种对音乐的爱好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萨特的想象能力和文化鉴赏能力,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是很有好处的。在他的成名作《恶心》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情节:主人公洛根丁在听一张唱片,那是一个黑女人在唱:“在这些日子里,亲爱的,你会想念我。”这应该是萨特自己对于音乐喜好的写照。萨特经常参加音乐会,他弹奏钢琴的爱好保持终生,直到晚年双目失明、胳臂也抬不起来才被迫放弃。而在那时,听自己喜爱的唱片是他最大的慰藉。他家中藏有许多名曲唱片。
萨特在将近70岁时,回忆童年的生活,特别提到自己对于月亮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觉得月亮是自己的月亮,他同月亮之间有一种默契。当他抬头遥看那一轮皎洁的玉盘时,总是不自觉地同她对起话来,向她任意倾诉自己心中的一切,虽然是默默无语的。
这里他仍然发挥着在阅读和音乐里面已经体现出来的想象力。当看到月亮上面依稀可见的明暗起伏之处时,他将那幻化为一张微笑的脸,一张只向他展示秘密的脸,一张让他倍感亲切的脸。童年萨特害怕黑暗,而月亮让他战胜恐惧,消除了黑暗的阴影。
这种月亮情结应该来自他的孤寂感以及力求摆脱这种孤寂感的需要。童年的体验在他成年后仍然有着影响。许多年后,他写了一篇小说,名为《午夜的太阳》:一个小女孩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