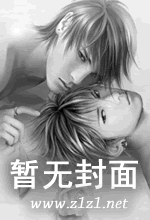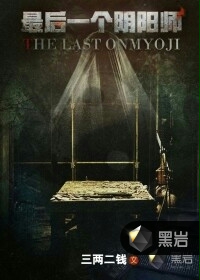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第4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个奖有什么意义?真正可以说他们在把它给某一个作家的那一年他就比他的同事、比其他作家更优秀,而在这之后的一年又有某人更优秀吗?人们真正有必要这样来看待文学吗?好像那些在一年或很长时间都是优秀的人们只有在这个特别的一年才能被承认是优秀的,这合理吗?应该说这是荒谬的。显然,一个作家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对其余的人来说是最优秀的。他最多只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而“最好的人”的说法表达得不好——应该说他是那些真正写了好书的人中的一个,而他跟他们是平等的。他可能是5年前、10年前写了这些书。
最后萨特将话题回到他自己身上:“我发表了《词语》,他们认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给了我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这就给了我的作品一种新的价值。但人们本该在一年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在我还没有发表这本书时,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我非常喜欢海明威,我个人也认识他,我在古巴同他见过面。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萨特反对等级制的思想基础是他对天才与平等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那种天才超人的思想同平等的思想并不矛盾,因为天才和超人只是充分表现了作为人的实在的存在,而根据地位和等级制度来分划分自己等级的人们只是一种未加工的材料,其中可能找到后来出现自由突变的超人。但这种未加工的材料毕竟不是由超人构成,而是由低能者组成,它是符合于那套不是面向人本身而是面向其属性──面向铁路巡警、出版检查官、教师等等──的等级制度的,总之,是职业、行为、他们用心包装自身的物体,即那些易受等级影响的东西。但如果一个人达到相当深度,等级就不可能了。萨特说,这是他为自己逐渐搞清楚的东西。
关于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天才,萨特说,“我只是在一闪念的直觉中才感受到我的天才;其余的时间它只是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在我这里,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我从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天才的作品。虽然它们都是按照我对天才作品的理解和要求去写的。我不轻视自己的作品。它们代表着某个重要的东西。而作为一个天才我有权嘲笑这些作品,拿它们取笑,虽然同时它们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天才不被承认,他不应该让自己绝望。”
萨特指出,关于天才思想的难点在于,在不同的智力之中有一种同等的东西。这就是说,一个作品可能被称为佳作,因为它的作者适合于写这类作品,他具有一定的专门技巧,但并不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别人不具有的性质。最后萨特说:“我想,我可能比另一个人更加有天资一些,智力较发达一点。但从根本上看,我的智力、感受力和别人是相同的。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优越性。我的优越性就是我的书,当然这是就它们是好书来说的,但另一个人也有他的优越性──这可能是冬天在咖啡店门口卖的一包热栗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优越性。就我而言,我选择了这一个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养女阿莱特(1)
在爱情关系方面,这一时期有一个女子进入萨特生活,她开始是萨特的情人,后来成为他的养女。1956年3月,一个叫阿莱特•;艾卡姆的阿尔及利亚籍姑娘给萨特写了一封信。她19岁,是犹太人,在卡涅的凡尔赛公立学校读书。当时她正在准备一篇论文,打算通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她读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信中,一方面,她就论文的有关问题向萨特请教,就萨特哲学中的有关问题请萨特解答;另一方面,这时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打得火热,她作为一个生活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感到十分苦恼,不知何以自处,于是也在信中抒发自己的苦闷。萨特回了信,让她寄论文来。以后他们不断有书信来往。然后顺理成章地是两人见面。然后阿莱特成了萨特的情人,他的最年轻的情人。
1958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刺激,也由于从事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写作的过度紧张和疲劳,萨特一度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除了波伏瓦的照护外,阿莱特也给了他许多抚慰。萨特和阿莱特曾一起去威尼斯度假。在那里,萨特写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最后一幕的初稿。萨特将剧本的内容读给阿莱特听,特别是主人公弗朗兹的演讲,让她提意见。阿莱特说,弗朗兹的讲话有些夸张和做作,但萨特的表演倒十分精彩。
要了解萨特与阿莱特的关系,他俩的通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资料。但萨特去世后,阿莱特并未出版他俩的通信集。不仅如此,当波伏瓦出版萨特的书信集(主要是萨特给她的信)时,阿莱特还特别要求波伏瓦,将萨特信中有关她的内容悉数删去,以至于波伏瓦在该书序言中特别声明:“为了不让第三者──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感到困窘或难堪,我删去了一些段落,改变了一些人的姓名。这些改变全都是由我一人作出的。有些地方是应艾卡姆─萨特女士的要求而改变的。”因此我们对萨特和阿莱特的关系很难有详细具体的了解。但阿莱特的这种要求从另一方面表明,她和萨特的关系一定有不少不希望为外人所知的亲密。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阿莱特在萨特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除了其他因素外,阿莱特有音乐特长是一个重要原因。音乐在萨特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弹钢琴,这一爱好撒特保持到晚年,直到他的胳臂因病不能活动才罢手。
从有关资料看,波伏瓦也能够弹一点钢琴,但水平不高,因此不能经常与萨特一起合奏。她和萨特经常进行的音乐活动是在一起听唱片。而阿莱特能够弹一手好钢琴,还吹得一口好笛子,歌也唱得不错。因此,萨特很喜欢坐在钢琴旁为她伴奏,或者同她进行二重奏和二重唱。在从事这样的活动时,应该是萨特一天最为放松的时候,也是心情最为舒畅的时候。大概其他的女性都不能取代阿莱特在萨特生活中的这种作用。
1965年1月底,萨特正式申请收养阿莱特为自己的养女。这一年3月,这个申请得到批准。此时距萨特和阿莱特认识正好9年。这一年萨特60岁。
萨特收养阿莱特为女儿,直接目的是为了改变她恶劣的精神状态和不利的社会生活状况。阿莱特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是悲惨和不幸的,因此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佳,长期处于忧郁状态。而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籍犹太人,在法国是倍受歧视的。萨特对于自己喜爱的女性,愿意奉献出一切。他很想帮助她改变精神状况,帮助她抹去过去的阴影,希望她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希望她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最根本的,是希望她有自信心。此前萨特交往的女性,例如月亮女人和万达,最根本的问题是对自己、对生活缺乏自信。萨特也试图帮助她们改变,但她们年纪大了,很难改变。而阿莱特还很年轻,还有较大的可塑性,萨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她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据我猜测,为了改变阿莱特的地位和状况,也许萨特曾经想过同她结婚。以前他在帮助波伏瓦和万达时都想到这一招,这也是他能够为喜爱的女性拿出来的最后一份礼物。但他比阿莱特大32岁,再同她结婚显然不适合;而且这还涉及到同其他女性的关系,特别是同波伏瓦的关系。于是他决定收养她为女儿,实际上,就他的年龄来说,显然,作她的父亲是足够了的。这样一来,阿莱特就自然地加入了法国籍,成了一个法国人,在法国生活不会再受歧视。作为萨特的养女,她也有了新的身分,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在财产方面都有了安全和保障。而且这里还有一种亲情关系,一种家庭气氛,这些对于改变阿莱特的精神状态都是有好处的。
至于这一行动的内在因素,则较为复杂。萨特去世后,阿莱特在出版他的《奇怪战争日记》和《伦理学笔记》两本书时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萨特收养她的问题。她说,萨特收养她是为了帮助她。她还说,他俩的这层关系中有些游戏的成分,因为她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而过去也无法抹杀掉。那么,这种“游戏成分”是什么呢?
由于萨特从小没有父亲,又由于母亲再婚的影响、对继父的反感,萨特不喜欢父子关系,认为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关系。他既不想被人强制,又不想强制于人,因此他不愿意结婚,当然更不愿意有孩子。但是,他对于这种人伦关系还是感到好奇。他在伦理学笔记中对这种关系作了探讨。而收养一个女儿可以满足他的这种好奇心,作为实际上没有子女的一种补偿,当然,这是象征性的,或者如阿莱特所说,是带有游戏成分。
实际上她是他的情人,而在名分上她是她的女儿。这里似乎有一种乱伦的关系。而萨特确实有一种乱伦意识。在自传《词语》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大约10岁时,我读了一本名为《横渡大西洋的客轮》的书,十分着迷。书中有一美国小男孩和他的妹妹,两人天真烂漫,彼此无猜。我总是把自己想象为这男孩,由此爱上小女孩贝蒂。很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写一篇小说,写两个因迷路而平静地过着乱伦生活的孩子。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不难发现这种梦想的痕迹:《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与厄勒克特拉,《自由之路》中的波里斯与伊维什,《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的弗朗兹与莱妮。只是最后这一对才有实际的行动。这种家庭关系吸引我的,与其说是爱的诱惑,不如说是对做爱的禁忌;火与冰混杂,享乐与受挫并存,我喜欢乱伦,只要它包含着柏拉图式的成分。”萨特所想象的“柏拉图式的乱伦”,在他与养女阿莱特的关系中得到实现。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养女阿莱特(2)
在这一收养行动中,还包含着一种因素,即萨特的“犹太人情结”。多年来萨特一直将犹太人问题当作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萨特对于犹太人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他觉得,“二战”期间,纳粹迫害和灭绝犹太人,他作为一个非犹太的欧洲人,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未能制止这种罪行。那么,将阿莱特收养为女儿,也许就含有这种赎罪意识。
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想来,萨特收养阿莱特之后,他俩之间情人关系的成分可能会逐渐减弱,而他对她的类似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可能会逐渐增强。其实萨特对这种感情应该不完全陌生。当年萨特对万达就存有这种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