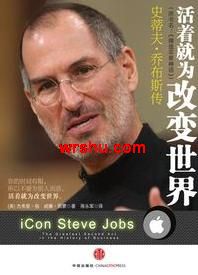学习改变命运-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邱吉尔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你想要其他人具有怎样的优点,你就要如何的去赞美他。”
反之,对于别人的缺点,你也应该学会用更加委婉的方式指出,使之听起来更像是赞美而不是直接的批评。
在你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也应该这样,以鼓励代替批评,以赞美来启迪他人内在的动力,使其自觉的克服缺点、弥补不足。渐渐的,你就会发现,这种办法比你去责怪、去埋怨有效的多。这样将会让你拥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创造出一种和谐的气氛,从而给学习和生活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
第五部分“作揖主义”(1)
不明智的争论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你要知道,当一个人辩论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单纯的用理智分析问题,他所有的人格尊严都已经行动起来,要求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事后他也许会觉得自己错了,但是他必须考虑到宝贵的自尊心而坚持说下去。
刘半农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左派作家,《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曾写过一篇叫《“作揖主义”》的文章,其间为人处世的思想至今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 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相象,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靶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切。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第五部分“作揖主义”(2)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时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欢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觉!”
所谓“作揖主义”,不是不坚持真理,不是当滥好人,而是不把时间花在与人无用的争论上,全心全意做自己的事情,用事实来说话。《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是这个道理。
《庄子·齐物论》提出“辩”的反命题,认为“辩无胜”——靠辩论获得的胜利没有意义:“即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大意:我和你辩论,你胜了,我输了,我说的就一定错误吗?我赢了,你输了,我说的就一定正确吗?其实无论辩论结果如何,我俩谁对谁错,或者都是对的,或者都是错的,仍然无法断定。)
不明智的争论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你要知道,当一个人辩论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单纯的用理智分析问题,他所有的人格尊严都已经行动起来,要求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事后他也许会觉得自己错了,但是他必须考虑到宝贵的自尊心而坚持说下去。美国心理学家奥佛斯屈在他的《影响人类的行为》一书中说:“当一个人说‘不’,而本意也确实否定的话,他所表现的决不是简单的一个字。他身体的整个组织——内分泌、神经、肌肉——全部凝聚成一种抗拒的状态,通常可以看出身体产生一种收缩或准备收缩的状态。总之,整个神经和肌肉系统形成了一种抗拒接受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要让他冷静的分析问题并放弃自己的观点,简直难于登天。本来除了辩论,你还有其它方法可以证明你正确的,但现在,他把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维护自己的尊严等同起来,恐怕再好的方法也要归于无效了。
所以,如果你是正确的,事情的发展自然会证明你的看法,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也会慢慢改变态度。而一旦辩论,往往会使人将坚持自己的看法视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即使事实证明你是对的,他仍然不会服气,会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护,不仅不会信服你,反而有可能产生敌意。也许有那么一种人,天生杠头,即使用事实来说话他仍然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既然客观事实都无助于改变他的看法,口头的争论又如何能够呢?徒然增加别人对你的反感而已。
第五部分“作揖主义”(3)
近现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著名的大争论,比如洋务派与顽固派,保守派与立宪派、革命派与保皇派、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等,对于解放思想、推动历史发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例子能否反驳我前面的观点呢?我觉得,首先,总的来说,即使这样的辩论,也没有哪一方让另外一方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李鸿章洋务运动失败了,但他至死都反对君主立宪;康有为辩论不过革命派,但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他还是保皇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