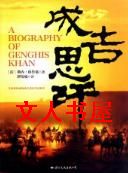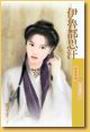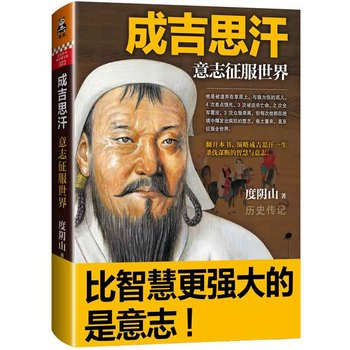成吉思汗-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12世纪末,克列亦惕人的汗已是父子相传的景教徒。这就是马可。波罗所叙述的〃祭司王约翰〃传说的来历,尽管后来有人曾武断地说〃祭司王约翰〃是指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皇帝。不管怎么说,克列亦惕人信仰的景教在成吉思汗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读者将会从本书后面的叙述中看到,基督教后来成了成吉思汗家族帝国的正式宗教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说克列亦惕人有统治整个蒙古的野心,这也是从历史资料中得出来的结论。大家知道,在成吉思汗时代到来以前的两代人时,克列亦惕部的汗曾进攻居住在戈壁滩东部的塔塔儿人。前面已经说过,北京的金王是支持塔塔儿人的。同塔塔儿人作战的那个克列亦惕部汗名叫马尔忽思一不亦鲁黑。这个名字的前半部是基督教徒名马克的变化形式(从本书后文可以看出,〃马尔忽思〃这个名字是当时北亚地区景教徒普遍采用的名字)。当时,马尔忽思一不亦鲁黑汗被塔塔儿人俘获并被押送交给了金国。金人像刑毙蒙古部首领一样(本书前文已经叙述过金人刑毙蒙古俺巴孩汗等人的情形)处死了马尔忽思一不亦鲁黑汗,即把他钉在木驴背上,使之辗转惨死。他的遗孀美丽的忽图黑台一依里克赤决心为他报仇雪恨。她假装豁达大度,不记丈夫被害之仇,带着一百个鼓鼓囊囊的羊皮袋,诡称羊皮袋里装满了牧民特别喜欢喝的发酵马奶酒,以此作为礼物,前去向塔塔儿部首领致意。实际上,每个羊皮袋里都藏着一名武士。塔塔儿部首领信以为真,立即设宴为客人接风。于是宾主人席,觥筹交错,互致祝愿。当宴会进行到一半之时,忽图黑台一依里克赤一声暗号,藏身于羊皮袋里的一百名武士瞬时一齐破袋而出,闪电般冲上去,手起刀落,塔塔儿部首领及其众从人,顿时血溅毡包,做了刀下之鬼。这真是蒙古式的《一千零一夜》之一夜。
马尔忽思留下了两个儿子,一名忽儿札忽思(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基督教徒名西里亚克的变形),一名菊儿汗。菊儿汗之后,接替汗位的是忽儿札忽思。忽儿札忽思的统治也很不稳,充满了风波和风险。他曾几乎被塔塔儿人推翻,幸亏西边的邻居乃蛮部出面援助,他才保注了汗位。他的长子脱斡邻勒是本书中的重要人物。脱斡邻勒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祭司王约翰〃,是成吉思汗一生开始时期的保护人。实际上,应当承认,这位北亚景教的代表人物为夺取汗位而采取的手段根本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父亲刚一去世,他就杀死了可能与他争夺汗位的两个弟弟塔亦一帖木儿泰赤和不花一帖本儿。杀了两个弟弟还嫌不够,他还想杀他的另一个弟弟额儿客…哈刺。额儿客一哈刺等设法逃人了乃蛮部。
至此,我们第二次提到了乃蛮部。本书后面将进一步谈乃蛮部的情况。乃蛮部居住在蒙古西部杭爱山以西,即科布多湖泊地区,阿尔泰山(蒙古境内部分),额尔齐斯河河谷和叶密立河河谷塔尔巴哈台地区。乃蛮汗亦难赤必勒格骁勇过人,正像当时有人所说,他生平临阵,只向前进,从不马尾向敌人。当时,他收容了前来投奔的脱斡邻勒之诸弟。同时,他还支持脱斡邻勒的叔叔菊儿汗反对脱斡邻勒。菊儿汗率众起义,把脱斡邻勒赶下台,迫使脱斡邻勒带着一百来个亲信逃到了色楞格河流域的哈刺温山谷。色楞格河流域是蒙古森林狩猎部落蔑儿乞惕部的地盘。为了换取蔑儿乞惕部的支持,脱斡邻勒将爱女忽札兀儿嫁给了蔑儿乞惕部首领脱黑脱阿。然而,此举似乎并没有换来蔑儿乞惕部的任何实际的支持。
脱斡邻勒在走投无路中想出了最后一着棋:去找也速该把阿秃儿,请求也速该把阿秃儿支持他。主意已定,他就来到也速该把阿秃儿跟前:〃请助吾一臂之力,帮吾从吾叔菊儿汗手中夺回吾之臣民。〃〃汝既如此恳切地求助于吾,〃也速该把阿秃儿慷慨地说,〃吾即同泰亦赤兀惕之二勇士忽难和巴合只前往,替汝夺回汝之臣民罢了!〃
也速该把阿秃儿说话算数,当即集合部队驰往忽儿班一帖勒速特,攻人菊儿汗大营。菊儿汗不防有此奇袭,只好慌忙上马逃人唐兀惕部辖区(今中国甘肃省境内)。
由于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干预,脱斡邻勒重新登上了克列亦惕部汗位宝座。两人在土拉河黑林发誓,彼此永远友好。
〃吾当永远铭记汝之助力。吾之谢忱将施及汝之子子孙孙,皇天后土作证。〃脱斡邻勒赌咒发誓说。
这是庄严的诺言,它使脱斡邻勒和也速该结成了兄弟,也确立了也速该之子的保护人。
在成吉思汗创业的整个第一阶段(直至1203年)中,这一〃黑林誓言〃一直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章 也速该之夺取诃额仑夫人
古代蒙古诗人描写了勇士也速该同一个后来成为成吉思汗生母的妇女结合的过程。诗人在描述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语言是非常尖刻的。在描给当时蒙古风俗的粗鲁特点方面,那些诗句简直是入木三分,胜过所有其他的有关插曲。
一天,也速该把阿秃儿在斡难河畔鹰猎为乐。忽然,他看见蔑儿乞惕部的也容赤列都骑着马而来。原来,也客赤列都刚刚从斡勒忽淑兀惕部娶妻回来,路过此地。斡勒忽油兀惕部是属于游牧于(蒙古东部)哈拉哈河注入捕鱼儿湖之河口地区的翁吉刺惕部的一个氏族。也客赤列都娶来的女子名叫诃额仑。河额仑夫人这个名字将在本书后文中屡次出现。这时,这一对年轻夫妇兴高采烈地从这里经过,恰恰被也速该一眼看见,这对于新郎来说太不幸了。也速该的确目力不凡,他一眼就看出这位少妇是罕有的丽妹。他马上翻身跑回家,叫来了他的哥哥捏坤太石和弟弟答里台斡惕赤斤。看到这三条大汉如狼似虎地扑来,也客赤列都不禁心里一阵发慌,急忙拨马(据蒙古诗人说他骑的是一匹栗色战马)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驰去。也速该兄弟三人也催马紧紧追来。围着小山跑了一圈后,也客赤列都又来到他妻子乘坐的车前。诃额仑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女人,她非常明智地对丈夫说:'校见彼三人之面色乎?吾观彼三人颜色,好生不善,似有害汝性命之意。汝若相信吾,可快逃性命。但得保住性命,何愁再娶不着好女美妇?……若再娶得妻室,可以吾名河额仑名之,算汝未能忘吾。快逃性命!离开此地!带去此物,以使汝记起吾时,可闻见吾之气息……〃
诃额仑说毕,即脱下一件衣衫,扔给新郎,也容赤列都急忙下马,接住新娘扔来的衣衫。这时,也速该三人也绕山跟踪而来,眼看就要来到车前。也客赤列都急忙上马,快马加鞭,一阵风似地沿斡难河河谷逃去了。也速该三人一看,也打马直追,但追过了七道岭,也没有追上也容赤列都,只好掉转马头,驰回诃额仑车前。也速该得了诃额仑夫人,得意洋洋地带着她返回自家蒙古包。蒙古诗人描给说,也速该当时因夺得这样的〃战利品〃而乐不可支,亲自给诃额仑赶车。其兄捏坤太石策马扬鞭导于前,其弟答里台斡惕赤斤傍辕而行护于侧。此时,可怜的诃额仑则在车中边哭边说:〃我夫赤列都,未曾逆风吹,不曾野地受饥寒也!如今却如何!彼在奔逃中,其双练椎迎风而动,忽而搭启后,忽而技胸前,爬山过岭,何等艰难。被何至落得如此惨境焉!〃据蒙古诗人说,当时河额仑的哭诉,使斡难河河水荡起怒涛,使森林随之呜咽。但是,傍辕而行的也速该之弟答里台斡惕赤斤则一边行一边酸溜溜地对车内的诃额仑说:〃汝欲搂于怀中者已越岭多矣,汝所哭者已涉水去矣,虽呼彼亦不回顾汝矣,汝虽寻踪往追亦不得其路矣,汝其止泣也矣。〃答里台斡惕赤斤就这样以挖苦的口吻劝着诃额仑,劝她忍耐顺从,认可眼前的事变。就这样,诃额仑跟着也速该来到了也速该的蒙古包。她明智地顺应了这一变化,从此全心全意地侍奉着也速该。
这一著名的插曲可以告诉我们许多情况。首先,它告诉我们,在当时的蒙古人中,异族通婚是组成家庭的准则。这一准则迫使人们为得到妻室而大肆抢掠妇女,而掳掠妇女又常常导致各部落之间以兵戎相见。读者从本书后文就会了解到,蔑儿乞惕人和居住在斡难河上游的蒙古人就经常掳掠对方的妇女,这种掳掠对方妇女的行动导致这两个部落之间彼此仇恨,而且这种仇恨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久而久之则又进一步导致一方吃掉另一方。其次,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蒙古第一个王国的覆灭在各部落之间引起了多么严重的混乱,上述抢掠妇女的情景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混乱已经超出了政治范畴,进而搅乱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因为,读者从本书后文就可以看出,当蒙古确定了成吉思汗家族的秩序时,蒙古男人就可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而不必通过掳掠妇女的手段实践异族通婚制,从而在本部落以外求得妻室。
最后,蒙古的传说向我们展现的上述如此生动的掳掠妇女的情景从一开始就充分显示了诃额仑夫人的性格。她当然是一个尽职的贤妻,她爱她的前夫,甚至可以说十分钟情于前夫。当也客赤列都从她的眼前逃走因而她再也看不见了的时候,她那动人心魄的伤心哭诉,以及两人临别时她主动给前夫留下纪念物的举动,都充分证明她是十分钟爱也客赤列都的。但是,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妇女,她善于坦率地认可无可挽回的事变。她满怀柔肠地安慰丈夫勿为失去她而忧伤,劝丈夫赶快逃命。而一旦进入也速该家,她又以同样直率的忠诚专一爱着也速该,而且,后来,当不幸降临也速该去世之后,她又坚强地承担起了主持这个家庭的重担。如果没有一个如此坦率正直的母亲,一个如此有魄力、具有务实精神的母亲,成吉思汗能否成就那样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恐怕是一个无人能回答的问题。
第三章 成吉思汗的童年
据佩里奥特在1939年进行的研究,也速该和河额仑夫人的长子、后来的成吉思汗,诞生于公元1167年(猪年)。当时,他家居住在斡难河右岸迭里温孛勒答合(〃李勒答合〃是孤山之意)上。婴儿初出母胎时,右手紧握着一血块大如石。在诃额仑临产前夕,也速该在一次对塔塔儿人的战斗中俘获了塔塔儿部的一名头目,这个头目名叫铁木真兀格。为了纪念这一战功,也这该就给儿子取名铁木真。从这一名字的词源来说,突厥一蒙古文词根〃铁木儿〃是〃铁〃的意思,以此来把〃铁木真〃解释成〃铁匠〃之意,从发音上来说是正确的。这偶然的巧合表明,此人后来之成为〃世界征服者〃要归功于其父母早已确定他将成为铁人,从而使他后来承担起了锻造一个新亚洲的使命。也速该把阿秃儿和诃额仑夫人继生下铁木真以后,又生了三个儿子,他们是:拙赤合撒儿、合赤温、帖木格。〃帖木格〃这个名字的字面含义是〃家庭王子〃,即幼子之意。此外,也速该夫妇还生有一女,名日帖木仑。也速该同其别妻速赤吉勒(据佩里奥特在1941年所作的考证,也速该的另一个妻子可能名为速赤吉勒)生有二子,一日别克帖儿,一日别勒古台。
关于成吉思汗的体格相貌特征,编年史作者们没有作足够的记载。他们只指出,成吉思汗幼时〃目中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