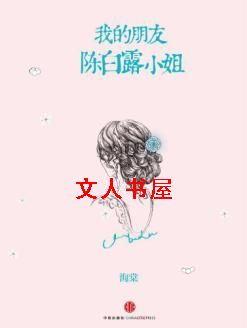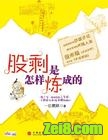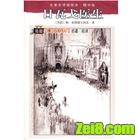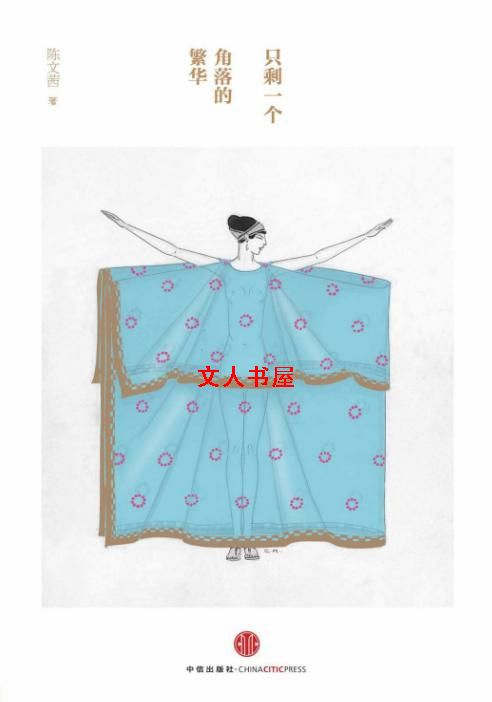作者:余华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旧约·创世记》第一天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我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昨夜响了一宵倒塌的声音,轰然声连接着轰然声,仿佛一幢一幢房屋疲惫不堪之后躺下了。我在持续的轰然声里似睡非睡,天亮后打开屋门时轰然声突然消失,我开门的动作似乎是关上轰然声的开关。随后看到门上贴着这张通知我去殡仪馆火化的纸条,上面的字在雾中湿润模糊,还有两张纸条是十多天前贴上去的,通知我去缴纳电费和水费。...
作者:一扔就涨各位菜鸟股友们,本人也是一大菜鸟,而且是运气极背的菜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这么背,反正自从买股票以来就没赚到过钱,即便是这轮十年一遇的超级大牛市。我只要买入股票后,三天内必跌至套牢。熬啊熬啊,终于熬到解套,满怀欣喜地抛出股票,享受解套的快乐不到两天,被我抛弃的股票就报复似的开始疯涨。然后我又陷入新的一轮循环。看看我的辉煌战绩吧,先是2006年年初于1.9元扔掉了青鸟天桥(600657),不料在出掉的一周后开始狂涨,一直涨到4元多然后10送11,再次填权。受此重大打击,我奄奄一息,痛苦了两个月,终于选择了万杰高科(600223)。2.5元抱了大半年,一直抱到过年前,实在受不了他的乌龟脾气。可是一出手,又立马涨了60%。眼睁睁地看着2006年所有人都赚得流油,可我却只赚点利息,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啊。...
作者:纪连海第一章 雍正皇帝到底有几个皇后看过《后宫甄嬛传》第一、二两集的朋友会发现,这第一集里有个“孝敬宪皇后”;而第二集里又说甄嬛与早先过世的“纯元皇后”十分相像。这就引发出了下面的三个问题:一是一般而言,清朝的皇帝到底应该有几个皇后?二是具体到雍正皇帝本人而言,他到底有几个皇后?三是雍正皇帝是否有个“纯元皇后”?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一般而言,皇帝应该有几个皇后?这就得先来看看大清王朝在雍正皇帝之前的这四个皇帝(大汗)的后宫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平生娶了16位女人,当时把这些女人统称为“福晋”,到了康熙年间,才按照她们的历史地位,分别追封各种名目的内宫称谓。被封为皇后1人,元妃1人,大妃1人,太妃1人,继妃1人,侧妃4人,庶妃7人。努尔哈赤的皇后姓叶赫纳喇氏,名叫孟古姐姐,是努尔哈赤第6任妻子,共活28年,生了皇太极,后来皇太极当上了皇上,“母以子贵”,成为皇太后;元妃姓...
作 者:[俄]帕斯捷尔纳克第一章他们走着,不停地走,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歌声休止的时候,人们的脚步、马蹄和微风仿佛接替着唱起这支哀悼的歌。行人给送葬的队伍让开了路,数着花圈,画着十字。一些好奇的便加入到行列里去,打听道:“给谁送殡啊?”回答是:“日瓦戈。”“原来是他。那就清楚了。”“不是他,是他女人。”“反正一样,都是上天的安排。丧事办得真阔气。”剩下不多的最后这点时间也无可挽回地流逝了。“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苦苦众生。”神甫一边念诵,一边随着画十字的动作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撒了一小把土。人们唱起《义人之魂》,接着便忙碌起来,合上棺盖,把它钉牢,然后放人墓穴。四把铁锹飞快地填着墓坑,泥土像雨点似的落下去。坟上堆起了一个土丘。一个十岁的男孩踏了上去。...
作者:[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作品赏析·--------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而扣人心弦。安娜第一次出现时的音容笑貌令人难以忘怀:她姿态端丽、温雅,一双浓密的睫毛掩映下的眼睛中“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在眼神和微笑中显现出来。在这幅出色的肖像中展现了安娜的精神美,也提示我们去探究她的生活之谜。安娜父母早逝,在姑母包办下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大官僚卡列宁。婚后在宗法思想支配下她曾安于天命,只是把全部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渥伦斯基唤醒了她晚熟的爱情。她渴望自由而大胆地爱,不愿像别特西公爵夫人那样在家宴上公开接待情人;也不愿接受丈夫的建议仍然保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偷偷与情人往来;终于冲出家庭与渥伦斯基结合,...
剧中人物--------------------------------------------------------------------------------腓迪南 那瓦国王俾 隆朗格维杜 曼 国王侍臣鲍益马凯德 法国公主侍臣唐·阿德里安诺·德·亚马多 一个怪诞的西班牙人纳森聂尔 教区牧师霍罗福尼斯 塾师德尔 巡丁考斯塔德 乡人毛子 亚马多的侍童管林人法国公主罗瑟琳玛利娅凯瑟琳 公主侍女杰奎妮妲 村女群臣、侍从等地点那瓦第一幕--------------------------------------------------------------------------------第一场 那瓦王御苑 国王、俾隆、朗格维及杜曼上。...
作者:陈文茜【,】内容简介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世人从迷梦中惊醒。美国万亿美元救市,冰岛国家破产,全世界经济一片哀嚎。如今,另一波崩坏正在发生,这个崩坏如荆棘藤蔓,隐发自美丽的欧陆。地中海的蓝天白云,依旧一派悠闲,但光天化日之下,恐怖剧码正在上演。希腊、法国、德国,无一幸免,欧洲经济体此刻正在崩坏,并且祸及全世界!看似不相干的社会运动总是祸起经济危机。世人都将焦点转移至中国。她是否能成为世界的救世主;她的年轻一代又经历着怎样的社会煎熬。是否全世界的这一代人都将成为这一轮经济危机的牺牲品?陈文茜以全球视野切入当下被广泛关注的欧债、美元、中国发展等经济问题,用历史的围度参照现实,串起全球性大事件,解读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
作者:许开祯【,】第一章 抱屈上任1车子在驶往三河市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着,马其鸣的心情仍然郁闷难平。从昨天到现在,马其鸣的情绪始终处在一种似痛似愤的不平中,他做梦也想不到,省委会来这一手,把他突然地从景山开发区副指挥的位置上撤下来,挪到三河去。这个决定太令他震惊,他几乎无言以对。马其鸣认定,这跟半月前召开的现场会有关。半月前,景山开发区在二号施工段召开现场会,省委佟副书记亲自到场,陪同他的有开发区总指挥、景山市市长许大康,还有省建设厅、省计委等方方面面的领导。二号施工段是开发区示范工程,由曾副指挥亲自抓,马其鸣平常很少来这儿。市长许大康向佟副书记详细介绍了二号施工段的建设过程,还不无得意地领着佟副书记参观了新建成的开发区统办大楼、科技信息城等。...
=春天,去看一条河在春天,去看望一条河。我居住的城市有一条大河,常年水汽蒸腾。春天,我要坐在河边,好好看看它,去想象河流里每一滴水珠的命运。它从天上落到地下,这段旅程不比一个人走过的路简单。我们常常感叹人生有多么坎坷和磨难,想来最多也就是一滴水的命运吧。我要在春天的河边,和自己娓娓谈心,接受一次浩荡春水的洗礼。在春天,对亲人说一声,我爱你。忽然间才发觉,我和亲人们似乎变得有点陌生了。多年来,我越来越沉默地坐在他们身边,一旦听到唠叨,就没了闲心,起身便走。如今的我才明白,爱在心里扎了根才会有唠叨。爸妈,尽管我抱怨过,哀愁过,但我依然爱你们。我想多陪在你们身边,多听听你们的唠叨。如果有一天,我突然站起来拥抱你们,情不自禁地说一声:“我爱你!”请不要慌张,也别羞涩,这么久以来,我只是羞于开口。...
全球化之舞:向海而生的中国企业 作者:王育琨 2005年若干中国一流公司演义了各有千秋的中国版全球化。育琨君的《全球化之舞》,力图写照这一宏伟历史场面,以期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实践留下一本闪光的备忘录…… 进入21世纪,勇于探索的中国企业家,超越自己所需的敢想敢为,汇集成一股强势的中国力量和震惊世界的潮流。作者审查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事件,潜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司如华为、联想、海尔、TCL以及海外的索尼、三星、IBM、惠普等的全球化事件和领袖人物的思维中去,用全新的视野,解读最前卫的全球化案例,挖掘深刻而复杂的人性,得出极富实用价值的结论。这里有许多原生的全球化事件,鲜活的案例,冷峻的观察,清明的智慧……...
作者:陆明前言管理的第一要素即是管人,也就是要根据人的心理和思想规律,通过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来改善人际关系,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劳动和管理效率。古人云:“人事之最难在于知人”,我们在每天的工作中需要和形形色色的人进行“心理上的较量”。那我们怎样才能在和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充分调动起周围一切的人力资源,让他们尽最大可能的为您服务呢?这其中包括您的员工、您的上下级关系、您的同事、甚至你的客户。这时若您能将管理心理学知识利用起来融会贯通,使之服务于我们的工作、生活,那您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成为无往而不利的强者!我们可以列出这样一个递进的等式:了解人的心理驾驭人的心理=支配人=支配世界。由此可见,我们任何一位渴望成功、渴望支配世界的人都应当而且必须了解并掌握一些管理心理学的知识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