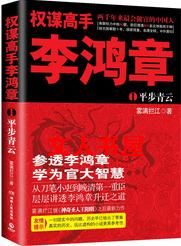晚清有个李鸿章-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李鸿章《二十自述》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从北京来函,叫李鸿章入都,预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收到父亲的来信后,李鸿章兴奋异常,他意识到自己报效国家,实现抱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从祠堂郢村老家出发,包括在去京城的路上,李鸿章一共提笔写了10首《入都》诗。这一组诗,一直为后人所传诵。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频年伏枥困红尘,悔煞驹光二十春;马足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遍交国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即此可求文字益,胡为抑郁老吾身!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
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
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已有殊恩;壮怀枨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
桑于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
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
一枕邯郸梦醒迟,蓬瀛虽远系人思;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诗酒未除名士习,公卿须称少年时;碧鸡金马平常事,总要生来福命宜。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故人共赠王祥剑,荆女同持陆贾装;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骊歌缓缓度离筵,正与亲朋话别天;此去但教磨铁砚,再来唯望插金莲。
即今馆阁需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览镜苍苍犹未改,不应身世久迍邅。
一入都门便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槐厅谬赴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
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李鸿章这10首诗虽然有一些矫情的成分,但在这样的诗中,明显地能看出一个人郁积于胸的大志。这10首诗在总体上有着相当才华,也是一代读书人的心声。一个行装寒碜、气宇轩昂的弱冠书生,怀着报效天下的强烈愿望,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去寻梦,其心境,其经历,都颇能引起那些皓首穷经梦想显达的士子们的共鸣。这也难怪李鸿章的这10首《入都》诗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曾国藩曾对李鸿章有一句半真半假的评价“只顾拼命做官”。这也算是从本质上一语中的。李鸿章的确是一个有着宏大志向、异常执著于功名的人。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李鸿章的这10首《入都》诗中,还隐藏着强烈的宿命意味。这一组诗有着浓郁的预见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偈语的意味。有很多今后的宿命,李鸿章似乎都觉察到了,也写到了。其中的一些诗句,出人意料地与李鸿章的人生轨迹相吻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首:“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这样的诗,哪像是一个21岁青年所写的呢?分明像临终之人的绝笔。正因如此,这组诗更有幽秘色彩,散发着凛凛的极地之光。
第十章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4)
一个人的气质总是与他的生长环境有关。安徽设省是在康熙年间。对于新设立的行省安徽来说,位于江淮之间的庐州并不有名,也一直受着冷落。它只是一个小地方,商业不发达,读书的风气也不是太浓。但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地方绝对让人不敢小觑,在历史上,这一带就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的交际地带。在安徽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具有一种通变的精神。这种通变即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它包括“批判、会通、创新”等环节,即胆识兼备的批判精神、兼容并包的会通精神和超越前人的创新精神。李鸿章之前,这一带在历史上就出过很多雄才大略,比如说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管仲,秦末项羽大帐中羽扇纶巾、料事如神的范增,汉末三国纷争时的枭雄曹操,以及东吴大将周瑜、鲁肃等。除此之外,庐州本身就在宋朝出了一代名臣包拯。而离李鸿章在时间和地域上最近的,是明朝开国皇帝、凤阳人朱元璋。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当然给这块土地积蓄了足够的底气,也决定了这一带经常出没卧龙凤雏般的人物。
正因为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在李鸿章身上,集中体现了很多江淮之间人的特点。具体说来,那就是在为人处世上,李鸿章既有中原人行为大气、敢作敢为、有机智有心计、懂勾心斗角的一面;同时也有南方人比较务实、精明能干的特点。从总体上来说,李鸿章仁慈、开朗、诙谐、喜权力、爱面子、重义气、狡猾、精明、不迂腐,在为人处世上比较平民化,
幽默、和蔼、直接,有时候带有很浓的痞气。
这个生长在祠堂郢村的合肥东乡人自小便有着很强烈的功名抱负。等到李鸿章24岁的那一年,他考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这也是安徽当时最年轻的翰林。李鸿章在翰林院当了一段时间编修之后,对于那种机械八股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厌倦极了,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正在此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朝廷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不堪一击。朝廷无奈只好借助于民间的力量来“平乱”。曾国藩被派回湖南后不久,办团练、组建湘军,在阻击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朝廷见这条路的势头不错,于是又派了一些京官回乡“练勇”,李鸿章与他的父亲李文安也被先后派回安徽,组织民团与太平天国打仗。
李鸿章回故乡组织民团还有个故事:李鸿章在京时,经常去一个名叫吕贤基的安徽老乡处,吕贤基时任工部左侍郎,旌德人。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顺江东下,攻占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安徽巡抚。消息传到北京时,李鸿章正在琉璃厂的海王村书肆买书,听到这则消息后,李鸿章连忙找到吕贤基,怂恿他上书朝廷,调派人马夺回江淮战略要地。吕贤基认为李鸿章很有战略眼光,文笔也好,便让李鸿章代为执笔奏折。结果奏折送上之后,咸丰帝命吕贤基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没想到自己竟被直接派到前线,全家人一时如丧考妣。吕贤基情急之下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
李鸿章的回乡之路并不平坦。当李鸿章回到庐州时,这片土地已是满目疮痍,昔日的诗情画意早已消失殆尽,有的,只是战争的残酷和硝烟:庐州失守,安徽巡抚被杀,李鸿章的家乡磨店也被太平军占领。李鸿章一到庐州,即忙着招兵买马,筹备与太平军的战斗。有点出乎意料的是,李鸿章的开局相当好,他很快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民团队伍,并且在
巢湖一带首战告捷,这一次胜利据说还是清军在皖的首场胜仗。为此,李鸿章受到了朝廷的蓝翎赏赐,官位从七品升至六品。第二年,吏部左侍郎王茂荫保奏李文安回乡“劝勉乡人,团练自卫”,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也从家乡来辅佐父亲。在此之后,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接下来的战斗很快变得残酷无比。不久,与李鸿章一同来安徽作战的吕贤基在舒城战败后投水自杀。第三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这个一直声称自己平庸无能,但却能培养出好几个杰出儿子的老实官吏在战局僵持中抑郁而死,临终时留下了“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的遗嘱。李鸿章又接二连三地打了好几个胜仗,先是攻克含山,然后又参与攻克了庐州。朝廷为了嘉奖李鸿章,将他的官位一下子提升至四品。
第十一章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5)
一个人的成功总会引起一连串的忌妒。现在,该轮到官运亨通的李鸿章了,一些谗言开始流传,更有人静静打报告给上司,说李鸿章的那些功劳都是偷天陷阱。更让人恼怒的是,来安徽的满族钦差大臣胜保也参了李鸿章一本,说李鸿章贪生怕死,兵败后混杂在土匪中溃逃。类似的小报告因为明显缺乏证据,很快就不了了之。安徽巡抚福济却乘机夺走了李鸿章的兵权。不久,庐州城再次被太平军占领。1857年底,陈玉成率太平军在合肥东乡三河镇,歼灭湘军李续宾部6000余人,李续宾战死,随军的曾国华失踪。李鸿章赋闲在乡,都未得参与。在此期间写了《明光村镇旅店题壁》,抒发胸中的怨气:
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袖携淮海新诗卷,归访烟波旧钓徒。
遍地槁苗待霖雨,闲云欲去又踟躇。
不久,李鸿章干脆携带家眷出逃,离开了安徽,来到了江西,投奔大哥李瀚章。曾国藩得知李鸿章的去向后,连写几封信给李瀚章,让李鸿章来湘军大营。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曾国藩身边。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走出了最为幸运的一步。这样的行为是他走上人生显赫道路的开始。李鸿章在曾国藩身前左右观察和感悟到的,可以说,恰如其分地采了这位大儒的“气”弥补了自己的软肋。李鸿章的性格和气质得到了根本性的升华,为日后成就一番事业,奠定了基础。
1862年,李鸿章40虚岁,在这一年中,李鸿章终于扬起了他人生的风帆,真正地起航了。
1861年9月5日,曾国藩率领湘军收复军事重镇安庆,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局势,对太平军形成了顺江而下的局面。与此同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部率重兵出击,打到离南京不远的地方。从战略上说,湘军对太平军的战略形势已经由防御、僵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太平军的失势,与其说是败于湘军,不如说是败于自身的内乱。由于太平天国本身的宗教观支离破碎、一知半解,有着浓郁的迷信色彩,缺乏正确的济世理想和组织理念,这样的集团在经过短暂的成功之后,很轻易将重心转移到对内部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上。攻下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内部爆发了闻名的“天京事变”,太平军产生内讧,韦昌辉刺杀了杨秀清,石达开拉起大队人马离开了天京,太平天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大大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平天国无奈放弃北上的进攻目标,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安庆失守后,太平天国更是陷入恐慌,他们一方面固守天京,另外一方面把进攻方向转向了富庶的上海一带。这样的行为,很明显不是以取得政权为目的,而是退而求次,预备与清廷各霸一方。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前锋直指上海。
在沪的江南士绅、买办慌了,他们紧急筹备“中外会防局”,希望西方列强出面干涉,同时选派曾是李文安、曾国藩“同年进士”的钱宝琛之子钱鼎铭,携冯桂芬起草的书信抵达安庆,泣请曾国藩发兵救援。曾国藩大为动容,一连几天与李鸿章商量发兵之事。洞察力惊人的李鸿章向曾
![[bleach]我和死神有个约会封面](http://www.9wshu.net/cover/0/39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