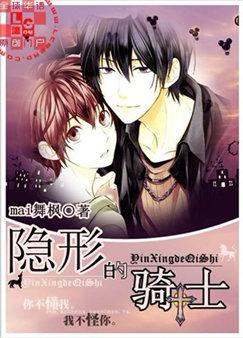隐形伴侣-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容易把菜园子像攻克碉堡似的攻下来,人困乏得干着活儿一闭眼就能睡着,出工总迟到,饭也常吃不上,日月星辰都乱了轨道。等陈旭想起来要看冰排,人说大江早已解冻多日了。并且,那早十几天播下的白菜籽,竟然就从土里绿茸茸地冒了头来凑热闹,一冒头就张着嘴要喝水;喝了水就引狼入室,招来一层密密的杂草,今儿铲了,明儿又来了,大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架势。就算你满不在乎,对它们宽容忍让,却有许多眼和嘴,会立即热心地愤怒起来:“肖啊,你家那菜园子……”菜园子是个地主婆,要人侍候。侍候原来是这样的滋味。丽丽赖在城里不下乡,嫁给省军区一个连长,生孩子还请保姆。食堂管理员已勒令他们退伙,年轻轻两口子吃食堂,懒成这样,不怕人笑话?结婚干啥?结婚不就是自个儿做饭,一条炕上睡觉吗?刘老狠批一车麦秆给他们烧火做饭,那麦秆拌着冰碴儿,做一顿饭就像熏蚊子,烟火缭缭的,总把肖潇弄得满面泪痕。
她任凭泪水混和着疲倦与委屈,涌流纵横。在大雨滂沱中哭泣,在游泳池里出汗。她时常并不躲避那股凶狠的黄烟,而是让它把她的头颈一古脑儿缠绕起来。勒紧她,勒得眼前一片混沌,一片模糊,勒出了几丝苦涩的水,心里才松快些。
“你哭了?”陈旭拿起筷子,仔细打量她。
“不,烟熏的。”她淡淡说。
先前那许多关于爱和未来的梦想,竟然就在那一天天蓬勃滋生的小白菜里消融下去。好像让那些青翠娇嫩的绿叶吸去了精华,做了菜园的肥料。每日早晨昏昏醒来,她总是惊异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地方……
肖潇瘦了。
分场竟然又卖起猪羔子来,五毛钱一斤,一只猪羔十来块,便宜。养到秋,二百斤大肥猪吃肉卖钱随你。成了家的人不买猪羔子养活?全分场的家属不在背后讲死你!
竟然就又分起自留地来。一个人三分,两个人六分。一里地长的垄,端端正正六根,等着人去刨苞米埯子。种上大豆苞米,到秋天喂猪喂鸡,干啥不好?你不想种这六分地?全分场的家属不笑话死你!
不买猪羔不行,不种自留地也不行。
虽然她有陈旭,陈旭有泡泡儿和扁木陀,他们的自留地里的苗苗,还是不如人家的出得齐全,他们的小猪羔还是不如人家的长得壮实。尽管陈旭发过誓,要在过年时让肖潇吃上猪肝和腰花汤,可猪槽空了,他却死活不肯到食堂去捡菜帮子……
肖潇叹口气,拎上一只土篮,走出去。
一行南来的大雁欢叫着从她头顶飞过。
杨树林在暮色中笼罩着一层淡青色的烟雾,浮荡地弥散飞升。树梢上蹲着那个忙累了一天的太阳,牵着自己未了的千头万绪,慢慢沉降下去。游尘中飞扬着阳光的温暖,安静地匍匐下来,归于泥土,空气中有一种新鲜又湿润的青草味,带着泥土的芬芳,从四面向她围拢。她的心有些慌乱,她看见树林子边上,地头地角那些枯黄的草根里,探露出一丛丛绿色的生命,眨着好奇的眼,从新生土地中拱出来。
啊,小草,是春天唤醒你们,还是你们唤醒了春天?
“踏青去!”妈妈说。苏堤上有猫耳朵,马兰头,荠菜馄饨,鲜死人了。比比谁先采到荠菜王……
而这里,把婆婆丁、苣荬菜、灰菜采下扔进篮子,却要填一口生锈的大锅,熬成一团浆,倒进猪槽。啊,小草,小草……
篮子沉甸甸,却空荡荡。她发一会儿呆,又蹲下身子。
大路上的广播喇叭响了,一个清晰的女声在播诵一篇讲用稿,似乎,有个熟悉的名字,从耳际滑过去。她站起来,用心辨别,那声音在昏昏的暮气里一遍遍重复着,——是郭春莓,是郭春莓在地区讲用的发言。
那声音说,她主动承担了二百头育肥子猪的任务,一天推饲料两吨多,每天打扫猪圈六遍,拉水车二十趟,每天背草垫圈,还发明了猪舍和饲料之间的洗脚池,让猪蹄保持卫生。她还设法把大豆炒熟,掺入饲料,使猪每天增重一斤半……
她埋下头,拼命地挖菜。
那声者说,她宁离娘一世,不愿离党一秒;
那声音说,她要永挑重担,消灭帝修反;
/* 53 */
《隐形伴侣》十七(4)
那声者说,她和“活命哲学”斗,斗私斗到死;
那声音说,为革命大养其猪,她要把血流尽、汗流干……
一阵冷风,肖潇打了个寒噤。
她也在发展养猪事业,为谁?不过,在水里游泳是多么痛快呀!小鸭说,让水淹没你的头,往水底一钻,多么痛快呀!她也在发展养猪事业,为谁?
篮子里的野菜浓郁又苦涩的气息,撩拨起她心上一种难言的惆怅。几丝内疚,几丝惭愧,几丝怨恨,回荡在苍茫的暮色里。你到底在做什么?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不求上进了?堕落了?庸俗?自私?软弱?……你完了!
她跌坐在草地上。篮子猛地翻扣过来,野菜撒了一地……
草地上开满了黄色的小花。
她拎着一只花篮来采花。篮子是竹子编的,里头放一本书。
她坐在山坡上看书。书页上的字其大无比,像墙上的大标语。一会儿翻一页,一会儿就看完了一本,却不知它讲什么。
书里夹一张书签,是一朵玫瑰花,她闻闻,发现那花没有花心。陈旭走过来,把花儿插在泥里,说:这是蚕豆花,种蚕豆吧。
她的蚕豆长得快极了,像竹笋,在大风里往上蹿。比向日葵还高。结下香蕉似的大豆荚,里头的蚕豆,像蚕宝宝一样是白的。她问陈旭,陈旭说:这不是蚕豆,是罗汉豆。
她把罗汉豆吞下去,她想自己大概马上变成罗汉了。罗汉只吃大白菜土豆,她低下头,看见自己变得好胖,肚子像罗汉那样鼓起来,陈旭拍拍她的肚子说:一定是儿子!她有点恶心,哇哇地吐,吐完肚子就瘪下去了。她端着猪食盆去喂猪。
一只黑花小猪,在砖砌的猪圈里团团转,发出狗一样的叫声。她把苞米粥倒进破脸盆里,那小猪吭吭几口就把粥吃得干干净净,它翘着嘴唇沿四壁又拱又舔,一会儿工夫,把一块砖头吞了下去,真上食!一个包头巾的老大娘说,多给它吃!又倒进一盆粥,一会儿又没了,再加一勺,还是没。她掰开它的嘴,发现那里头黑森森的是个无底洞,任你怎么填也不会满。她不再喂它,让它去吞砖头,它却掀翻了食盆,把砌墙拱得摇摇晃晃;她用一根树枝去抽它的脊背,它竟然咬住了树枝,差点跳出墙来,又嗷嗷地叫,脖子耸一耸,大耳朵呼扇呼扇,好凶。
这是条狗还是猪呀!她想看看清楚。有人说:这猪卖我吧,能看门。
陈旭在她耳边嘀咕:这猪肚里长朱砂了,不能随便卖,长朱砂的猪才这么怪。
她想不起来朱砂是什么,忽然听见广播喇叭里说总场文艺宣传队来演节目了,她刚要往回走,有人叫了她一声。
大路上走来一个姑娘,飘曳的长辫子,微微扬起的脸,迎着太阳,光彩照人。她觉得她有点像自己,想了一会儿,才明白她是宣传队的独唱演员郁笛。
她一闪身躲在了猪圈后头。
郁笛手里拿着一副竹板,系着红绸子,边走边唱:学大寨一定要往远处瞅,别坐在炕梢看炕头……哎嘿哎嘿呀……
她用手掩住耳朵,大叫:你唱啥格越剧?真难听。
郁笛不理她,还唱,唱了好久,总是一个调:哎嘿哎嘿呀——竹板不响了,郁笛说:这是东北二人转。
那个人呢?她问。明明是一人转。
不是,是独脚戏。郁笛把一只脚勾起来,像一只站在水里的鹤。也叫单出头。
她很想跟郁笛学单出头,就跟着郁笛往大架子上爬。上头有云雀在叫,小提琴声从云缝里传来……
郁笛钻进云缝不见了。她爬上一段阶梯,大架子猛烈摇晃起来,好像要倾斜倒塌。她叫了一声,跌下去。
/* 54 */
《隐形伴侣》十八(1)
华丽丰茂的夏季,踌躇满志地走过旷野。田垄的土圪和树根却把它的光脚板硌得生疼,三叶草和苍耳在烈日下越发刺烫灼人。夏天匆匆走过,撕烂了盛装,脚板上挂满丝丝血痕。夏被熬干了,变成了萎黄的秋。
收割后的水田,留着一丛丛半尺高的稻茬。初冬的早霜,将稻茬染成一块开花的棉田,银光璀璨。偶有几朵遗忘在田埂上的蒲公英,被风一吹,似凄清的小雪扬扬洒洒,水田的低洼处,看得见一束束干瘪的稻穗,标本似的封存在玻璃般的薄冰下……
秋也是筋疲力尽。
工间休息的时候,陈旭坐在稻草堆上抽烟,闷闷地想着心事。
脱谷还没有开始,这几天的活儿不太累,只是将割下的稻子码垛装车,拉去场院。他喜欢挑叉子这个活儿。狠狠地扎住几个捆,轻轻一抖,甩出去,像甩去了许多不快,浑身轻松。力气用得巧,可省下体力去干家里的活儿。自留地的苞米黄豆倒是收得差不离了,过冬的柴禾还没有备足。路边的蒿草,都竖了捆,有了主,得上水库去割苇子,一来一去二十里地。炕要扒、火墙要掏、北窗要堵死、南窗要溜缝,还有大白菜土豆要下窖、大红萝卜要用沙子埋上……这件没做完,那件已在等着,没完没了,与其说为着猫冬倒不如说是像替自己下葬,万事须料理得齐齐全全……
他厌烦得很。他知道自己完全是机械而无可奈何地去做那些琐碎又琐碎的家务事。
平心而论,他对那些事,几乎完全没有兴趣。厌烦发作的时候,他真想把眼前的锅碗瓢盆,通通砸个稀烂。完全是为了让肖潇高兴、让肖潇满意,他才不得不在天亮时迷沌沌地睁眼去自留地;天黑时酸乏乏地上井台挑水。肖潇用起水来像个没龙头的管子,哗啦哗啦,一会儿缸就见了底。她改不掉她那个爱干净的毛病,照样一天洗三遍脸,照样三天擦一遍澡,照样一盆衣服洗得水清清才罢休……肖潇疼他,一个月分场卖一次肉,她总省给他吃,可从来不怜惜他担水。他连条扁担也没有,一只手一个桶,一口气拎到家门口,她笑笑,苍白的脸上浮起两个满足的笑靥,像个漩涡,一闪又不见了。
他却从心底疼她。夏天时她黑瘦黑瘦,这几个月脸上身上却突然像个发面团似的“胖”起来,胖得暄松,一按一个坑。她总照镜子。他不敢说,那不是胖,是浮肿。妊娠的女人恐怕都是要这样“热胀冷缩”一番的。
那未知的小生命,也如同一架无声的发动机,驱使着他从地里到家里,奔忙劳碌。为迎接他(她)的到来,他像一只公狐或是雄燕,本能地筑巢猎物。他意识到自己可笑,便惶然又怅然,他实在没有任何思想和物质的准备,在此安居乐业,传宗接代,他原本是为着养息心头的创伤,才躲进这避风遮雨的小窝,在她的温情中汲取活下去的勇气。然而,她把那根救援的绳索扔给他,缚住了他,也缚住了自己。他俘虏了她,也俘虏了自己。两个残兵败将,却在无意中得了一个胜利果实,他得知她怀孕那天,只觉得两眼漆黑,满腹酸水,竟也似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