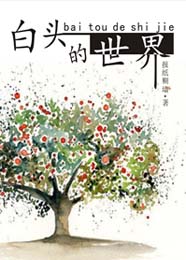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莫泊桑述评-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一看大马车在田野间行驶、当野外的景色象画一样映入她们因肉欲而凄迷的眼帘时,那种由然而生的返仆归真的体验吧:“绿油油的田野在大路两边伸展,到处都夹着一大片一大片黄橙橙的油菜花,起伏不定,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有益健康的气味,一股刺鼻的、甜津津的气味,被风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在已经长得很高的黑麦中间,露出矢车菊天蓝色的小脑袋,她们想去采摘……有时候整个一块田好像被血淹没了,原来是田里长满了虞美人。在野花装点得无比美丽的原野上,白马小跑着,而那辆大车装的好象也是一束更加绚丽多彩的鲜花,一会儿消失在一个农庄的大树后面,一会儿又在树丛的另一头出现,重新在夹杂着红色或蓝色的那些黄色和绿色的庄稼中间载着光彩夺目的一车妇女,在灿烂的阳光下飞驰。”这种在原野上的飞驰,正是回归自然的一个象征;而在巴黎,除了肮脏、灰暗的房屋之外,她们见不到大自然。
接着,是向质朴的人性的回归。她们走进教堂。“后来突然一下子静下来了。”莫泊桑描绘着这乡下教堂时的仪式,”所有到场的人都同时跪下,主祭神父登场了,他白发苍苍,年高德劭。”在经文的诵念声及随后的唱诗班的歌声中,某种圣洁的超升的力量潜入这些妓女的内心,唤起了对美好的往昔岁月、尚未堕落的岁月的回忆,以至被这些遥远的回忆“压得透不过气来,涕泗滂沱地呻吟着。”令人不解的是,莫泊桑这个对宗教毫无信仰之心的登徒子,描绘起教堂的崇高的仪式时,竟像一个天主教的艺术家。
《泰利埃公馆》完稿以后,莫泊桑并没有将它拿到《高卢人报》或什么别的报纸专栏上去连载。尽管他在巴黎已经出了名,可是他的那些作品不是结集在 《梅塘晚会》里,就是间断地连载在报纸上。必须在巴黎的读者中再抛入一颗炸弹!——莫泊桑想——而这颗炸弹除了是完全属于自己名下的一本集子之外,还能是什么别的呢?
带着《泰利埃公馆》的手稿以及其它两篇刚写出来的中篇小说的手稿,莫泊桑找到一家不起眼的出版社,位于圣拉萨尔火车站附近的阿瓦尔出版社;之所以找阿瓦尔这样的小出版社,是因为莫泊桑眼下对自己尚无十足的信心。当然,阿瓦尔出版社的经理维克托·阿瓦尔受宠若惊地接受了手稿,并建议莫泊桑赶写几篇,好使集子显得更厚重些。
一八八一年五月,以《泰利埃公馆》作书名的小说集问世。这个集子收了八篇近作,除《泰利埃公馆》外,还有《在河上》,《一个女雇工的故事》,《一家人》,《一次郊游》,《春天》,《保尔的妻子》以及另一篇早已发表过的短篇小说 《西蒙的爸爸》。这个小说集再度使莫泊桑成为巴黎谈论的一个话题,也使阿瓦尔出版社的牌子得为人知。
一些大的出版社——例如大出版家沙邦吉埃的出版社——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即低估了一个“新手”的天才。
《泰利埃公馆》的扉页上题着这样的献辞:“献给伊万·屠格涅夫,以表深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慕。吉·德·莫泊桑。”这人莫斯科人是值得莫泊桑如此敬慕的;这位客居法国的俄国作家不仅是莫泊桑的挚友,而且,更主要的,是他的又一位精神影响者。不过,屠格涅夫施与他的影响和福楼拜的性质不一样,更带一点虚无主义的色彩,这几乎和莫泊桑本已有之的厌世情绪一拍即合,甚至成了他此后看待世界的一副镜子。屠格涅夫把莫泊桑的小说集带到了俄国,并赠了托尔斯泰一本,而正是这位俄罗斯大文豪替莫泊桑作品的俄文本写了序言。莫泊桑的天才已不拘限于巴黎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法国评论界对于莫泊桑评价的或誉或毁,几乎都是基于艺术上的原因或是基于梯也尔时代的道德规范;而来自托尔斯泰的评论则更注重某种人性化的道德力量,也即一种道德的宗教在作品中的映射。“那使一部艺术著作凝结成一个整体,从而产生反映生活的幻象的这种结合力量,并不是人物与环境的统一,而是作者对事物的独特的道德态度的统一。”托尔斯泰这样说道;这是一种非法国式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批评,而非法国式的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批评。
这部小说集体现了一八七五年——那时,莫泊桑还只是一个整天耽于野心的练笔者——莫泊桑在致母亲洛尔的信中对于自己日后作品总体的一个构想:即在小场景上展示小人物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或昙花一现的“荣”与无可挽回的“辱”。
巴黎最高贵的沙龙也向莫泊桑敞开了大门。他被介绍进了克利希街朱丽叶·德鲁埃的圈子,而这位杰出的女子,众所周知,是大诗人雨果的情妇。雨果在这里接待来访的艺术同行们。这位体魄刚健、仪表堂堂、灰胡子浓头发的老作家穿着软底鞋,在柔软的地毯上缓缓走动。这个圈子要算巴黎精神趣味最高的圈子,也是那个时代的天才们——随便点出几个:甘必大,乔治·克列孟梭,斯泰法纳·马拉美,法尔居耶尔,罗丹,絮吕·普吕多姆,勒孔特·德·利斯尔,弗朗索瓦·科佩,等等——聚会的场所。然而这个过于贵族气的沙龙是不适合莫泊桑这位狂放不羁的诺曼第人的,他和巴尔扎克一样,对于贵族社会,除了想征服它的最有魅力的女人外,并不觊觎其它。因而,莫泊桑更愿意去另外一个女人较多的圈子,圣格拉蒂安的玛蒂尔德公主的沙龙,与他初识的奥迪尔·布雷纳把他介绍进了这个令人回忆起第二帝国那些无忧无虑的岁月的圈子,而这位在上流社会中如鱼得水的女子日后不仅成了莫泊桑文学上的开路者,而且成了他的情妇,——当然,只是那些情妇中的一个,因为这位过于痴情的女子向他透露了这么一条“至理,”一条于连·索黑尔和拉斯蒂涅都曾顶礼膜拜的“至理”:“切不要忘记这一点:永远是女人使男人获得成功。”
尽管如此,沙龙以及都市,对于莫泊桑来说,仍是一个不自在的场所。“说到底,他从来就没有适应过大城市的生活。”马克·安德里写道,“他开始定居巴黎时,就感到外省人背井离乡之苦。”至于莫泊桑是否有背井离乡的感受,那是值得研究的;可以肯定的是:巴黎或者任何喧嚣的都会,都不适应莫泊桑这个过分留恋大自然的诺曼第人居住。
就在他引起各沙龙注目的时候,他却离开了巴黎,于七月登上了赴阿尔及利亚的海船。
他更多地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踏上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大陆的。他凭吊古战场,了解土著文化,而夜里呢,就睡在帐篷里。不久,又随同两个法国军官,在茫茫的撒哈拉大沙漠中跋涉。“多么遥远,远离世界,远离生活,远离一切,躲在这又小又低的帐逢里面。”莫泊桑在文章中写道,对这种类似沙漠苦行僧的生活似乎感到惬意。“在沙漠游牧民的帐城,他感到巴黎是一个不健康的城市”,安德里写道,“城里挤满了肆无忌惮的野心家。”
这次长时间的旅行,几乎没有映入他的作为小说家的视野——作为小说家,他不愿把任何一种走马观花似的东西写入作品内;而是映入了他的作为“记者”的视野,——它形成了那本出色的游记《向太阳》,一八八四年该书在巴黎出版。
重返巴黎的莫泊桑再一次发现:在他外出时,巴黎不仅没有忘记他,反而以更大的热情等待他的新作。 《费加罗报》、《吉尔·布拉斯报》以及老伙伴《高卢人报》都像饿坏的胃一样等着他去填充。莫泊桑没有让巴黎失望。不久,一八八二年五月,他的又一个小说集《菲菲小姐》,由布鲁塞尔的出版商基斯特麦克斯出版问世。
这个集子中最值得一读的是那个不朽的短篇 《菲菲小姐》。莫泊桑再一次揭示了那个已经过去十二年之久的战争主题,这个主题曾在《羊脂球》中得到天才般的反映。和 《羊脂球》一样,上场的仍是法国的妓女与作为征服者的普鲁士军官。这些占领军对诺曼第长得没完没了的雨天感到烦闷透了;为了解闷,他们从鲁昂找来了五个妓女。可在吃晚餐时,那个名叫“菲菲小姐”的普鲁士少尉无礼地说了一通有辱法国尊严的狂言。“法国和法国人,法国的树林、田野和房舍都属于我们!”这个金黄头发的小矮个子满嘴酒气地嚷着,把一杯香槟酒倒在了一个妓女的头发上,“所有的法国女人也属于我们!”这句话刺痛了良知犹存的法国妓女的尊严,那个烈性子的拉歇尔站了起来。喊道:“我!我!我不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妓女;普鲁士人需要的正是这个!”气急败坏的菲菲小姐抡起胳膊打了她一个耳光;为了自卫,她把一把餐刀插进了他的胸口。菲菲小姐直挺挺地倒在地板上。趁着混乱,拉歇尔跳窗逃走,逃到附近的教堂钟楼躲了起来。故事在雨声与远远传来的欢快的钟声中结束。
这篇小说只是重复了 《羊脂球》的那个主题,即在一个沉沦的灵魂里,仍有一种不可沉沦的尊严,正是这种主要见于布衣短褐之下的尊严,才使法兰西民族从失败的泥污里站起来。
《菲菲小姐》及此前的《泰利埃公馆》两个中短篇小说集的问世,已向莫泊桑自己、并且也向整个文坛证明了他是一个伟大的短篇巨匠,一个文体家。不过,莫伯桑并不满足于这些“小小的杰作”,他想像福楼拜那样在更大的场景上展示人物的命运。他不用在远处寻找题材。他从自己的家庭里就看出了一种隐在沉默之中然而像岩石一样沉重的悲剧:浪漫主义的“蓝花”在一个对它不利的时代里的命中注定的枯败。
早在一八七七年,在莫泊桑的习作稿中,就有以自己的家庭为剖析的对象而构思出的一个长篇小说的写作提纲。然而,就七十年代而言,一部从大场景上反映心灵史的长篇小说,是超出莫泊桑的能力范围的。于是,这个写作提纲被不断地修改,不时地被添进去一些活页似的片断;直到一八八三年——离最初的构思已有整整六年了!——莫泊桑才灵感忽至地找到了形式,而赋予了这部间断地写了几年的作品一种命运的逻辑;这种逻辑,正如他在一篇论文中所提到的,是“一连串巧妙地导向结局的匠心组合。”这部题为《一生》的长篇小说于四月份问世。立刻引起了轰动。
紧接着《一生》的出版,莫泊桑变戏法似地又向饥渴的巴黎抛出了两个短篇小说集: 《山鸡的故事》与《月光》。当然,这和先前的一些短篇小说一样,这些故事的场景仍在外省,在诺曼第。莫泊桑仿佛从打猎中感受到了一种在巴黎的裙带边不能得到的刺激,一种更男性化的刺激或者征服。几个小时隐蔽在树丛中,或者端着猎枪从早到晚在诺曼第光秃秃的平原上奔跑,追赶那些时而飞起、时而俯冲下来的鸟群。“我象一只山羊那样敏捷地朝前走着,眼睛望着我那两条在前面东翻西找的猎狗。”这个熟悉打猎生活的作家写道,“塞尔瓦正在右边一百米外的一块苜蓿地里搜索。”
这些野外的生活以及所见所闻后来都成了莫泊桑小说的直接题材。
他仿佛把自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