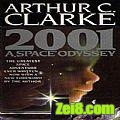书屋2000-09-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实上釜底抽薪的是价格,而价格则是图书市场一个潜在的辣手摧花的杀手,书价成倍数倍地不断攀升向上,令人咂舌的价格成为屠宰阅读羔羊的最快的兵不血刃的利器,公众的阅读快感在经济这柄锋锐的无往而不胜的利器威逼下消解。受众在权衡利弊计较得失的最终选择了忍痛割爱,形而下的实用主义从来都是形而上的理想主义的天然克星。
古人各领风骚二百年而今人约略走红一两天。自由阅读的意志体现无遗,大众的选择使二者的口味先后三异其变。爱人者恒被人爱,成为一个创造和阅读的真理。
屡教知改的花儿和草儿们索性不肯生长,抑或生长出别一样妖异的姿态,褪化成吃昆虫的猪笼草或是让牲畜们吃不成的骆驼剌或是狼毒什么的。远离社会大众回避矛盾,一壁厢深情地抚摸自己,一壁厢婆娘式的诟骂他人,眼里没有别人而只有自己,置他人的玉液琼浆于不顾却一味自恋式地啜吸自己的排泄物,成为一款新的喝尿族。世纪末的浮躁还具体表现在太过功利和急切地甚至是不择手段地盲目寻找大师,排定座次,乘机也为百年后的自己顺便寻找一个名不副实的所在。
凡此种种不如意构筑成一道人为的樊篱,隔膜了唇齿相依的天然关联,休戚与共的生存纽带也被畜意斩断。羊儿们吃不了也不再吃那些变异的草,甚至索性不再做羊儿,脱下羊皮披起了狼皮,与羊儿们做了对头。随处可见的是无所事事低迷纤弱莫名其妙空空荡荡寻寻觅觅的野草闲花,和冷漠的置身事外的羊儿们以及已经扮出一副狼模样的阅读受众,谁也不去问津世纪末呈现萧条和疲软的创作和阅读的草场。没有创作便不会有阅读,而一个世纪的阅读质量如何,将取决于这个世纪的创作实绩。然而辉煌也罢幽微也罢都将成为过去。新一轮的阅读和创作即将随着新世纪的曙光而展开。创作的热铁烙刻在阅读的木头上会留下印痕,冰块却只能留下一滩清水,冷静和热力缺一不可,得事先储备。
可怕的是好的坏的都一块迈入了新世纪,世纪末令人担心的一些东西也同样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初。有钱人不读书,没钱人读不起书。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极大逆转。人们在有意无意地漠视道德,漠视是非,漠视行为准则,忽略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钱重要的道理。所以我想问一句:中国,在世纪之初,你创作的思考和阅读的准备,做好了没有?
“吐新纳故”谈读书
? 段崇轩
写字台、床头柜上,总是堆积着墨香幽幽的书籍、报纸、杂志,崚崚嶒嶒如一座小山。隔一段时间就须清理一次,但过不了多久小山又长了起来。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每天都要读书,还不时的写一点东西,就像农民种地、工人做工一样,阅读和写作就是我们最日常的劳动和职责。但近年来我却深切地感受到:该阅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总是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阅读状态中;读过的东西似乎很多,但收获却越来越令人怀疑。书店的新书像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过些时间就忍不住光顾一次,抱回一摞;全国的几家权威性文学月刊、选刊,总是如期寄来,不可能全看,但为着了解文坛动向,也得浏览一下吧?《读书》《文学评论》等几份理论杂志,自费订阅已经多年,每期总会有几篇感兴趣的文章。《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两份大报,虽然是周刊,但一期有二十四版,加起来就是四十八版,经天纬地;鲜活尖锐,不能不看。再说,这些书报杂志大抵是自费购置,不读岂不是等于把钱漂了水花?不要说有时为写一篇文章,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阅读大量的有关作品和资料;不要说为自己圈定的研究领域,要有意识地收集材料、阅读书刊、摘录卡片了。仅仅是如上所述的那些新书新报和新杂志,就足够你天天“饱餐”了。反正我每天晚上的宝贵时间,几乎都交给了这些时尚读物。我们就像“减负”之前的中学生,被名目繁多的书海、题海轮番轰炸,被情愿不情愿地“填鸭”一样灌输着。我们生存在一个时尚读物层层包围着的文化世界中。
有一件事深深刺激了我。今年有两家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关于乡村小说研究的专著和一本文化随笔集,终校由我来“把关”,校完书稿,我突然觉得有一种空虚感和愧疚感。洋洋四十万言中,到底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呀?到底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呀?它在当前的人文研究领域能有自己的“立锥之地”吗?我在自个的作品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时代潮流的泡沫、对他人的重复以及自己的一些零星感受。而缺乏真正的文学研究应有的扎实的文化根底、开阔的审美视野、特别是自己独到的思想探索。而造成这种局限和“病症”根源的,正是那些貌似新颖、现代、开放的时尚读物!多年来我不敢懈怠、勤勉读书,收获得竟是一些发育不良的果实。我相信我的这种阅读和写作状态,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也是许多同行朋友的“通病”。看来我得改变一下自己的阅读思维和阅读方式了。
我想到了德国著名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悬置”式研究理论,他认为要把握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将一切有关客观与主观事物实在性的问题都存而不论,并把一切存在判断“加上括号”排除在考虑之外,而要通过直接的、细微的内省分析,从而“回溯到事物本身中去”。现象学是一种复杂而艰深的哲学,我们不必也无力去细加探讨,我感兴趣的是它的“悬置”理论与方法,它对我们的读书与研究倒是颇有启迪意义。读书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譬如为了增长知识,为了修身养性,为了提高境界,但它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与写作。读书与写作犹如耕耘和收获,二者密不可分,互为因果。读书的范围与质量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写作的境界与成败。如果我们沉陷在鱼龙混杂的时尚读物中,是断然写不出博大而精深的学术作品的。如果说这些年来我的写作中还有一些值得自慰的篇什的话,那么孕育它们的“土壤”绝不是那些时尚读物,而是一些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包括新时期以来的优秀作品)给予我的陶冶,是一些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社科理论著作对我的滋养。而这些好书在我的阅读历程中竟是那样少得可怜。看来,我们的阅读也必须来一次革命,来一个“悬置”,坚决地把那些时尚读物赶出写字台和床头柜,使我们的阅读回到文化的源头,回到经典中去,这样我们的写作才有可能进入自由而独创的境界。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时尚读物是一个美丽的陷阱。生活类书刊教你怎样实现衣食住行的现代化,把你诱入一个丰富、温柔、便捷的时尚化人间;文学作品进入多元化时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自会有一些精品力作诞生,但却普遍存在着浅薄化、世俗化、消解人文精神的倾向,很容易使人头晕目眩、丧失判断;人文科学的境况似乎好一点,总会有一些恪守贞操、特立独行的学者、理论家,在那里“十年磨一剑”地著书立说,薪尽火传;但也会有一些投机钻营者,在那里东拼西凑、邯郸学步、现炒现卖甚至欺世盗名,搞出一些泡沫式的伪学术来。浸染在这样一种时尚读物中,你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那无异于在沙滩上盖楼、在温室中养花。更有一些理论上的“二道贩子”,生吞活剥地读了一些西方现代理论,就煞有介事地制造出一套套的理论“体系”,变幻出一串串的怪诞术语,让你陷入理论上的迷魂阵。新思想新观念往往具有极大的传染性和误导性,如果你缺乏坚实的思想根底,就极容易被人所俘虏所异化。在我的那些习作中,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
文化、思想、文学的发展是有“源”、“流”之分的。当前林林总总、热热闹闹的思潮和作品,只是特定历史转型期的一种潮流而已,它来去匆匆,大多是随波逐流的“浪花”,能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毕竟是少数。真正的阅读就是要溯流而上,找到各种思想文化之“源”,从源头中吸取思想、精神、智慧、方法。譬如孔子、孟子、庄子,譬如刘勰、三曹、司空图、王国维以及现代评论家的文论;譬如西方古典、现代的哲学和美学;譬如古今中外那些久传不衰的文学经典。回到源头、经典自然不那么容易、轻松,但只有在那里才能获得真知和智慧,才能构筑起自己的思想文化堡垒。所谓“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当然,时尚读物也不可以全部“扫荡”、束之高阁,其中的时代精神流向也还是要努力去把握,文化市场的“行情”也还是要晓得一些。但你切不可太在意、太投入,否则就会被潮流淹没,难以自拔。
看来,我的写字台、床头柜上该来一番“吐新纳故”了。
夏清泉的画——也谈构思
? 方 成
在我国漫画家里面,除为数不多的老漫画家之外,大都是八十年代前后从各地涌现,至今才二十年,还都是业余创作,自学而能的。他们的作品总的看来,大多是表现技巧往往只偏重艺术构思的一个方面,而对绘制技法考究的人是不多的——而这应当是艺术构思的另一个方面。漫画艺术重幽默——讽刺一般也是幽默的。幽默可说是一种语言方式,是艺术语言。其运用技法,是看你怎么说得俏皮,画得其味。要想得奇巧俏皮,自然是艺术构思的功夫。但漫画是画出来的,要用画面人物艺术形象来展示,那么,画中人物造型以至表情动态,都是画家创作出来,同样要经过艺术构思过程。对这方面重视的画家却不多,在绘制上看得很明显。绘制上的粗简使表现技法不足,自然会削弱作品的艺术魅力。夏清泉也是八十年代前后起步的漫画家。他的作品发表不像一些同时代作者那么,但他在创作上颇为严谨,从作品的内容,表现技法和绘制笔墨上都下功夫,不草率。作品的艺术效果得以较充分发挥,自有较强感人之力。
重读《绿天》
? 高道一
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苏雪林(绿漪女士)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病逝,享年一百零四岁。这是继冰心女士辞世后,我国文坛殒落的又一女作家。
我手头收藏有一册北新书局一九三一年七月第五版毛边本,绿漪女士的成名作《绿天》。说起来,那还是三十九年前,我在北京西单商场旧书摊上淘到的。在版权页上贴有“小梅”的朱文版税印花(小梅,大约是苏雪林原名苏梅的缘故吧)。这本书我是翻阅过的。今天重读却无意中发现书中夹有一张木版印制的蓝色“覆据”(21×8厘米),内容是“今收到忠兴(即兴)乡呈文壹件 民国二十年七月六日”,落款是“县教育局稽查处”的长条形红色印章。巧合的是,这个日期正是该书出第五版的时间。因此我推想,大约是乡政府的一位文书,到县城送公文,他是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这一天早早地来到县城,衙门还未办公,先去逛书店,买了一本刚刚出了第五版的《绿天》,然后将公文送到县教育局,随手将收据夹在书里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收据就沉睡在书中。过了三十年,不知怎么的,这本书流落到西单的旧书铺,其原因可以做多种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