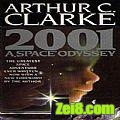书屋2002-01-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失去的故乡才是真正的故乡。忘记了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写乡愁的作家都生活在别处,是“别处”照亮了“故乡”,是“别处”确认了“故乡”。刘亮程说:“我中断了这种生活,我跑到了别处。远远地回望这个村子我才更加清楚地看清了它们:尘土飞扬中走来走去最后回到自己家里的人、牲畜,青了黄,黄了青的田野、树。”
故乡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某个处所,它跟经度纬度无关,跟土地肥瘠无关,跟贫富无关,跟人口多少无关。它只跟人的心灵相关,跟人的精神相关,是远离之后难于割舍的眷恋,是五步一回头的伤感,是对韶华不再生命流逝的慨叹,是追怀往事的怅惘。故乡是心灵的寄寓之所,是精神的栖居之地。
那个村庄原本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个村庄在别人眼里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刘亮程以他特殊的目光打量着的村庄,以他敏感的心感受着的村庄,以他的回忆、 联想和想象重构着再造着的村庄,以他的文字描述着的村庄。我们差不多是站在他的背后,看他把头时而抬起时而低下,时而左转时而右转,我们循着他的视线捕捉视点,指认视角。他注视着村庄,我们注视着他的注视。他感受着村庄,我们感受着他的感受。他描述着村庄,我们也想描述他的描述。谁要是抱着实证主义的态度,以那个地理学意义上的真实村庄为蓝本,为依凭,去实地考察一番,来验证刘亮程的散文,肯定会大失所望,也会大煞风景。
细节的聚焦和放大
已经消逝的人、事和物,我们凭借记忆把它们重新唤回,用文字符号向它们招魂,把它们从过去的时光中带回到眼前,变为活生生的、当下的存在,重新建构我们与这些人、事和物的关系。照我看,这就是写作的意义。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记忆。记住什么忘掉什么,是一个人记忆的秘密,它把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区别开来。有的作家记住了生活宏大的一面,有的作家记住了细微的生活情景。刘亮程属于后者。他说:“那些存在于角落,没有被人留意的琐屑事物,或许藏着生存的全部意义。”他会记起“早年贪玩没留意的半句话和一个眼神”,他要在记忆中寻找“早年掉落在地上的一根针”。对细节的聚焦给他的每一篇散文烙下了特殊的印记。村庄里的人、畜、树、风、阳光以及其他事物都在他的散文中充分演示各自的细节:
他正从西边一个大斜坡上下来,影子在他前面,长长的,已经伸进家。他的妻子在院子里,做好了饭,看见丈夫的影子从敞开的大门伸进来,先是一个头——戴帽子的头。接着是脖子,弯起的一只胳膊和横在肩上的一把锨。她喊孩子打洗脸水:“你爸的影子已经进屋了。快准备吃饭了。”
孩子打好水,脸盆放在地上,跑到院门口,看见父亲还在远处的田野走着,孤独的一个人,一摇一晃的。他的影子像一渠水,悠长地朝家里流淌着。
公驴像腰挂黑警棍的乡村警察,从村东闲逛到村西,黑警棍一举一举,除了捣捣空气,找不到可干的正事。
狗追咬一朵像狗的云,在沙梁上狂奔。
我拿过多少回的那根木棍,抓手处的木节都已磨光磨平。
西风进村时首先刮响韩云家的羊圈和房顶。
小饭店没有窗户,他们一个接一个进来时,像风中的门一开一合,小饭馆里一下一下地黑了七八次。
刘亮程似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轻而易举地逮住事物的细节,那些我们往往熟视无睹的细节。这与他有着锐敏的、精细的感觉分不开。在我们没有感觉的地方,他有感觉。在我们有轻微感觉的地方,他有强烈的感觉。在我们有强烈感觉的地方,他已经被感觉击倒在地了。
为了突显细节的逼真,营造细节的“现场氛围”,他频繁地使用数量词。“我在第七声鸟叫之后,悄悄地爬下草垛”。“我确实听见了鸟总共叫了八声。”他告诉你鸟叫了几声,很准确,好像一个小学生掰着手指在数着。“听见动静人大喝一声,狗狂叫两声。”人的叫声和狗的叫声是一比二,一点不含糊。他要点燃一蓬蒿草,连划三根火柴都没点着,“第四根终于划着了,点着了。”请记住,是“第四根火柴”划着了。刘亮程就是这么说的。“蚂蚁得三年后才敢把家搬到新来人家的墙根,再过三年才敢把洞打进新来人家的房子。”你最好别问这里的“三年后”是否真实可靠,他可没说自己是昆虫学家。“我见过一只老鼠抱着一棵草,摇来摇去,落下七粒草籽。”老鼠真行,摇下七粒草籽,要是每天吃一粒,正好吃一周。跟着刘亮程,我学会了算术。村庄里有一户人家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 “面袋抖了三遍,灶上空沸的半锅水,浮着几片枯叶。”如果这一家的主人背着刘亮程“再抖一遍”,那么面袋应该是抖了四遍。“那根直端端指着我们家房顶的横杈上少了两个细枝条,可能入冬后被谁砍去当筐把子了。”河边一棵树上的细枝条,他也数过了。你知道半下午的时候一堵土墙的影子有多大吗?你我恐怕都不知道,但刘亮程清楚:“它的影子里顶多能坐三四个人,外加一条狗,七八只鸡。”
普鲁斯特认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不在于艺术描述对象的伟大还是渺小,而在于作家对这一事物的感受。他说:“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只要被感受到,得到再创造,就再也不是微不足道了,就成为整个生命,成为艺术。”〔1〕
刘亮程对重大的社会事件不感兴趣,一双眼始终盯住村庄中的细节不放。当他的笔墨偶尔牵涉较大的事件时,他也是作了“细节化”的处理,转移我们的视线和关注事物的焦点,让我们的目光从大处回落到小处。比如村里选村长,他不写别的,却大写狗的反应:“那几个想当村长的,一人拉一把子人,整夜整夜拉选票,挨家挨户敲门,闹得狗彻夜吠叫,许多狗捱不到村长选出来,就早早挣死了。剩下的狗叫到最后也没声了,嗓子叫坏了。狗一叫坏嗓子,不几天就急死了。”
在他笔下,时间也是由村庄中细小的事物来刻度的,你无法从他的文字获得那种由外部重大社会事件来刻度的时间,诸如1949、1966、1978等。他要让细小的事物给原本空洞的时间注入内涵,他从细小事物的变化和衰朽中领悟时间。“锨刃磨钝,镰刀变成一弯废铁,墙倒塌水井枯竭,木门和家具被虫蛀朽,虫老死,牲口剩下出气的力气。”一条麻绳历经一代又一代人的使用,由粗磨细,“麻绳扔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人最后也把麻绳给扔了。”有一条路被走坏了,废弃了。有一棵树由小长粗了。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描述着这一切,向我们传递属于村庄内部的时间意识。他说:“一个村庄的一百年,无非是草木枯荣一百次,地翻耕一百次,庄稼收获一百次。”
聚焦细节的同时,放大了细节。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一张小嘴就占满了整个画面。在科技影片里,甚至人体的一个毛孔就占满了整个画面。特写镜头的作用,就是放大事物的局部和细节,扩展和延伸事物存在的空间。刘亮程用了类似的手法。他放大了村庄一个又一个的“毛孔”,而后隆重邀请我们走进这些“毛孔”。这里的一个人,一只虫,一个木桩以及其他事物仿佛比别处大了几十倍、几百倍:
木桩上绑一根麻绳,细细的,顺着绳摸去,是一颗牛头,牛一动不动,鼻孔里的气沉缓又均匀。顺着绳摸回来,摸到木桩上的树疙瘩,脚踩上去往上摸,有一个斜杈,滑溜溜的,杈的根部一道斜斧印,已经磨蹭得不刺手——这是韩云家的拴牛桩。
有人从屋里端出一盏灯,一只手遮住灯罩,半个院子里晃动着那只手的黑影。
我侧过身,清晰地看见枕在炕沿上的一排人头。有的侧着,有的仰着,全都睡着了。我突然孤独害怕起来,我觉得不认识他们。
村庄是小的,村庄中的人、事和物更小,但是当一个又一个的细节被聚焦,被定格,被放大,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无比丰富、无比阔大的世界。
想像的真实和诗性的话语
刘亮程曾在那个村庄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身上留有与他一同生活过的“许多事物的珍贵印迹”,“我成了记载村庄历史的活载体,随便触到哪儿,都有一段活生生的故事”。村庄的一草一木,一虫一畜,一事一物早已渗入他的皮肤、骨血和心灵。
然而,我们现在读到的文字,绝不是一个锁闭在村庄中的人有关他个人以及村庄中其他人和物的刻板记录和生硬报告。这些文字内在地包含了三种距离。一是空间的距离,他是从城市遥望那个村庄。二是时间的距离,他是从现在回望过去。三是想象与现实的距离,散文里的村庄与实际的村庄是两码事,它已经过了想象的变异和变形。
简单记录外部世界的物象、景象和事象,不能成为艺术。这样的事也无须由作家来完成,只要一部傻瓜相机,就可以做得更好,最多外加一部摄像机。艺术的创造,需要的是自由的想象。哲人爱默生说,生活的真实包括想象的真实。想象拓展了狭窄的生活,想象给生活注入了新的内涵,想象展现了事物不同的可能性,想象开启了另一个不同的视域。
一只蚊子吸了一肚子血,血太重了,蚊子的翅膀驮不动,蚊子摔在地上,死了。一头牛吃了春天的绿草,又去河边饮了水。春草枝枝叶叶蓄满了长势,尽管吃到了肚子里,在水的滋润下又长了一截子,牛便撑死了。一个梦游的人走到另一个村庄,被狗咬醒。是不是生活的巧事,都让刘亮程遇上了呢?显然不是,问题的答案只有在他的想象中去寻找。
“在西边的一个墙角上,我的尿水年复一年已经渗透地壳深处,那里的一块岩石已被我含碱的尿水腐蚀得变了颜色。看看,我的生命上抵高天,下达深地。”刘亮程不可能用肉眼看到地壳的深处,他是用想象的目光去看。
在野外,一只狼朝他瞪着蓝幽幽的眼睛,突然又跑开了。一个偷苞谷的贼,一条腿断在地上,用另一条腿追他,他惊惶失措。这些童年少年的往事未必真的发生过,大抵不过是心灵深处恐惧意识的产物。他说:“或许许多事情都没有发生,但被我经历了。”“随着岁月日长,我越来越分不清哪些生活情景是现实,哪些是梦幻。”
当作家以强大的想像力穿透外部事物,化物为“我”,寻常的东西就会产生不寻常的意味。刮风时院门一开一合,“我站在门外,等风把门刮开”,“我一进去,风又很快把门关住了”。一块经世多年的木头和经世多年的一个人“经年的相依中一些木质已进入掌纹和身体,人的气息和心境也渐渐磨进木头”。一棵树被砍倒了,但刘亮程说大树的影子还保存在天空中,“整个天空满满当当地浮现出一棵树,天空在用我们不清楚的方式念记天空下消失的每一样事物。”“我们家榆树上的一片叶子和李家杨树上的一片叶子,在空中遇到一起,脸贴脸,背靠背,像一对恋人和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