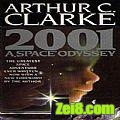书屋2002-01-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真正甘于寂寞、特立独行的精神,以学术为崇高的事业。我又想起了青年时期的费尔巴赫那句名言:“你知道,真理决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决不会头戴皇冠地到来。你知道,经常受到世界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普通人。”
学术商品的供应与需求
? 党国英
把学术与商品联系起来,是要招人骂的。但如果仔细研判一番学术成果的供给条件,便会发现把它看做一类特殊商品,大抵是讲得通的。
学者著书立说,大多想拿著作给人看,为的是求得声誉或换得金钱,很难找到例外情形。如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做学问虽然不是为金钱,但为在自己的交往圈里求得闻达,却是有的。一切衣食无忧的人士都可能不为金钱而做学问,但干脆不为声名而做学问却是极为罕见的。肥马轻裘的阔佬与衣不蔽体的穷人有不同的偏好,前者拿学问作为交往的手段,但在后者面前却浪得一个风雅的名声,让后者以为他们的风情雅习是天生的。其实,旧时代的学者要么想把自己的学问做给皇帝看,要么做给同好看;恐怕是因为做学问给皇帝看的风险太大,或者成本太高,才有人乐意在同好之间交流学问。也有人做学问变得穷了起来,但那绝不是初衷。在当今时代,做学问成了一种职业,一种安身立命的行当,就连声名也成了换饭吃的手段。追求做学问的乐趣还是有的,但不是首要目的。于是,学者把自己的著作当成商品,也就是平常事了。如果有人做学问既不追求安邦定国,也不是为了安身立命,而是纯粹追求一种所谓特殊的“生存状态”,一种生活的乐趣,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学问有没有人欣赏,更不去考虑把自己的著作当成商品来兜售,那么,除非天道相助,使他们衣食无忧,否则他们的学问是做不好的。这番道理有史为证:中国历史上鱼米之乡出才子。学术商品要丰产,物质商品投入要充足,这恐怕是学术商品生产的最基本的规律。
生产学术商品的人,便是学者。钱钟书曾刻意区分学者和文人,推崇前者,鄙夷后者,这好像有理,其实经不住推敲。揣摩他的意思,对做学问的人,他是把德行好的看做学者,把德行不好的叫做文人。这不对。学者的德行也就在一般人的平均水平上下,德行差的可以做出好学问,德行好的却未必一定做出好学问。不是有材料说罗素的德行也不怎么样么?学养对学者的行为的确有影响,例如,中共党史上有学者背景的人物,比起其他人物,往往更多地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无畏气魄,其原因也可能是学养深浅影响了人的价值观,而价值观不完全是一个德行问题。价值观对人产生一种内在约束,而德行对人只是一种外在约束。当大众景仰一个人的价值观时,常常误以为他们在景仰这个人的德行。我说这番话,是想指出学术商品生产的另一个规律:学术商品是道德中性的。
对学术商品,在社会上有几种不同的需求。
一是大众的需求。以我的经验,大众需要一些教条式的政治判断、政治口号或其他时尚语言符号。大众并不需要真正新颖的思想,或者对新颖的思想接受起来极为缓慢;新颖的思想使他们不放心。如果有人把新颖的思想变成教条,并与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大众才会为之欢呼。大众也不需要复杂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理解起来太难。实际上,满足大众对理论的需求,往往是通过政治化的学者来实现的。
另一种是一般读书人的需求。这种人喜欢新奇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喜欢的新奇往往可能是平庸的东西。这些人往往把自己看做是有相当鉴赏能力的人,其实其中的一些人也实在是附庸风雅。但这些人对学者的著作有极大的需求能力,是最大的图书购买群体。这些人极易受媒体的操纵,而媒体也常常看这些人的眼色行事。有证据表明,那些浅薄的学者很可能赢得这种人的青睐,而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的作品,要赢得他们的欢心实在很难。原因很简单,这些聪明的人并没有时间去认真读几本书,对学问的好坏不具备判断资格。但是,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智高一等,一定要去捧新奇的东西。这就像叔本华说的那样,因为人人都读不懂黑格尔,所以人人都说黑格尔好,黑格尔伟大。
第三种需求是学者圈子的需求。学者的自命不凡的毛病,其实是对新东西的恐惧,是想守住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只有少数站得很高、不害怕谁超过自己的学者,或者已经被偶像化的学者,才显示出一种宽容与大度。学者的圈子里原本有一种互相吹捧的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垄断资源,求得自己的长期安全。于是,有一种表面上看来奇怪的事情,就是一大批学者聚集在一小撮并不懂学问为何物,或者已经告别学问的“学阀”或“学贩”的门下。
政府对学术商品的需求要复杂一些。政府官员作为个人,对学术商品的需求表现为上述三种需求中的一种;作为官员,对理论的需求程度和需求方式则取决于政府的结构。我们可以多侧面地分析这个问题,但这需要一篇大文章。这里我只想说我的一个体会。常听人们说学者们对政府发生多么大的影响,有人甚至把政府的一些错误归咎于学者的“坏点子”。这种看法实在是夸大了学者的作用,是一种外行之见。在和平时期,政府往往有自己的信息搜集和信息处理系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过滤信息,学者们对政府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短期看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斯蒂格里茨甚至说过,理论经济学对政府行为干脆没有影响。真正对政府行为发生影响的,是现实的压力,包括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社会紧张程度的压力以及国际环境的压力等。学者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可能在大的时间跨度里才有意义,特别是通过教育这个环节,学者们对年轻一代的知识结构发生影响,官员从这些年轻人中产生,学者们对政府的影响才间接地得以体现。
按照常理,领政府薪水的学者该为政府说话,但因为政府的运作有一个成本问题,所以学者们也有可能并不竭力去满足政府的需要。所以,他们对政府的俸禄坦然受之,同时又以批评政府为己任。从历史的经验看,政府与学者之间的这种博弈并非一定有很糟的后果;如果有好的历史条件,这种关系还能推动民族的进步。
左派!是吗?不是吗?
? 雷池月
从正反两方面提出的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回答,通过这种“反复论证”之后,从逻辑上说,问题的答案会更接近真理(真相)。但事实上却未必如此,有时往往像风靡一时的大学生辩论会上的交锋一样,离结论越来越远。汉武帝刘彻悼念李夫人的名句“是邪?非邪?……偏何姗姗其来迟!”属于纯粹的抒情,并不要求答案(当然也得不出答案,不过中了齐少翁的骗术而已);而在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里,“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这段脍炙人口的台词,就成为极具思辨色彩的问题了。然而如果有人真要去论证,那也是绝对没有结论的。
虽然这种提问方式并无补于求得真相,但人们都还是习惯地想依靠它来解除别人或自己认识上的困境。作为常人,岂能免俗?于是便有了本文这样一个标题。
话说大约四五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议论苏俄历史得失的文章,一位当记者的熟人看过之后说:“最好寄到《XXX追求》去。”他说话时表情平静,看不出任何褒贬的意思,而我偏偏又孤陋寡闻之至,根本不知道《XXX追求》是何方神圣!过了许久,才明白那是某些文化人所戏称的“左派据点”。当时我想,他如果不是开玩笑就一定是误解了我文章的意思,小事而已,一笑置之。过了两年,又渐渐地风闻有人议论我是“新左派”。直到最近,终于亲耳听到一位先生在电话中对别人说:“雷池月啊……这人好像很左!”——顺便声明一句,我并非有意偷听,而是适逢其会——总之,看来我是真正被某些人定性为“左派”了。事已如此,不得不采取“是吗?不是吗?”的形式反躬自问,并把心得昭告于所有关心我的人。
先问“是吗”?答曰“不是”——按惯例得先进行无罪推定。根据是什么?想了很多条,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从十八岁被划定为极右分子,二十余年间,为这顶帽子受尽了非人的磨难——就凭这一条,若干年来形形色色非左非右、时左时右、亦左亦右的政客、文棍、老变色龙和“破落户子弟”便没有资格对我在政治上作这样或那样的定性。为了证明言无虚谎,必须简要回顾一点历史,尽管我很不情愿又一次忍受揭开伤疤的痛苦。
严格地说,四十多年前那个初夏,当我犯下“向党和人民进攻”的极右罪行时,尚未满十八周岁,如果在今天,也许可以援引《未成年人保护法》来为自己开脱的。可惜,那时不兴这一套。我都有些什么具体“罪行”呢?大字报两张:第一张约两三百字,就肃反问题、胡风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和学生科(管理学生的机构,那时编制紧,不像今天叫什么学工部或学工处)的职能作用,提出了一点简单的并且决无恶意的疑问;第二张则不过数十字,大意是既然要人家提意见,就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而不应反过来追究当事人。这张大字报是为我定案的主要材料,曾经被收辑到广东省编的《毒草集》第二卷。可以说决定我此后的命运,它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我至今不很明白它何以会引起当权者那样强烈的反应,以至就在那个夏天,还没开展批判斗争,我就已经被划定为极右分子。
反右斗争是我走向成人生活的第一课,所受“教益”,理当牢记。可惜我偏偏是比较健忘的人,只记得“和风细雨”云云,言犹在耳,“暴风骤雨”却说来就来,至于群众斗争的宏大场面,当时未必不刻骨铭心,如今却已是模糊一片了。对于所谓的“批判斗争”,事后主要的感想是,人类在漫长的史前时期进行的大量围猎活动中,逐渐形成一种从玩味猎物的恐惧和痛苦中取乐的本能。进入文明史后,这种本能所渴求的快乐就从失去反抗能力的异族人、异教徒和一切异己分子身上去得到满足。壮观者如罗马克里色姆竞技场,惨烈者如圣·巴托罗缪之夜,声势浩大者如1936年反犹太法颁布后的柏林或汉堡……至于个人记忆中的某些面孔上洋溢着的那份从“斗争”中所获得的兴奋和愉悦,无疑也是这种本能的极好的证明。在历史上好的或坏的政治在这里有一处极明显的分野:前者压抑这种本能,不给它提供发泄的机会;后者却诱导和培育它,使之不断发育膨胀。谢泳有本书叫《中国知识分子自杀考察报告》,简而言之,自杀几乎无一不是不堪被围猎的痛苦和恐惧而作出的选择。我不相信有哪位领略过真正高标准的“批判斗争”滋味的人,没有萌发过死的念头,活下来的总是顶过了或错过了那最揪心的一刻。
斗争高潮过去以后,决非境遇改善之时,因为兽性一经煽起,不加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