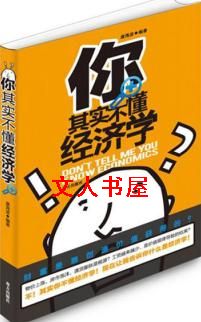张五常学经济-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高的学问:十年窗下只写一本历史书(The Prosecution of Huguenots and French Economic Development),注脚的文字远比正文多,其考查的严谨与详尽真的一丝不苟。得到感染,一丝不苟是我自己后来的治学之道,只是四十七岁后,累了,下笔只着重自己的思维,不管他家之说。
我有机会问Scoville:「十年窗下一本历史书,值得吗?」他回应道:「我那本书的题材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只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众人皆说昔日法国逼害新教徒(Huguenots)对法国经济有很大的不良影响,我研究的结果说没有。最近一位法国史学家评论这本书,说在我之后法国这个老话题是不需要再研究了。学问的发展,总要有些人花时间去回答一些问题。如果我花十年能使后人不需要在同一问题上再下功夫,应该是值得的。」这是学问的真谛,深深地影响了我,虽然后来作研究时,见到生命那么短暂,我要考虑很久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才动工。
学问茫茫大海;学者沧海一粟。一个学者希望争取到的只是那一粟能发出一点光亮罢了。
艾智仁与赫舒拉(求学奇遇记?之八)
曾经多次写艾智仁与赫舒拉发,因为他俩是我求学时最主要的老师。这里从比较广泛的角度说,也比较简略。自己平生最高的荣誉,不是什么院长会长,或什么大教授,而是行内任何知道艾智仁与赫舒拉发的人,都知道我是他们的学生。少人知道的,是我没有选修过他们的课。我是他们的旁听生,每个旁听了三年。我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写成的。
一九六一年进入了研究院,选修的价格理论由R。 E。 Baldwin传授,教得好!这位老师来自哈佛,教的是新古典与哈佛早期的理论基础。宏观与货币我师从K。 Brunner,很苛求,是在他举世知名之前的事了。选修过的科目不能再选修,所以只能旁听艾智仁与赫舒拉发的课。
一九六二年的秋季我开始旁听赫舒拉发。艾智仁当时造访史坦福。旁听赫舒拉发的第一课他就对我重视,而差不多从那天起他就认为我是他教过的最好学生。奇怪几个月后的口试(前文提及)他不给我通过。艾智仁呢?他要等看到我的博士论文才没有怀疑。
早就听到艾智仁厉害,不少人说他是价格理论的天下第一把手。我当时开始意识到,经济学其实只有价格理论,只要掌握得好,什么宏观、货币等都可以变化出来。当时我读过凯恩斯的搞起宏观经济学的《通论》,认为作者对价格理论掌握得不够。那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季,我认真地求学三年了。
进攻价格理论的策略是明显的。从Baldwin那里我打好了传统价格理论的基础,尤其是这位老师把新古典经济的各大家教得通透。跟着轮到赫舒拉发。赫师也是哈佛出身,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对费沙(I。 Fisher)的利息理论与资本的理念发表过重要文献,可以填补新古典的一角空白。再跟着轮到艾智仁,还没有上过他的课,但听说这个人的思想天马行空,无从捉摸,我倒要尝试一下。
我是因为要等艾智仁从史坦福回到加大,旁听了他的课,才考他出的博士试题,于是决定缓慢下来。后来等到进入研究院的第三年的下学期才考博士笔试,但同学通常分两年考的四张试卷,我在五天内考完——三卷第一,一卷第二——追回了时间。
旁听了赫舒拉发几个月后,我问他:「你的学问与艾智仁的怎样比较呢?」他回答:「我广博,艾智仁湛深。」是重要的提点,也显示我选走的Baldwin…Hirshleifer…Alchian的路线与次序是很理想的策划。当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并不大名,但从多方的评论与自己读过的文章衡量,天下间不可能找到更为优胜的学习价格理论的阵容。我已经拜读过所有关于价格理论的名著,而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佛利民(M。 Friedman)的《价格理论》,虽然是天书,但较早的「非法」学生笔录版本我背得出来。
策划确定,问题只是艾智仁要到一九六三年的秋季才授课。打冲锋,需要选修考试的科目清理得七七八八,等艾智仁,等听过他的课才考他出的博士试题,一时间变得无锋可冲了。我于是决定跑到图书馆去,获得一个仅可容身的小房间,差不多一半日子住在那里,不分昼夜地读,读得天昏地暗,只是要旁听或进膳或消闲一下才跑出来。那大概是一九六三年初到一九六五年秋季转到长堤作助理教授的时日,读了两年半。
长驻图书馆就有这样的方便:书本用不着借出来,以小车把一组书籍推进自己的小房间,读后放回在通道可以找到的小车上,有工作人员替你执拾。这样读可以读很多,而当时我选读的不限于经济,凡有兴趣的都翻阅一下。感谢上帝,妈妈遗传给我的过目不忘的本领,大有用场。无论什么题材,翻阅三几本就觉得说的差不多,抄作远多于创作,知道搞学问不容易杀出重围。那些批评我数十年不读书(实情如是)的人,不知天高地厚。
那时我对考试漠不关心。还要考的四个博士笔试随时可以考。这种试考基础,考知识,考思维,无须准备。等艾智仁,因为知道他考的是思想,我要跟踪一下。
听课与跟老师研讨,比起读老师的论著有很大的分别。一个学者的思想有很多细节不可能全部写下来,而这些细节能让学生体会老师的思考方法。一九六三年秋季第一次听艾智仁的课,很有点失望,因为他说明旁听生不准提问。这一点,同学们也失望:我提问别开生面,往往举座哗然,很热闹的。后来艾智仁容许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提问,只我一个,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羡煞同学也。
艾智仁的思维深不可测,是每个同学的感受。当时我对价格理论的操纵,可谓来去自如,但开始听艾智仁的课,我不知他在说什么。我想,有这样的深度,我一定要触摸到他的层面才罢休。旁听到大约第三个学期(那时一年二期)我开始触摸到这层面,第四个学期豁然开朗。话虽如此,转到长堤任职后的第一年,每次艾师讲课我尽可能驾车回到加大旁听。
走毕了上述的Baldwin…Hirshleifer…Alchian的价格理论的全程,第一次开花结果是论文《佃农理论》。后来不少人认为那是价格理论应用的典范。这些评论加起来比不上艾智仁当年说的那样深刻。他说:「不要以为你推翻了所有前人对佃农的分析而沾沾自喜。你没有提出任何新理论,只是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你比他们都高一点。」
从长堤到芝加哥(求学奇遇记?之九)
《佃农理论》是在长堤大学写成的。虽然导师是加大的艾智仁与赫舒拉发,但个多小时的车程不方便,时间要预约,只能写好了初稿,让他们先读,才登门求教。这样,在长堤与我共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E。Dvorak就成为我的「试音板」了。每有新意,向他表演一下,看他是否大叫天才。
长堤有一个小奇迹。那里的图书馆竟然有全套的《台湾农业年鉴》。是奇怪的刊物,有点发神经。这年鉴详尽地罗列了台湾每年每县的每种农植的耕地与收成,包括农地面积与耕地的轮植,印得密密麻麻,中英对照。没有谁会翻阅这样的刊物,而就是作农业研究,这类资料一般用不上。只是我要以台湾的土地改革来验证佃农分成在管制下对土地的边际产出的影响,虽然重要但极为冷门,才用得着这类资料,甚至不可或缺。
记得艾智仁读到我论文中最重要的验证那章时,很有点不相信我的想像推理与统计数据,以为我可能在袖子里出术。我从长堤借出几册《台湾农业年鉴》,带给他看,他自言自语:「发神经,怎会有人搜集这些资料呢?他们要来作什么?」
顺便一提。一九六七年初我在长堤博物馆举行一次摄影个展,很成功。那时每星期教十二课,论文要赶工,展览的工作也得到Dvorak协助,而开幕的鸡尾酒会由他的太太主理。据说因为主理得出色,不少人跟着要求她主理酒会,大名远播,最后美国的西区经济学会的每年盛会都委托她主理了。光流水逝,匆匆数十年矣。
博士后我转到芝加哥大学。那是个很可怕的地方。名家云集(当年那里的朋友后来有六个拿得诺贝尔奖),各争上游,互不相让。讲座或研讨会议天天有,午餐一定谈学术,晚上酒会不醉无归。我在旁听、讲座、研讨、酒会之间疲于奔命,加上每隔一两天女秘书就把几篇文章放在我的书桌上,不少要评审。我奇怪那里的一些同事可以活到今天。
衷心说实话,我喜欢学,学得快,但绝对不是个喜欢跟人家研讨或辩论的人。从广西拿沙的日子起我喜欢独自游玩,有自己的世界,而长大后喜欢独自思考,不管外人怎样说。我可以一连数天足不出户,有时一整天呆坐书房。少年时在香港逃学,没有伴侣,我往往一个人坐在柴湾的一块巨石上下钓。根本没有鱼,永远是那块石,只是四顾无人,胡乱地想着些什么,对我是一种乐趣。学术上我很少与人争论,谁对谁错于我无关痛痒。港大有一位同事,一事无成,见我不回应某人的批评,大做文章,说我不负责任。胡说八道。回应批评我可以大量地增加文章数量,但何必做这些无聊的工作呢?思想是自己的,独自魂游得来,是对是错是轻是重,历史自有公论。没有机会传世的学术文字,不写算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中,一方面我很希望能得到那里的大师的启发,另一方面我不想参与他们的思想竞赛。史德拉(G。 J。 Stigler)与佛利民是天才,当然可以教我,但他俩当时如日方中,是大忙人,不敢多花他们的时间。虽然佛老的办公室在我隔邻,我是要到他退休了才多求教于他。夏保加(A。 Harberger)的课我旁听了一段日子,但他既是系主任,又是拉丁美洲的学生领导,分身不暇。舒尔兹(T。 W。 Schultz)与庄逊(D。 G。 Johnson)搞农业经济,本来志同道合,但他俩忙于行政工作。另一个庄逊(H。 G。 Johnson)视我如弟弟,我感激,但他一半时间在伦敦。蒙代尔(R。 Mundell)是个怪天才,编辑名满天下的《政治经济学报》,我只在酒会时才能与他多谈几句。L。 Telser是个独行侠,H。 Usawa带他的一群学生,Z。 Griliches整天看数据,G。 Tolley有他自己的项目——虽然大家常有来往,但研究的兴趣有别。余下是几个像我那样的后生小子了。
芝加哥的法律学院别有天地。戴维德(A。 Director)是我的英雄,但比我年长三十四岁,正退休,我不便常常请教他。高斯(R。 H。 Coase)也在法律学院,编辑《法律经济学报》,研究兴趣与我相近,治学方法一样,所以谈得来。我与高斯的往事,写得多了,这里不多说。
芝加哥学派名不虚传。这学派不是外间说的高举自由市场,或是大捧货币理论,而是他们重视理论或假说的事实验证。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也同样重视,只是远不及芝大那样人多势众,「思想斗争」远不及芝大那样热闹。
我认为经济学除了解释现象没有其他用途,就是提出政策建议,经济学的贡献是解释政策会引起的效果。我走经济解释(事实验证)的路走了整整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