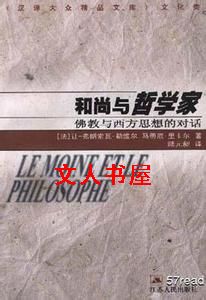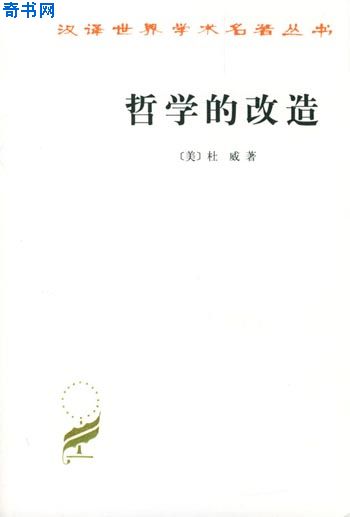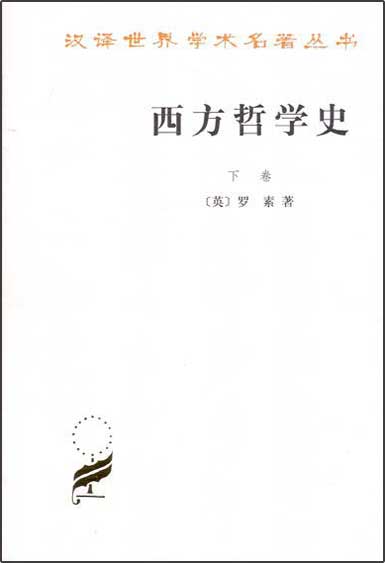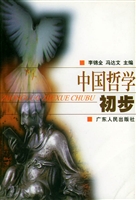诗化哲学-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甚至把费尔巴哈也归入这种浪漫派。⑵他把这种浪漫派视为衰微的同义词。此外,他还根本否认雪莱、列奥帕蒂、海涅、爱默生是浪漫作家。因此,有人称他为新浪漫派之始。但他究竟给了浪漫精神一些什么东西呢?他提出的东西究竟是值得赞同的,还是应该否弃的呢?正如对任何一个权威我们都不能妄加信奉一样,对尼采同样如此。
尼采与早期浪漫派一样,企图复活远古精神,膜拜希腊神话,寻求现代的新神话学,不自觉地把艺术尊奉为神。他所提倡的狄奥尼苏斯精神,是施勒格尔早已发现了的古代现象。《快乐的科学》也与《卢琴德》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青年尼采还曾醉心于诺瓦利斯的著作,自称对诺瓦利斯的哲学见解感兴趣,而实际上,他对道德的看法又确与诺瓦利斯的见解有瓜葛。他的《悲剧的诞生》明显地与施勒格尔对古希腊的研究有关。施勒格尔在他的《希腊诗研究》中提出,要建立德国的“新的定在形式”(NeueDaseinsfovm),想通过德国精神与希腊精神的再结合来进行一场“审美革命”,这一设想,实际上在作为新的人性——诗性的代表,扎拉图斯特拉身上实现了。凡此种种,都表明,尼采在精神渊源上,是与早期浪漫派一脉相承的。
但尼采的直接出发点,又仍然是由叔本华所翻转过来了的生存意志的本体论。所不同的就在于,意志生命本体不是要通过诗化,或审美的显现(直观)来扬弃自身,而是意志生命本体自身就是诗一般地沉醉、升腾、勃发。叔本华手中的意志尚只是盲目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动机),在尼采那里,已膨胀为一种原始性的生命力的实体。充实、弘大的生命力就是本体,生命力是超个人、超主体的原始般的充满激情的实在,是永动和矛盾,苦恼和极乐,是万物之原,是世界的唯一根基,只有它能使感性个体深挚、坚强。个体的使命就是把自身中蛰伏着的生命力发挥出来,从而与超个体的生命本体合欢,这本身就是诗。
尼采从希腊文化中去发现人类生命力弘扬的理想,以富于弘大、沉醉、华美的生命为追索的境界。因为,他觉得现代社会和近代精神早已把生命力扼杀了。“非人格化”的机械和机械主义,工人的“非人格化”,错误的“分工”经济,使生命成了病虽态;作为达到文化之手段的现代科学活动导致了生命的野蛮化。而人类的精神早在苏格拉底之时就开始败坏了,这就是由于逻辑推导的知识的出现。
尼采讲,苏格拉底主义的“知识即美德”是一条害人不浅的信条。它把人从一种梦境的幻美世界引向一个虚假的逻辑领域,梦境的倾向已经在逻辑三段论的外壳里化成蛹,悲剧艺术彻底败坏在他手里。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代表着一个在希腊世界闻所未闻的人类典型的出现,即专事推理的人类类型的出现。它欺骗人们泰然自若地相信,由于逻辑的引导,思维能接触到存在的最深处,不仅能认识存在,而且还能稍稍加以变化。这一骗人的形而上学的幻象,又进而变成了科学的本能,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科学引向它的极限。“在科学的神秘论者苏格拉底之后,哲学的派别相继而兴,一浪接一浪,于是一种料想不到的广泛的求知欲普及于全知识界。仿佛求知是一切得天独厚的人们的特殊任务,这就把科学引人汪洋大海之中,从此它一去不返。由于求知欲的普及,一个共同的思想之网第一次笼罩着整个世界,而且大有穷究整个太阳系的规律之展望;——如果你看清楚这一切,以及现代科学的高得惊人的金字塔,你就不禁要设想,在苏格拉底身上见到所谓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⑶。
在对一切知识的占有欲的驱使下,科学一往无前,永无厌足地乐而忘返,结果,对生命力的美好感受就被取而代之了。对万物的本质不是以生命去感受,去体悟,而是借诸知识与认识去测量。深入万物的奥秘,成了唯一真正的人类天职,建立概念、判断、结论等手段,被视为一切才能之上的最高尚的事业和最值得赞美的天赋。甚至那最崇高的道德行为、恻隐之心,以及“心如止水”的梦神式的涵养境界,也被知识的辩证法,思想的助产术败坏了。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简直就在暗示,苏格拉底当初被希腊国家公审法庭判处死刑而不是放逐,这完全是公正的,因为他直接影响促使酒神悲剧瓦解。苏格拉底本人到是第一个借知识与理论来超脱死亡的人。为了知,他临刑时泰然自若。他的这一举动是在提醒人们,只有科学和知识才使生存显得有意义因而也才显得合理。但科学是否真能使人超生死,是否真能为人生提供意义呢?当科学和知识统领了世界之时,出现的却是荒诞、自杀、苦闷。苏格拉底的知识至上说是一个最大的骗局。如今,知识与人格的严重分离不是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吗?所以,尼采说,苏格拉底把知觉看成是创造性的,实在是一件大怪事。科学迟早要被神话所取代,科学的终极目的就是神话。到底还有一个知识王国是逻辑学者不得其门而入的。
尼来把西方智慧从苏格拉底起就一笔给勾销了,康德、黑格尔这些大哲更是不在话下。后来海德格尔提出,西方形而上学自苏格拉底以来就误入歧途。他更为彻底,甚至把尼采也算作是苏格拉底线上的人,而且是最后的完成者。而实际上人们照样也可以把海德格尔算作是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者的。无论如何,海德格尔有这么大的口气,固然首先得之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法,中止一切权威的判断,把它们搁置起来,但也不能不说与尼采的精神有着相当的瓜葛。⑷
尼采拚命反对求知欲和科学的追逐,这与浪漫派否弃科学,提倡诗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知识、科学是否能解决人生问题,是否能提供生存的意义和合理性?是否有了知识就等于是一个完美的人格?现代的许多刽子手往往是很有知识的。尼采继叔本华在本体论上的转变之后,在认识论的转变上又向前走了一步。他反对的不仅仅是因果、时空的思维方式,而是整个求知欲。人们所应认识的,不是关于实在的知识,而是自己的生命及其价值。一味追逐外在的知识,乐而忘返,必然会带来内在生命的丧失。
尼采预言,科学的求知占有欲最终是要碰碎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认识,新的知识,即艺术式的认识,人生的知识。“因为,科学领域的圆周有无数的点,至今尚丝毫不能想象这领域能否彻底测量;所以才德兼备的人,未到人生之中途,便接触到这圆周的边缘,由此看入渺茫的所在。一旦栗然见到理论到了科学的权限便蟠虬乱转,终于咬住自己的尾巴,于是,一种新的认识,悲剧的认识,突起浮上心来,那就需要艺术的保护和救济才能忍受得住。”⑸
正由于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求知欲占据了西方精神,所以,追寻生命的本体就不但要超逾科学的思维方式,也要超逾历史,返归人类太初的质朴。尼采在前苏格拉底的神话中找到了生命本体的诗。“希腊人在萨堤儿身上见到的,是未受知识玷染,未入文明门阀的自然,……萨堤儿是人类的本相,是人类的最高最强的激情之体现,是因接近神灵而乐极忘形的饮客,是与神灵同甘共苦的多情的伴侣,是宣泄性灵深处的智慧之先知,是自然的万能性爱之象征”。⑹
人因天禀生命力而具有无限开发的可能性,活的血性的感性、意志、直觉是本能的自由的生命显现。寻求浅薄的快乐,绝非人的神髓。充实的人生,固然伴有深切的满足之感,但也伴有深切的苦痛之感,人对于痛苦经验的深浅,乃表示他生命力充实的程度。坚强的本能、意志是人的理想的人格,这是毅然决然独步人生的道德。尼采把浪漫派的审美的超验性(拒斥庸俗现存社会的超验性推向否弃陈腐的偶像和习俗,激励人去自由地建树新的生活方式。“尼采关于超人之说,是一种诗一般的召唤,要求有一个比较仁慈的、比较具有创造力的人,把欢乐和尊严授予这个人类生活”。⑺
在尼采看来,生命力本体本身就是诗,就是美。世界犹如一件自我生育的艺术品,艺术家的创作不过是对生命的谢恩。即使现象不断毁灭,生存之核心却万古长青。另一方面,本体也需要美化、诗化、艺术化,“真正的存在和太一,这种永劫和矛盾,同样也需要醉心的幻影,快乐的假象,不断地来救济它”。⑻这不但是因为,“我们自居为艺术品,在这一意义上有莫大荣幸;——因为,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来看,存在和世界才是永远合理”,而且还因为,“求知的我们并不就是‘存在’本身,——存在才是这种艺术喜剧的唯一作者和观众,是它替自己准备了这永恒的娱乐。唯有当天才在艺术创作活动中同这世界的原始艺术家融合为一的时候,他才能窥见一点艺术的永恒本质”。⑼由此,本体论的诗推导出来了。
在尼采的笔下,所谓“存在”,所谓“世界”,都不再具有传统本体论上的自然实在或客观外界的含义,它们就是生命力,亦即意志的代名词。尼采的生命力本身也就是权力意志。只有领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他对本体的如下诗一般的描述。
存在对我们说,像我这样吧!我,在外表的永远变幻之下;我,永远在创造,在促进生存;我,万物之母,随时用这形象的变化来满足自己。
“世界就是:一种巨大无匹的力量,无始无终,……一个奔腾泛滥的力量海洋,永远在流转易形,永远在回流,无穷岁月的回流,以各种形态潮汐相间,从最简单的涌向最复杂的,从最静的、最硬的、最冷的涌向最烫的、最野的、最自相矛盾的,然后再从丰盛回到简单,从矛盾的纠缠回到单一的愉悦,在这种万化如一、千古不移的状态中肯定自己,祝福自己是永远必定回来的东西,是一种不知满足、不知厌倦、不知疲劳的迁化——:也就是我的这个永远在自我创造、永远在自我摧毁的酒仙世界。”⑽
对于这样一个本体世界,当然不能依据理性、逻辑去推论,而应凭据以本质为本的直觉,凭据审美直观。它实际上就是个体的生命力摆脱一切历史的重负,重归宇宙的生命本原。所以,人的本能生命力与日神的梦境世界的交溶,与酒神的醉境世界的交溶,与大自然的和解欢庆的共醉,不依赖于知识,不依赖于推理、演绎,完全是以整个生命去把握对象,是一种莫名颤动的统一感。正是在这种统一中,人与宇宙的本原同一了,被疏远了的、敌对的或被征服了的大自然再度与她的浪子(人)欢庆和解。
与尼采同一时代的狄尔泰这样评论他:“尼采明确有力地表述出他否定推论的、逻辑的知识得出的最后结论。在尼采看来,人作为文化的创造者,首先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才是科学意识,由于对人的使命的绝望,他成为创造和建立价值的哲学家。有情感有想象的与众不同的人的特征在于,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力掷入生存的一种形式,在于当地发现了这一生存形式不恰当时,他能激切地否弃它,因为生命的形式是不可重复的。”⑾
从上个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