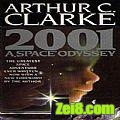书屋2002-01-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作品洋溢着宗教与人性的光辉,使他的诗不是纯粹的哲学的诗化或哲学化的诗,而是具有宗教目光的人性的诗化,从而更深地揭示了人作为人的本来面目:存在中一分子,自然中一员。
“诗不是诗人的陈述,更多的时候是实体在倾诉。”在海子这里,诗是自然生成的,而诗人的任务不过是把它说出来而已。
就让我这样把你们包括进来吧
让我这样说
月亮并不忧伤
月亮下
一共有两个人
穷人和富人
纽约和耶路撒冷
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
一同梦到了城市外面的麦地
白杨树围住的
健康的麦子
养我性命的麦子!
“朦胧诗”群体在诗歌界造成的印象是:诗就是努力地发掘词语的涵义,从而使诗歌的涵义呈现出“不可捉摸”的特征。这也成为当时诗歌的主流。海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创作的目的就是要拂开历史语境在词语表面造成的遮蔽,使词语回到涵义本身。比如“麦子”、“麦地”等海子的常用意象,读者(评论家)们常常认为它们包含了很丰富的涵义,但只要我们认真地参读原作,就会发现诗人是在元素和词根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的。“麦地”就是生养诗人的麦地,“麦子”就是诗人赖以延续生命的麦子。正是对这种“元语义”的运用,才使海子的诗作普遍带着一层神秘忧郁的色彩,充满了某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空旷气息。诗人选择了“民间”作为自己的桃源。所谓民间,在文学上其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并不是语言或体式,更重要的是在文本中流露出来的价值立场。民间并不代表对抗,而是一种自在、自足的状态,是一种倾诉。对于诗人而言,只有走向民间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诗歌的土壤,诗歌才会具有从土地里流露出来的真实的声音。
“在什么树林,你酒瓶倒倾/你和泪饮酒,在什么树林,把亲人埋葬”;“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些淳朴而直白的诗句就像黄土高原上默默流淌的黄河,沉静而安详。诗人知道自己首先是一个人,也有常人的喜怒哀乐,所以他为自己亲人逝去而忧伤,在本是关心人类的时刻想念自己的姐姐,并且只想念姐姐而不关心人类。这就是真正的世俗的、民间的立场。诗的意义逐渐从“群体话语”中脱离出来,回到语言的本身。
检索一下海子的诗篇就会发现:它收集了大量上古神话语素,这些语素长久在语言的河流中存在,但在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由于时光的流变已经使其意义显得含混而暧昧。诗人抛弃了自己的所谓“知识分子”的既定视角,深深地沉入语言之中,或是直接追寻到几千年前的神话中的原始涵义,或是退而在真正的民间找到抒情的语句:“你是我的哥哥你招一招手/你不是我的哥哥你走你的路。”“民间”作为诗人的家园和理想王国在诗歌中构建起来。诗人以飞行的速度穿梭于各个时空,历史在诗人笔下重现。
面对社会,海子显得沉默而孤独。他和他最重要的朋友骆一禾一起,站在民间的土地上,坚韧而执著。深入民间是一个艰难的任务,描述民间,更是面向孤独的写作。在当今工业化继续加剧的今天,海子所歌唱的农耕时代的一切都在逐渐消散。但一种沉重的使命感驱使他不断地走向民间的深处,将散失在民间的那些农耕时代的余晖一缕缕地收集,组建起一座民间的诗歌大厦,在荒野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早在1985年,海子就说过:“走出心灵要比走进心灵更难。”这就像一个预言,注定了诗人最后的悲剧结局。
早期的海子对诗歌的力量充满自信和期待,他希望自己的所有信念都可以在诗歌中得到满足。在那首脍炙人口的《祖国(或以梦为马)》中,他写到: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在工业社会的强大攻势面前,农耕文明不堪一击,毫无还手之力,被这一社会的必然进程打得粉碎,灰飞烟灭。海子对自己本身的失败早已有所预感,他也知道所倾慕的农耕文明只存在于遥远的理想和现实的诗歌中。他所做的不过是把一个图景展现出来,展示它动人心魄的美丽。农耕文明的一切犹如空谷足音,渺远非常,“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海子也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必将孤独而无望,“只身打马过草原”。但他对诗歌的力量始终保持了难能可贵的自信力。在喧嚣的尘世,诗人努力地建造一座民间的诗歌大厦,成为诗人理想和生命的寄托。直到有一天,诗人发现自己建造的大厦所依赖的基础——农耕文明在工业社会的冲击下烟消云散,一切对农耕文明的歌颂都已成为过眼云烟,诗歌已经变成一些人争名夺利的工具。诗人的理想、追求都因为基础的丧失而变成没有希望的空想,真正的打击一下击中诗人的心脏。随着农耕时代在人们的视野里渐行渐远,诗人生活的信心也逐渐消亡。在海子的最后一首诗作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出他对死亡的倾慕: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
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海子一直以诗歌的王子自居,并且把自己与普希金、兰波、波德莱尔相并列。他的作品有许多就是诗人与这些王子的直接对话。这个王子的家谱上写着代表人类最高贵的精神家族的成员。那些早夭的天才在人类精神史上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诗人之死,在1989年3月26日。
诗人之死,并不单纯是诗人个人的死亡,而是象征着农耕时代的最后一位歌手的死亡。当海子在列车的重压下为农耕文明殉葬而去的时候,列车也卷走了农耕时代的最后一抹余晖。
新世纪的一页正在打开,新世纪的诗坛沉寂而荒凉,……每到黄昏,站在世纪的交界,我们依然忍不住回望十几年前那片美丽的风景,想起远去的诗人……
也给李慎之先生一封信
? 解正中
李慎之先生:您好!
等了一个多月,《书屋》2001年七、八月号合刊总算出来了。当我看到林贤治先生给您的信后,不禁怅然若失,惊诧不已。林贤治先生不少文章是颇具锋芒的(如去年发表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然而,这篇为鲁迅先生正名的辩辞,似乎是走了题。由此看来,他的思想深度是远远落在先生之后了。
您对“五四”精神的论述,对鲁迅、胡适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我除了对“宽容”一节略持异议外,您所说的“能够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毋宁还是胡适”等观点,都可以成立。林先生的某些论述,难以使人折服,比如林先生说:“陈独秀并没有像先生那样把个人主义从民主法治、自由主义那里分开。”谁把个人主义同民主法治科学自由分开了呢?您不但没有分开它们,还强调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甚至是民主科学的“始基”。我同意您对“五四”精神的进一步阐明。德先生、赛先生、自由、法治等较有规范性的概念,比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等概念明确、具体。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概念不仅有些空泛,且易被曲解。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允许的事。个性解放不是无边的自由,更不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个性解放、个人主义只是一种精神欲望,不是行为规范,而个人价值的体现,个人愿望的实现,真正人权的确立,最终要靠民主、法治、科学等来保证。如果说个性主义是“多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而个人主义“则表现在社会国家方面”,那么,此二概念在林先生眼里显然也还是有区别的,尽管都是以个人价值为本位。由此可见,“个性解放”的概念诠释有欠单一的准确性,不如民主、科学、法制、自由等概念所包括的内涵明白、实在。陈独秀所讲的那段几乎无所不包的内容,只是归结为一个目的:为了人权。然而,陈独秀五四时期喊得最响亮,阐述最核心的,仍然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科学、法制、自由,与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绝无矛盾,问题在于“五四精神”的清清楚楚的准确表达究竟是哪个更好?在我看来,个性解放是目的,民主科学是手段(民主有时也是目的),我们是用手段去达到目的呢?还是高喊口号(目的),而轻视手段?无疑手段更重要。陈独秀先生之所以是位贤者,就因为他在晚年大彻大悟之后,把民主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了,而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先生是一直十分明确的。
评价胡适的功绩,不等于否定鲁迅先生的伟大。您的文章,也一直是这个观点。不知为何林先生得出不同的结论?鲁迅伟大,也不等于鲁迅每一件事,每一个观点,都是正确的。正像胡适也不是“每事对”一样。圣人还有三错哩。……我始终认为,鲁迅、胡适对旧礼教、旧宗法、封建主义、独裁专制,都是非常痛恨的。但在“立”的方面,胡适毕竟比鲁迅用心更多,也更富于思想成就。
海 子 论
? 枕 戈
我原以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的是精神颓废、意象繁杂、死气沉沉的朦胧诗,而没有那些清澄透明、构想新奇、抒情有力的诗;我原以为在中国是不会产生史诗的,而不知在八十年代产生了庞大雄奇的现代史诗《诺日朗》、《太阳七部书》……而海子是高踞于那场诗歌运动中最杰出的诗人——海子不朽!
“当我们面对穆旦的诗歌时……我们面对的将是整个世界现代诗!”——这是查良铮;在经历他的转折和承上启下后,海子以他空前的精神力量从八十年代崛起来了,倒下了,“海子的早逝是世界文坛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查海生。“两查”让中国诗歌重新展示了她原有的风范和魅力。
海子在燃烧了他五六年的诗歌生命后卧轨自杀了。有人说这是人类飞蛾扑火的举动,有人说他成就了烈豹扑向太阳的英雄之举,也有人说这世界真是黑漆漆的一团——海子说他自己“走到了人类的尽头”。总之,思考的人们对诗人之死或有一种快慰或有一种恐惧感,连我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也感到一丝生的渺茫虚无了。
单就诗歌而言,在我们的祖先写完无比辉煌的唐诗后,我们还要用方块字写一种白话诗,一种风格、形式迥然不同的“现代诗”。有人在诗歌写作中继承了古典诗的辞藻,有人则刺取了西方诗歌的技巧。在这场争闹中,最有价值的诗歌却成了殉葬品。所以,在中国,往往最喧闹的